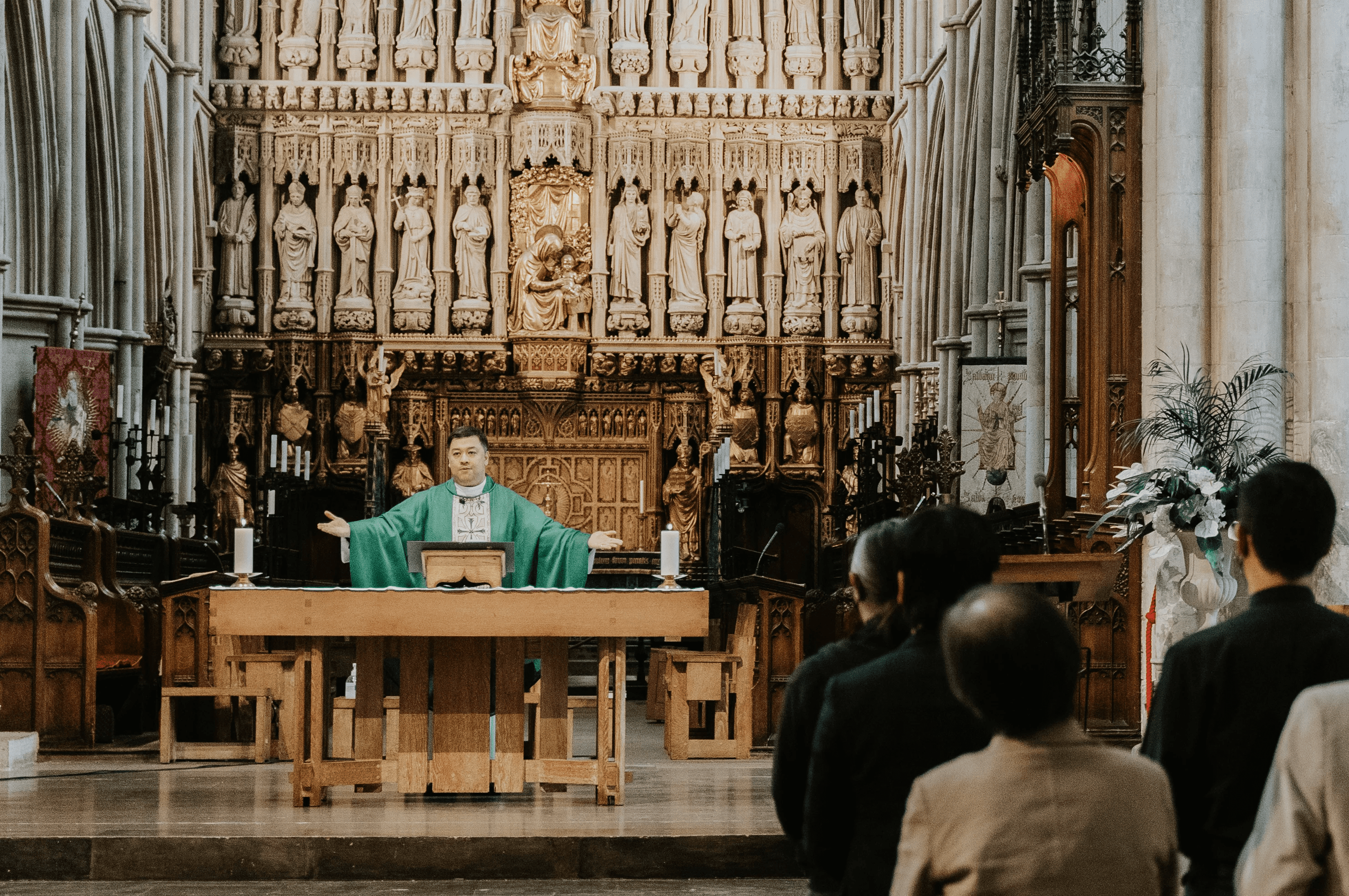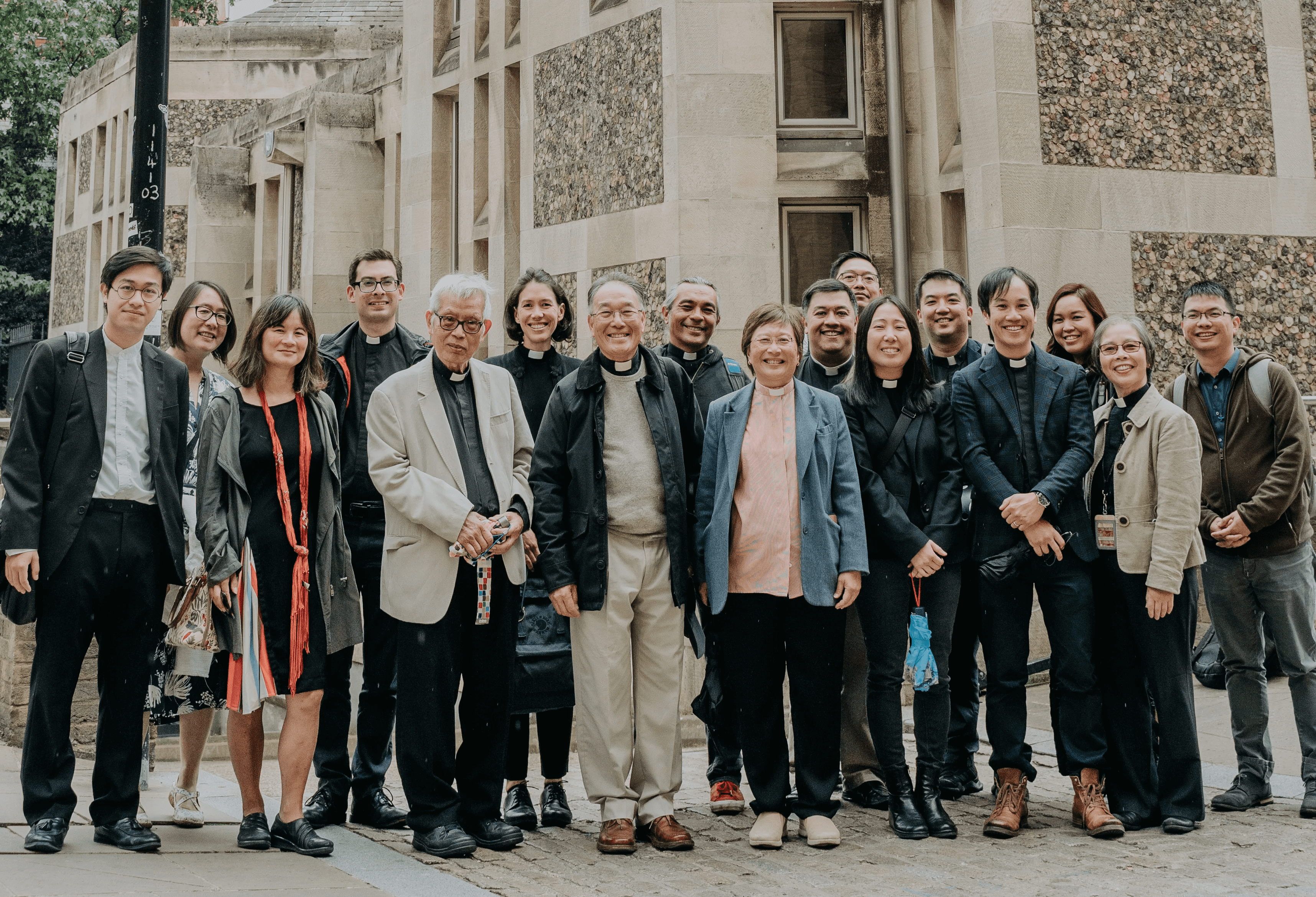在1899年的最後一天,中國反動派人士綁架了西德尼·布魯克斯(Sidney Brooks),一位24歲的英國聖公會差會(SPG)宣教士。他們對宣教士進行了數小時的折磨後將其殺害。英國當局迅速採取行動:處決了兩名罪犯並被要求賠償。但如果英國人以為這樣就能平息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怨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接下來6個月內,成千上萬憤怒的中國人從華北的村莊裡大吼大叫地跑出來,揮舞著刀劍,高呼:“燒,燒,燒!殺,殺,殺!”他們拆毀小會堂、大教堂、孤兒院、醫院和學校,並殺害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他們的暴動被稱為義和團運動,為新教現代宣教運動帶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上海心態
致使義和團起義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但可以用“外國人的傲慢”來作為總結。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外國人在一個又一個條約中迫使中國讓步,獲得了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德國人,以及最大的一群日本人,把整個國家分割開來,有如在玩“冒險”(Risk)桌遊一樣。外國人有時甚至能擁有整個城市的控制權。
更糟糕的是,他們在中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橫行,因為知道自己不會因任何罪行被逮捕。如果一個喝醉的水手殺了一個妓女,或是他的船長放火燒了一艘貿易船,他們會受到中國給予高級外交官員的治外法權的保護。
有太多的宣教士(不包括戴德生)持有所謂的“上海心態”,也就是將他們的飛地(一個國家境內有一塊主權屬於他國的領土)之外的世界視為“異教徒的世界”。在一些地方,宣教士與英國當局的關係比跟當地人更親密,他們更喜歡在領事館內跟水手們一起踢足球。
許多外國人也鄙視中國人。一位加拿大人說,一位“溫和的挪威人”曾告訴他,“在這裡待了幾年後,他的精神狀態變得非常遲鈍,有時會擊倒或弄傷中國人”。
宣教士的驕傲和中國人的憤怒在1899年爆發。那年,中國政府授予宣教士官位,讓主教或教長有等同於省長的權力,而普通的外國人則等同於地區行政長官。一位宣教士寫道:“還有哪個政府會給福音宣教士這樣的特權?”
許多冒險進入“異教徒的世界”的宣教士則是不自量力。他們之間不少人公開嘲笑中國人視為神聖的信仰——祖先崇拜和儒家戒律。有些人會在中國人進行祭祀行為時衝進寺廟,譴責他們拜偶像。
一位美國作家在1900年初寫道:“中國從衰弱的文明中被釋放出來的那天即將到來。他們的原動力將來自基督教所啟示的重要真理。”這句話代表了當時多數外國人和宣教士的想法。
和諧的拳頭
在19世紀90年代末之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得他們已經受夠了。義和拳,或稱義和團,開始引領這股不滿的力量。
義和團的起源不詳,但到了1890年代末,他們身上總帶著一股神秘的色彩。他們在手腕上繫著紅絲帶,腰間繫著黃腰帶,頸部掛上黃色護身符。他們相信外國武器傷害不了他們。他們的法師對群眾表演,用一把火槍(裝著空彈夾)射向一個教徒,以此來“證明”他們有刀槍不入的能力。他們低聲念著咒文,誘導人們進入恍惚的狀態,且信徒之間用秘密信號和密碼交流。
義和團的倡導者挑起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恨。他們宣稱外國人是“一等魔鬼”,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是則是“二等魔鬼”,那些為外國人工作或與他們合作的人則是“三等魔鬼”。他們四處散播中國的兒童在基督教孤兒院被殘害、中國婦女被誘騙到教堂裡遭受強暴。
他們散發數以千計的傳單和公告。其中一份提到了當前造成巨大痛苦的干旱狀態,說:“由於天主教和新教對中國神靈無禮,破壞了神聖性,不服從佛祖,激怒了天地,雲雨團因此不再到來。但800萬靈兵會從天而降,把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掃蕩乾淨!”
席捲而來的暴力
1900年1月,事態急遽發展。在北京,反動勢力對皇帝和皇位背後的力量——慈禧太后的影響越來越深。皇宮發布了一道鼓勵義和團的詔書。在整個冬末和春季,義和團增加攻擊的次數。各處村莊被洗劫一空,也首次出現關於中國基督徒被殺的報告。
義和團的怒火在當年6月份爆發開來。山東長老會的建築物被一群暴徒摧毀。兩名英國宣教士在保定府東北幾英里處被殺。位於北京城外的美國傳道委員會的基地被燒毀,多名基督徒被殺。
6月中旬,暴力事件席捲了北京,國際部隊被從沿海召來保護外國人。軍隊在途中遭到抵制,但還是攻下一些中國堡壘。慈禧太后認為這次攻占是一種宣戰行為。6月24日,皇室頒發詔書命令在全中國境內屠殺外國人。
在北京,外國人群體蜷縮在城市的一個小區內,長時間被圍困著。在中國的宣教士無處可去。這次起義主要不是反對基督教,但宣教士和他們的信徒是主要的受害者。
6月30日和7月1日,在保定府有15名宣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被殺。
7月12日,兩名男子、五名婦女和五名兒童,全都是外國人,以及五名中國基督徒在大同被殺。
7月31日,六名宣教士和八名中國人在太谷被處決,他們的頭顱被帶到了總督那裡。
在山西省,巡撫毓賢策劃了一場最血腥的大屠殺。7月9日上午,在首都太原,所有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被圍捕起來。他們被戴上手銬帶到省長面前,省長被武裝保鏢包圍著。
一位在這場磨難中倖存下來的基督徒描述了當時的情況。“第一個被帶出來的是法辛先生(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地抱著他,但他輕輕地把她推到一旁,走到士兵面前,一言不發地跪下,他的頭被劊子手的斧頭一刀砍掉了。在他之後很快就輪到…..洛維特醫生和威爾遜(Dr. Lovitt and Wilson),他們每個人都被劊子手一刀砍下頭。然後,毓賢開始不耐煩,他吩咐他的保鏢(他們都帶著長柄重劍),讓他們幫忙殺死其他人…。”
“當男人被殺掉後,女人被帶走了。法辛夫人緊緊抓住她孩子們的手,但士兵把他們分開,一刀砍下他們母親的頭……洛維特夫人被殺時還戴著眼鏡,握著她小兒子的手。她對人們說:‘我們來中國是為了給你們帶來耶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們沒有對你們帶來傷害,只有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待我們?’一名士兵在斬首前摘下了她的眼鏡,砍了兩刀才成功。”
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天主教徒以同樣的方式被殺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一些人的頭被放在城門上的籠子裡。
像這樣屠殺的消息傳開後,宣教士家庭和忠誠的皈依者把他們的財物收集成捆,徒步或駕著騾車、驢子試圖逃離。許多人成功到達偏遠的農村地區,在那裡過了幾天或幾週神經緊繃、衣衫襤褸的被追捕的逃亡生活。有些人倖免於難,或者躲過了追捕;有些人則被抓住並被砍死。
8月14日,國際部隊解放了北京。北京被洗劫一空,執行懲罰的遠征隊被派往周邊城郊,這導致了更多的暴行,只是這次是勝利者的暴行。根據一位英國上尉的說法,“傲慢的外國士兵分散去到一蹶不振的鄉村中隨意剝削”,導致了“搶劫、殺戮及各種暴行……許多無辜的和平的非戰鬥人員被屠殺……整個地區被無情且非必要地的清洗。”
一些宣教士利用了這樣的搶劫機會。雖然也有些宣教士試圖阻止搶劫的行為,但其他人依然故我的進行搶劫。有個人甚至寫了篇文章叫做“道德的搶劫”。許多宣教士差會要求對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及生命的賠償。(戴德生是拒絕接受賠償的宣教士之一。)
不斷增長的的憤怒
基督教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曾說:“基督徒的血是福音的種子”,這句話在中國也被證實是正確的。殉道者的勇氣,包括中國人和宣教士的勇氣,激勵著中國教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迎來三倍的成長。
不幸的是,中國人的憤怒之後又持續了五十多年,直到共產黨成功地把所有“外國鬼子”驅逐出境。
翻譯: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