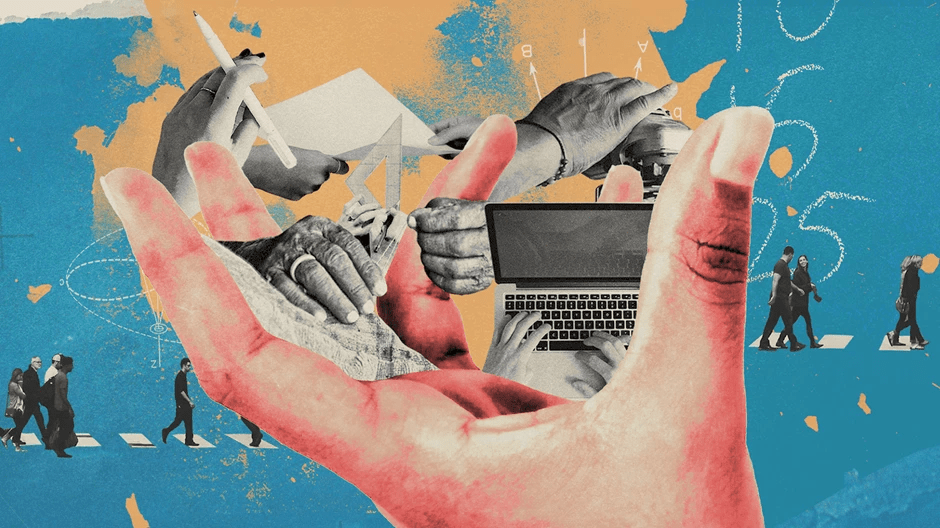「燈光。」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聽錯了。 請學生重複他的答案
「燈光。」
我再次陷入沉默。顯然我漏掉了什麼。
「你是說用電嗎?例如,代替蠟燭?」我不確定地問。
「不,」他回答。「我是說電燈——你知道的,電燈。」
我這才恍然大悟。這位學生指的是燈光,調光器、聚光燈、彩燈,與「舞檯燈光」相關的所有控制裝置——你可以在單口喜劇、戲劇製作或音樂會上見到這些東西。
我向大約40名大學新生提出的是這個問題:假設你下週末去一個新的城市旅行,週日早上你選擇去教會。你希望在教會裡見到什麼?
我經常以這個問題開始關於敬拜儀式的討論,即不同基督教傳統在公共敬拜中遵循的「腳本」,無論教會的敬拜較為熱情或是冷靜。學生通常會提到招待小組、引座員、位子的排列、成員、講道內容、什一奉獻、禱告、經文。有時會提到聖餐。很少人提到基督教信經和認罪。
但是,學生們有越來越頻繁提到科技的趨勢:螢幕、影片、攝影機、現場直播。還有其他同樣具有科技含量的元素(儘管他們並不這麼認為):麥克風、耳麥、樂團(皆有較多複雜細節的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科技發展和適應的標誌;所有這些在基督教儀式上都相對較新;至少在教會普遍使用方面而言,尚未經歷數個世代。
我的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誠實地說了他的第一個想法:燈光。當他想像去教會時,當他想像走進教會敬拜的地方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可控的照明系統。昏暗的燈光用於安靜冥想,明亮的燈光用於祝禱,聚光燈用於講道,不同顏色的燈光用於不同的樂隊成員和他們各自的獨奏時刻。
從聖言和聖事等基督教敬拜儀式到戲劇性的燈光秀。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的學生的回答主要反映了他們在大型教會的經驗。我的學生一般都是來自聖經地帶的福音派基督徒。即使他們來自農村或小城鎮,他們的成長經歷也會讓他們覺得那些是規則的例外,而潛規則是擁有高品質敬拜「製作」的富裕大教會。當他們搬到像阿比林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會以這個標準用腳投票(選擇教會);當他們搬到休斯頓、奧斯汀或達拉斯-沃斯堡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也會如此用腳投票。
但根據最近的研究,如今絕大多數美國教會的成員人數都在100人或100人以下。因此,當我們想到典型的會眾結構時,我們腦中的畫面應該是個由二、三十個家庭組成的地方教會型態。這種規模的教會很少有資源配備專業的照明設備,或是對專業照明設備的期望很低。他們更擔心的是如何讓教會的燈一直亮著。
此外,雖然美國教會的出席率和成員人數都在下降,而且美國教會的平均人數僅勉強達到三位數,但出席教會的總人口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大型教會。換句話說,隨著參加教會活動的人數下降,有參加教會的人也越來越多選擇去大型教會。這種現象改變了人們想到「一般教會」時會有的感覺及畫面,因此也改變了人們對「典型敬拜聚會」的想像。
要負擔、維護和操作我學生心目中那種專業燈光,教會的規模必須遠遠超過90%美國教會的規模,也就是超過250名固定聚會會友。然而,對我的學生和其他許多人而言,這樣的規模及其特徵已然成為教會的典型聚會方式,而非特殊的聚會方式。他們覺得「今日的教會就該是這樣啊」,是人們在陌生城市隨意參觀一間教會時的合理預期。
這樣的趨勢既是許多教會開始投資科技的原因,也是許多教會投資科技的結果,這些科技使主日早晨成為一個高製作成本的獻祭,無論這樣的獻祭是獻給現場的觀眾看,還是獻給在家看線上直播的人。早在COVID-19之前,許多教會就已開始一場科技儀式的軍備競賽,以有著高科技公共敬拜的「主日早晨」來吸引慕道友,尤其是年輕的家庭和專業人士。
對許多經驗豐富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Gen Z)福音派基督徒來說,最先進的、高畫質的、專業水準的錄影和音訊及音樂,配上流暢的轉場和華麗的燈光,無縫無障礙的為網路直播準備——已逐漸成為常態,「教會」,或「敬拜」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在最好的情況下,福音保留了穿透所有噪音的力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基督徒們既無法接收到主的話語,也接收不到主的身體和寶血。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長時間的輕搖滾音樂會中間,聽到一場精緻的TED演講,具有靈性但沒有宗教性。
毫無疑問的,這些教會的牧師們都是出於好意。如果有更多的人想聽福音、讚美上帝,我們難道不該讓他們有機會這樣做嗎?我們難道不該建造適合的環境,並禱告他們願意來嗎?
極少人會認為,光是教會建築物的大小就能證明教會不信實於主,而我也不是那種建議教會應丟掉麥克風,讓天生有大嗓門恩賜的傳道人講道就好——這種是所謂的反對科技進步的盧德主義份子(Luddite)才會有的擔憂。與科技有關的神學問題比這更嚴肅。首先,我們很少能預先找到答案。科技的益處及壞處需要在實地實踐中識別,而我們確實需要識別力。僅僅因為某樣新科技在一開始時看起來有助於教會的使命是不夠的。
我們可以反過來檢視基督教敬拜的本質是什麼。我問我的學生們,如果他們第一次參觀某間教會,他們會期待見到什麼?他們應該期待見到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教會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性回答是:他們應該期待聖言(講道)和聖事的儀式。他們在拜訪一間教會前就知道,除了少數有限度的不同處之外,他們會在教會裡禱告、唱詩歌、做信仰宣告(如念信經)、懺悔罪過、聆聽主在經文中的話語、聆聽人宣講福音,並領受主的身體和寶血——為了救贖他們而擘開的天糧。無論他們在哪個國家,使用哪種語言,旅行至大城市或是小鄉村,拜訪的是5000人的教會還是50人的小教區——等待著他們的都應該是這些。
請注意,舉行這個儀式的必需品有哪些:以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位領袖、聖經、一點餅和酒。換句話說,就是基督徒、聖經、象徵基督身子跟寶血的某些物質,以及ㄧ個能讓人們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這麼簡單。事實上,每個週日早上,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你都能發現人們在大教堂、私人住所、大樓公寓、購物中心、自助餐廳、泥屋、河邊、樹下、或藏在地下室和閣樓裡(怕被人發現)——舉行這個儀式。
這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奧妙之處。除了製作文本(早在印刷術出現之前)和飲食(生活所必需)所需的工具之外,教會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並不需要任何科技。也許,就具體情況而言,新科技有幫助儀式進行的潛力。但它們同時也有造成傷害、扭曲和誤導人們的潛力。
一方面而言,敬拜本身是一種教理(catechesis)。它塑造我們的心思、意念和想像力。年輕人確實有權在特定的主日期待見到他們在之前數百個主日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在我看來,目前的教理形式顯然奏效了,但卻是朝錯誤的方向奏效。
不少福音派基督徒如今誤認普通的敬拜儀式就是我在前面形容的「教會科技秀」——各方面而言都是一場表演。但既不是聖餐故事的表演,也不是儀式腳本的重演,而是一場精心製作的高畫質節目。如果我是對的,人們確實開始認為這樣的聚會是普通教會的聚會(因為這種形式在較大的教會中很普遍,而如今更多的人選擇去到大教會),那麼我的建議是,牧師們需要回到白板聚會的年代——或者我應該說,我們需要回到久經歷史檢驗的聖言和聖禮的智慧裡,也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基礎。
另一方面而言,試想一下,誰「有能力」參與這場敬拜軍備賽?肯定只有大城市的大教會。而誰沒有這種能力呢?所有其他教會。也就是說,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會無法玩高科技遊戲。
鑑於過去幾十年裡,有數千萬美國人離開了教會,我們的基督教儀式已然失能。考慮到教會的使命,敬拜軍備賽也是短視之舉。但最重要的是,這是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失敗。
我們不希望小型教會關門。我們希望各種規模、各種類型的教會都能蓬勃發展——以它們現在的樣貌,在它們所在之處茁壯成長。但是,如果現代教會的普通標準已經變成我上面概述的具備高科技製作的能力,那麼這些小型教會,即使坐落於大城市,也會繼續消亡,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缺乏跟上他們的鄰舍(大教會)步伐的資源。
關於如何引領一次充滿喜樂的敬拜,傳遞不受抑制、聖靈深刻臨在的敬拜,我們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一次信實的敬拜應該是任何教會都能做到的,無論他們的科技能力如何。
我們必須想像一種敬拜、教理(catechesis)的可能性——對像我學生這樣的基督徒來說,這種教理首先能讓他們想到復活的基督:祂永活的話語、祂的身體和寶血、祂聚集一處的子民。問題是:什麼樣的敬拜儀式才能讓我們產生這般心思意念?
作者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