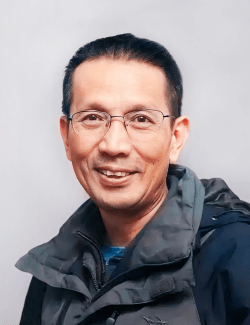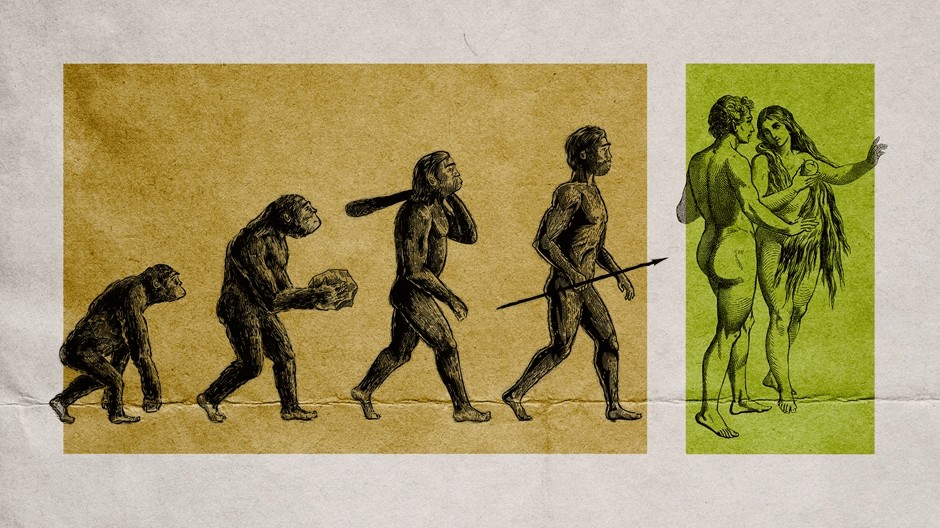人們常說,我們的文化已經失去了它的根基。就像歷史上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我們的時代是個人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確的事(士師記17:6)的時代。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正是上帝最喜歡的時代,祂能在此刻再次證明,祂在基督裡呼召的不是義人,而是那些失去了錨的人。
但在像這樣的時代,以這種角度看事情並不是我們的本能。當道德每況愈下,當人們行為不端,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用律法來敲打他們:「停止這樣做!你應該如⋯⋯這樣這樣做!」。無論在家裡還是在教會裡,這確實是我的本能反應。我常常忍不住想把上帝當作盟友:「聽著,聖經說⋯⋯所以你應該⋯⋯。」
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試圖呼籲讓這個「道德正在失喪的文化」回歸「聖經價值觀」的基督徒背後的動力。但是,回歸聖經價值觀的呼聲往往與試圖操縱人們做出正確行為的企圖連結在一起。例如,十多年前,佛羅裡達家庭協會(目標是「捍衛、保護和推廣傳統的聖經價值」)曾引發的風波:他們向勞氏公司施壓,要求撤下電視節目《全美穆斯林》的廣告。
「聖經價值觀」ㄧ詞的使用主要符合政治保守派的政治議程。但聖經價值觀並不屬於保守派。因此,我們不時聽到溫和派和自由派同樣呼籲根據「聖經價值觀」做出政治決策,在這裡,他們提及的「聖經價值觀」指的是對窮人的關心、使人和睦⋯⋯等等。
時不時地,一些政治領袖也會加入使用「聖經價值觀」的合唱行列,即使他們必須小心謹慎地用。英國前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當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的聖經詹姆士王譯本問世400週年紀念儀式上表示,「聖經幫助英國建立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觀,使英國成為今天的英國」,這番話引起ㄧ陣軒然大波。他認為,堅持聖經價值觀可以對抗「缺乏任何真正的責任感或道德準則」的現象,這種現象最近讓「一些銀行家和政客漠視社會上其他人」。他還提到英國曾經歷過的騷亂和「伊斯蘭極端分子持續不斷的恐怖主義威脅」。他說,「道德中立和被動性的寬容再也無法解決問題。」
見到英國人在短時間內經歷了這麼多事,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他們的挫折感。同樣的,當一些事件出現嚴重的道德問題時,我們本能地會想以道德律(或所謂的「聖經價值觀」)糾正一切。
但這個策略似乎未曾奏效。首先,在宗教選擇多元的文化或世俗國家(沒有法定宗教)裡,這種策略本身並不具有說服力。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會質疑一種強勢的宗教傳統價值觀。其次則是關於人性。你越是要求別人服從聖經價值觀,人性就越有可能反抗這些價值觀。去掉了「耶穌願為罪人而死(並復活)」的框架,聖經價值觀在不信的人耳裡聽起來不過是壓迫性的ㄧ系列律法。
在教會裡,情況則可能有所不同。首先,扎根於基督饒恕的框架下,談論聖經價值觀可能是有益的。因為聖經的倫理教導就會被視為「以愛為根基生活的指南」。這些價值觀不再是一系列律法,而是作為被恩典救贖的人具體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們的本能仍傾向把這些有益的教導變成純粹的律法,即使在教會內也是如此。我在自己的教會傳統——聖公會中就看到了這種跡象。我們這些聖公會內的保守派一直堅持要求主教們在性道德問題上「服從聖經的權威」,當聖公會總會拒絕後,我們拿著聖經成立了自己的教會。
又或者應該說,成立了「教會們」。因為從那以後,我們又分裂成各種聖公會運動和分支教派。而分裂至今依然繼續著,聖公會美洲傳教會的八位主教辭去了在盧安達省的職務(在這件事發生的幾年之前,他們曾公開承諾會順服盧安達省的教區)。這些分裂向我表明,我們的動機也許不像我們起初想像的那樣充滿恩典。就我個人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的動機並非如此。因為我被激怒了,我再也無法忍受他人對聖經權威的不服從!
當聖經被人這樣使用——作為單純的律法——就會產生一種教會文化,在這種文化裡,分裂及分裂中的再分裂持續發生著,即使聖經的權威不再受到威脅。
* * *
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我們保守派為「聖經的權威」或「聖經的價值觀」辯護時,我們常試圖讓其他基督徒服從某些教義(如童貞女降生或基督的代償贖罪)或服從某些道德規範(如禁止婚外性行為或看限制級電影)——我們將聖經當作讓他人服從的籌碼。
容我為自己澄清一下。我確實相信耶穌由「童貞女」所生、相信基督的代償贖罪、相信性行為應發生在婚姻中的一男一女⋯⋯等等。我相信經典的正統教義和倫理,因為我相信它們是聖經所教導的,或是從聖經教導中推論而來的,我相信聖經是上帝神聖的啟示。
但我並不認為聖經從根本上是個道德工具。與其說聖經是一本律法書,不如說它是一本禮物書;與其說聖經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生活,不如說它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與上帝相處、建立關係——因著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可以肯定的是,聖經在某種程度上是用來「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的,但聖經的目的並非讓人們緊緊持守著規定,而是像保羅所說的,使我們「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3:16-17)。在我看來,如果聖經的教導能產生出「善事」,肯定是以上帝的寬恕為基礎,以及耶穌基督為罪人而死並復活的恩典。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下,我們的「善事」才是以愛為基礎,才能結出聖靈的果子。否則,所有教導僅僅只是一系列的律法。
我相信我們受到律法的誘惑比我們願意承認的多很多。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談到聖經中關於上帝的愛的信息時,我們之中很少人會推崇聖經的無誤權威或讚美它的神聖啟示性。我很少聽到人們這樣說:「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林後5:19)——我們可以相信這一真理,因為這是神無誤的話語!」或是,「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5:1)——是的,我們真的從律法中得了自由,因為上帝無懈可擊的話語是這樣說的!」相反的,我很常聽到人們說:「你不能有同性戀關係,因為聖經這樣禁止。」或者說,「你必須相信從童貞女而生這件事,因為聖經這樣說。」聖經已不再是向我們啟示好消息的書,而是一本道德之書。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包括我自己——我們無意間侵蝕了聖經的教導。整本聖經裡至少有一個明確的信息,那就是:律法不能使我們成為義人。拼命遵守每一條聖經教導,或試圖讓別人遵守它,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事實上,宣揚律法及其權威——甚至是聖經的權威——會產生與我們意圖完全相反的效果。正如保羅所說,律法只會喚起我們的「惡慾」(羅7:5)。當有人告訴我必須做某件事,必須服從某種標準或律法,我只會想反抗。這就是聖經關於人性的教導。我們在遵守律法方面的經驗每天都在證實這一點。因此,我們越是把聖經當作律法的棍棒,人們就越會反抗它。
難怪每當我們把聖經當作律法書時,它都無法說服他人。也難怪它能如此迅速地在我們中間形成一種恐懼文化。我們這些以「聖經的權威」為基礎建立新教會的人可能會開始想像:「我們現在必須格外警惕。我們必須互相監督,以免其中一人偏離聖經道德的軌道。」我們以聖經的權威作為我們分裂出去的理由,如果我們的人不再遵從聖經,我們的存在(分裂出去)就是個騙局。
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就會造成教會中的人變得越來越互不信任、互相評判,以至於新的分裂幾乎無可避免。從古至今的教會歷史就是這種模式的見證。
解決這種情況的方法不是放棄聖經權威。我們新教徒不想放棄「唯獨聖經」,也就是以聖經作為我們信仰和實踐的準則。但聖經信仰的第一要義不是律法,而是恩典;不是順服,而是饒恕。聖經的權威不在於它的命令和教義,而在於它所帶來的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如果你的信仰從教義和倫理的要求出發,你最終會得到一個令人恐懼、不饒恕人的教會,以及一個沒人願意與之有任何關係的上帝。但是,如果你從這個奇妙的信息出發——上帝為我們這些道德淪喪的人提供一位救世主!——那麼,各種教義和倫理道德就會自然湧現出來,這些教義和倫理道德能促進自由和新生命的成長(彼前1:13-15)。
馬克·加利(Mark Galli)是《今日基督教》的資深執行主編。他是《混沌與恩典:發現聖靈解放的工作》(貝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