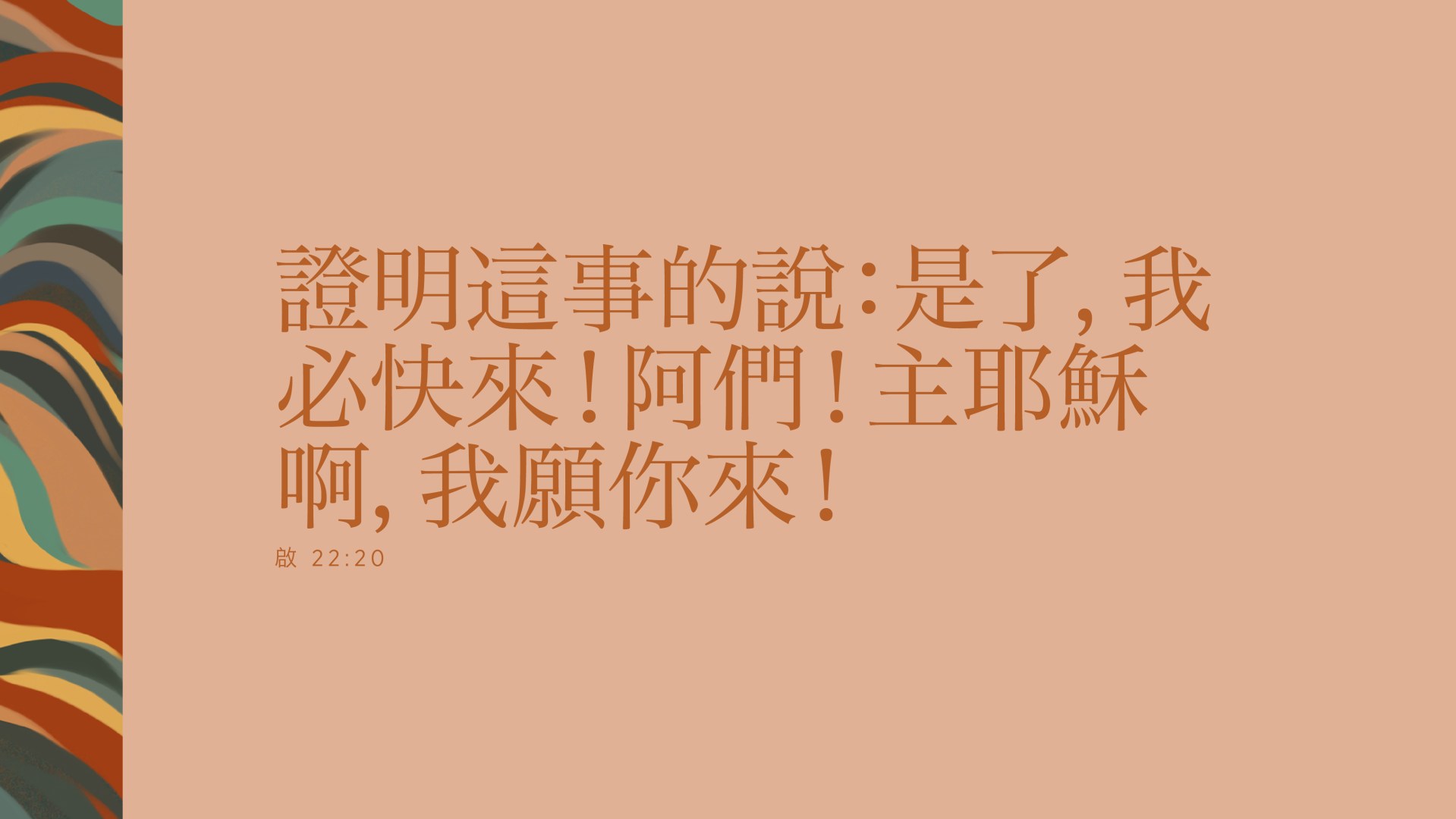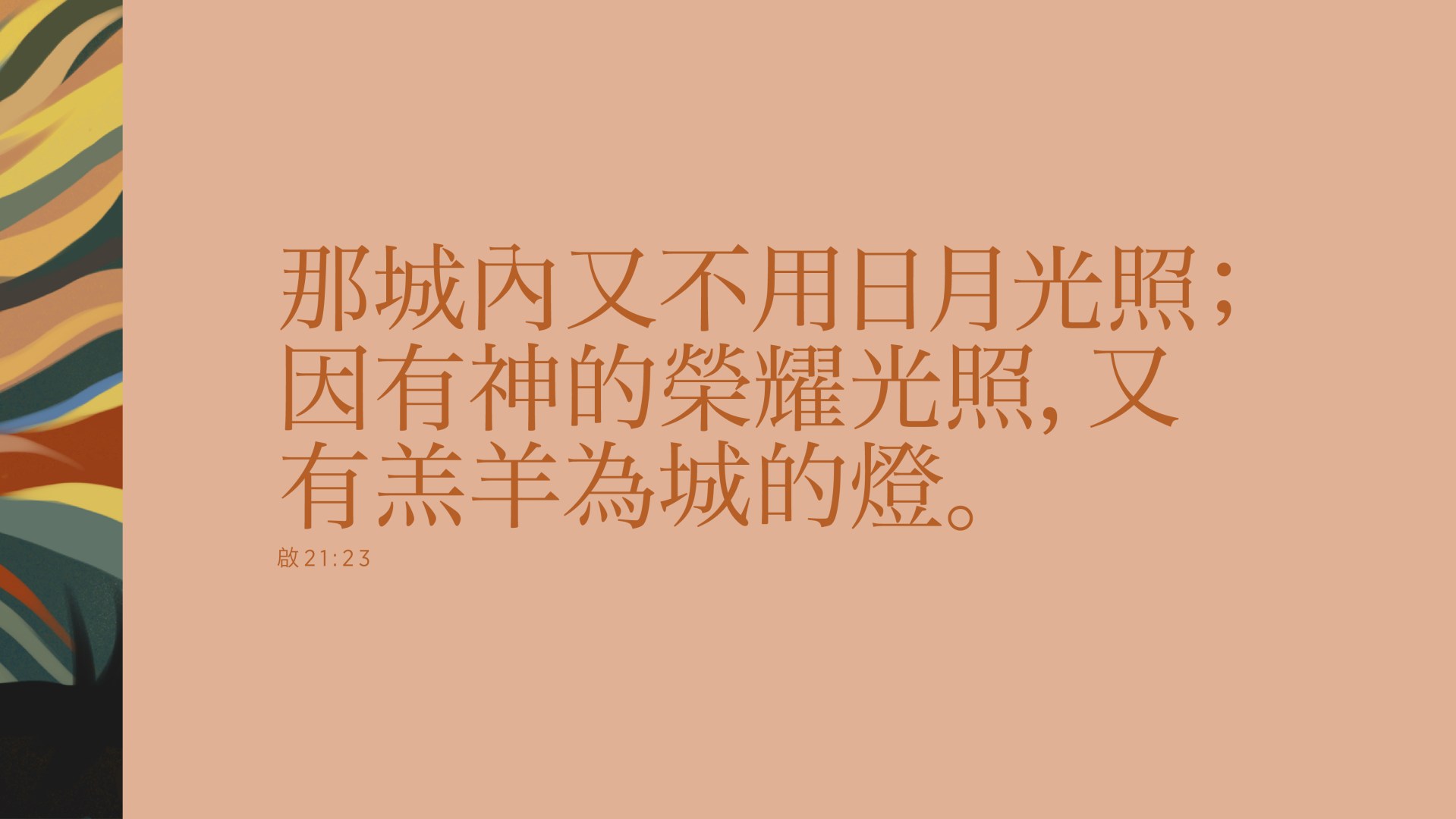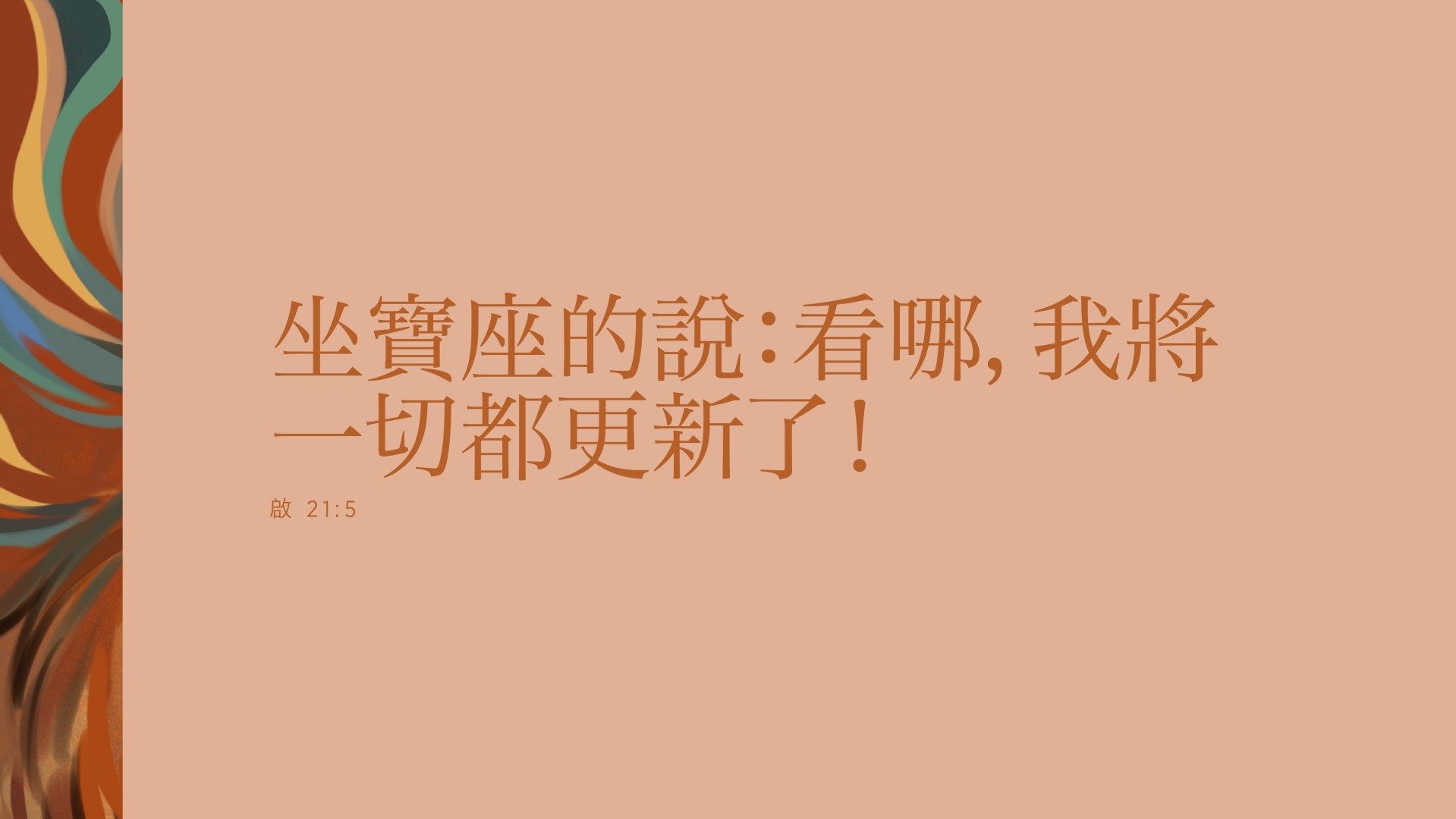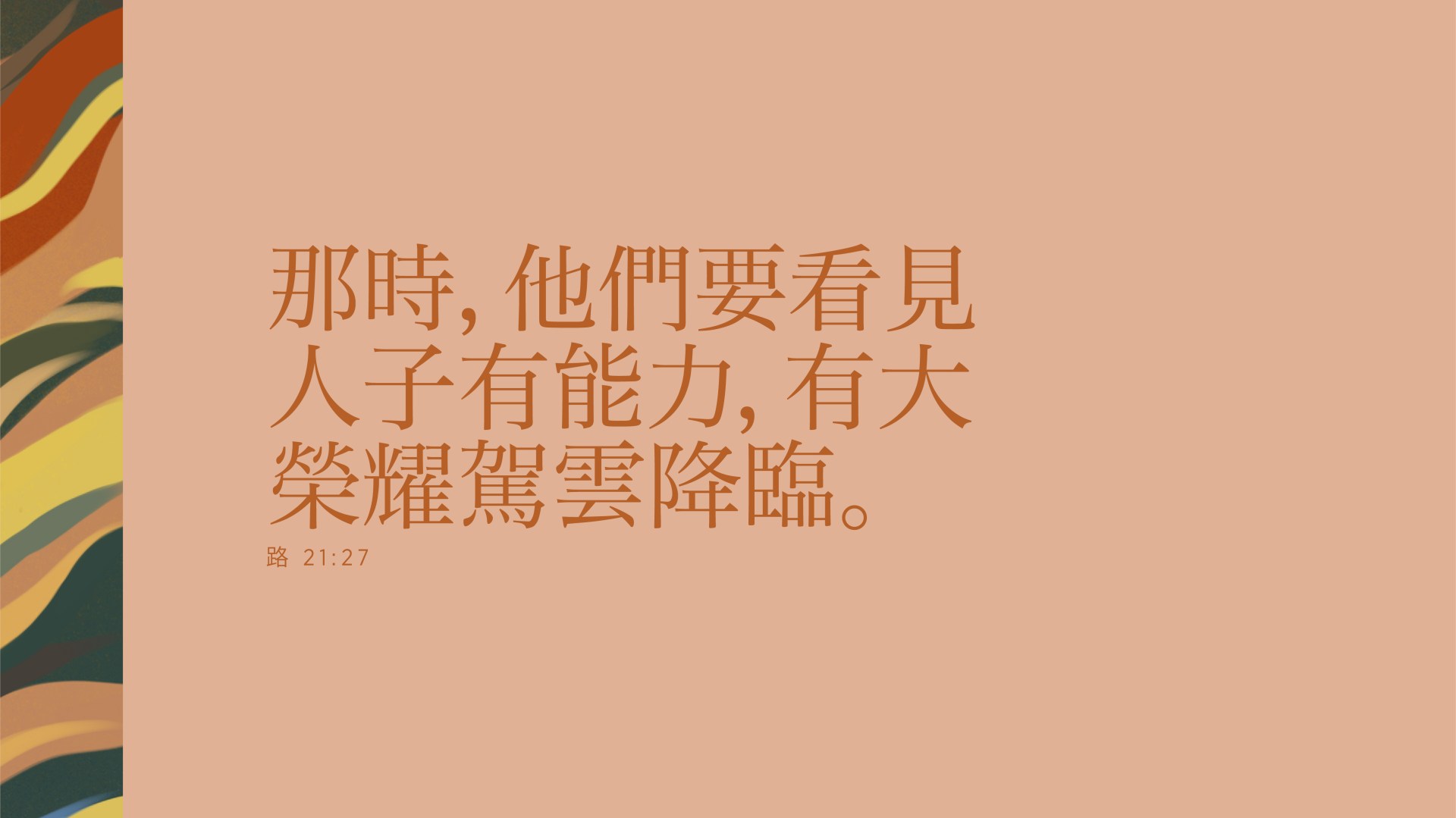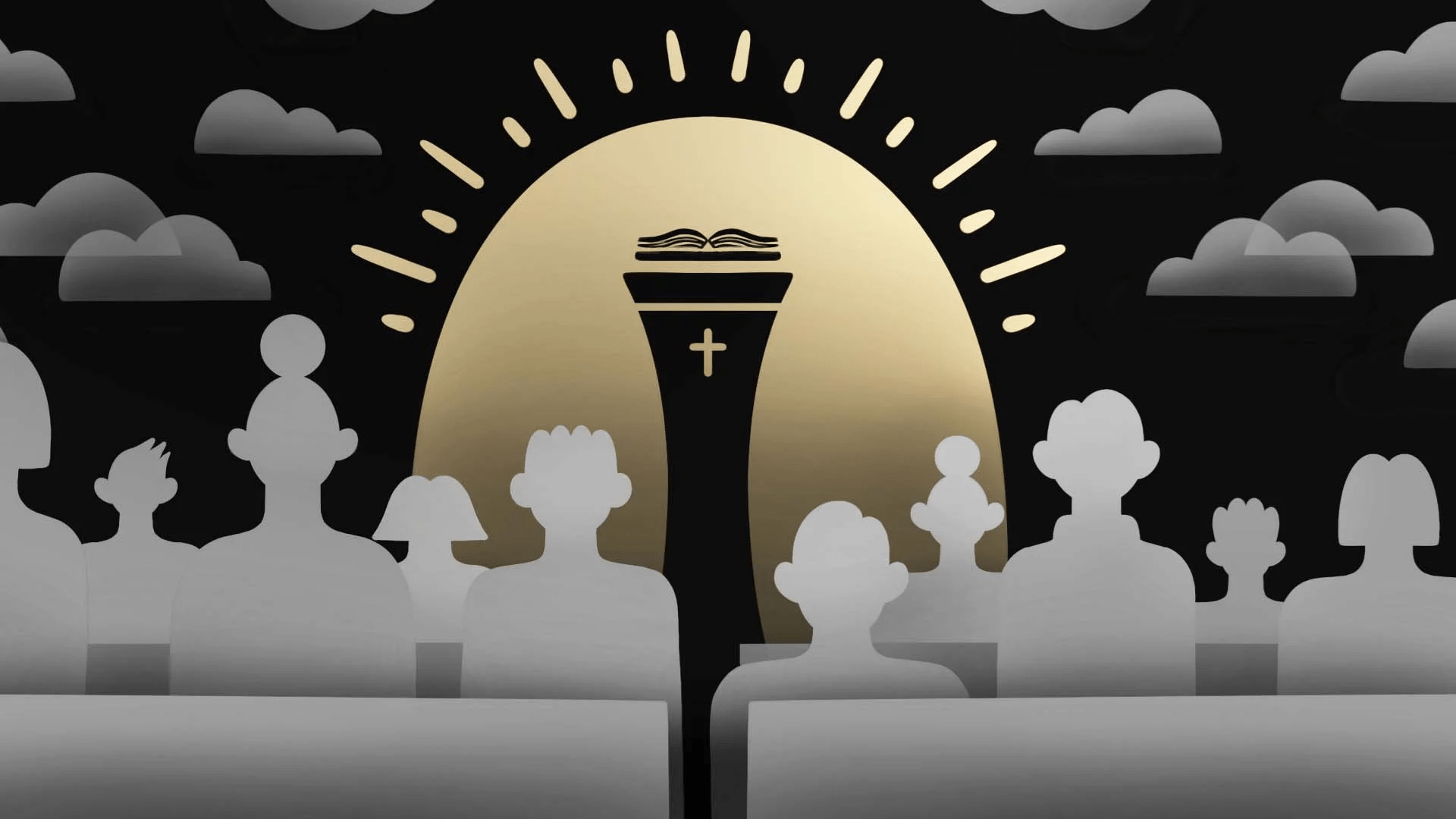閱讀:啟示錄22:12-20
《聖經》以禱告結束:“主耶穌啊,我願你來!”這樣的一個禱告與許多將臨期的讚美詩相呼應,比如《以馬內利來臨歌》(“O Come, O Come, Emmanuel”)和《我們渴望的耶穌》(“Come, Thou Long Expected Jesus”)。
基督徒從很早就開始為此祈禱。這是我們所知最古老的基督教祈禱文(除了主禱文)。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保羅曾引用過亞蘭文原文的版本,Maranatha,意思是“主必要來!”(林前16:22)。保羅既然認為哥林多教會的希臘語讀者能認出這個亞蘭文短語,就可以想見它在早期基督教崇拜中佔有的重要地位。
《啟示錄》22:20是對耶穌要再來的應許的回應。在第12節和第20節中,耶穌自己說:“我必快來。”這個應許貫穿整本《啟示錄》(見2:5, 16; 3:11; 16:15; 22:7, 12, 20),應許祂將來對一些人施行審判,為另一些人帶來祝福,直到最終這一應許得到了回應:“來!”
我們首先在第17節聽到這個回應。這是“聖靈和新婦”的禱告。說是“聖靈”的禱告,可能是指聖靈在敬拜中通過基督教先知說話。“新娘“就是教會,她加入了聖靈的祈禱。
我們可以想象新娘等待新郎到來時的樣子。她已經裝飾好、準備迎接他(見19:7-8)。但若僅是如此,說“新娘”就是“教會”還不盡然,即使“教會”確實應該如同“新娘”一般期盼、準備着主的來臨。新娘是那禱告着的教會,說著“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我們必須想象在基督教會眾崇拜中大聲朗讀《啟示錄》的情景。當朗讀者讀到下一句話時,“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啟22:17),整個會眾都同聲禱告,歡呼:“主耶穌啊,我願你來!”他們衷心的禱告表明他們真是羔羊的新娘。
但是在第17節的後半部分,“來”這個詞的用法發生了變化。現在它關於聽到的人——“每個口渴的人”,被邀請“來”,從神那裡領受“生命的水”。生命泉的水屬於新的創造(21:6)和新耶路撒冷(22:1)。但它也早已屬於那些等待着耶穌降臨的人。
就好像祂在末后降臨之前已經來到我們中間,讓我們預嘗了新的創造。因為這就是救恩的意義。我們等待祂,因為我們已經遇見過祂。
理查德·包衡(Richard Bauckham)是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退休聖經教授,著述頗豐,包括《啟示錄中的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