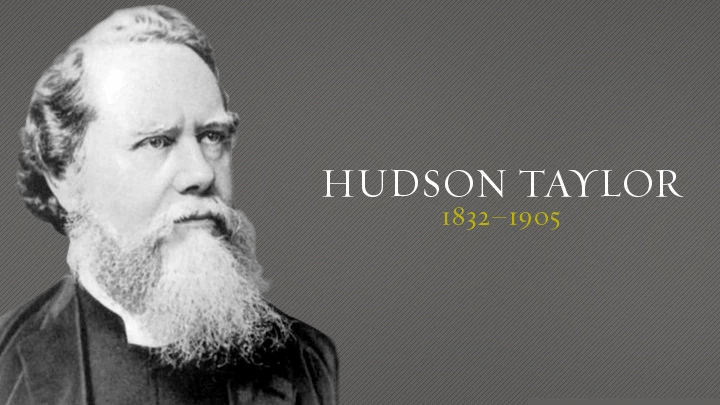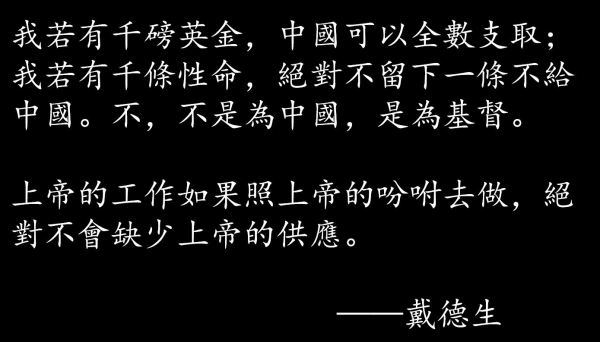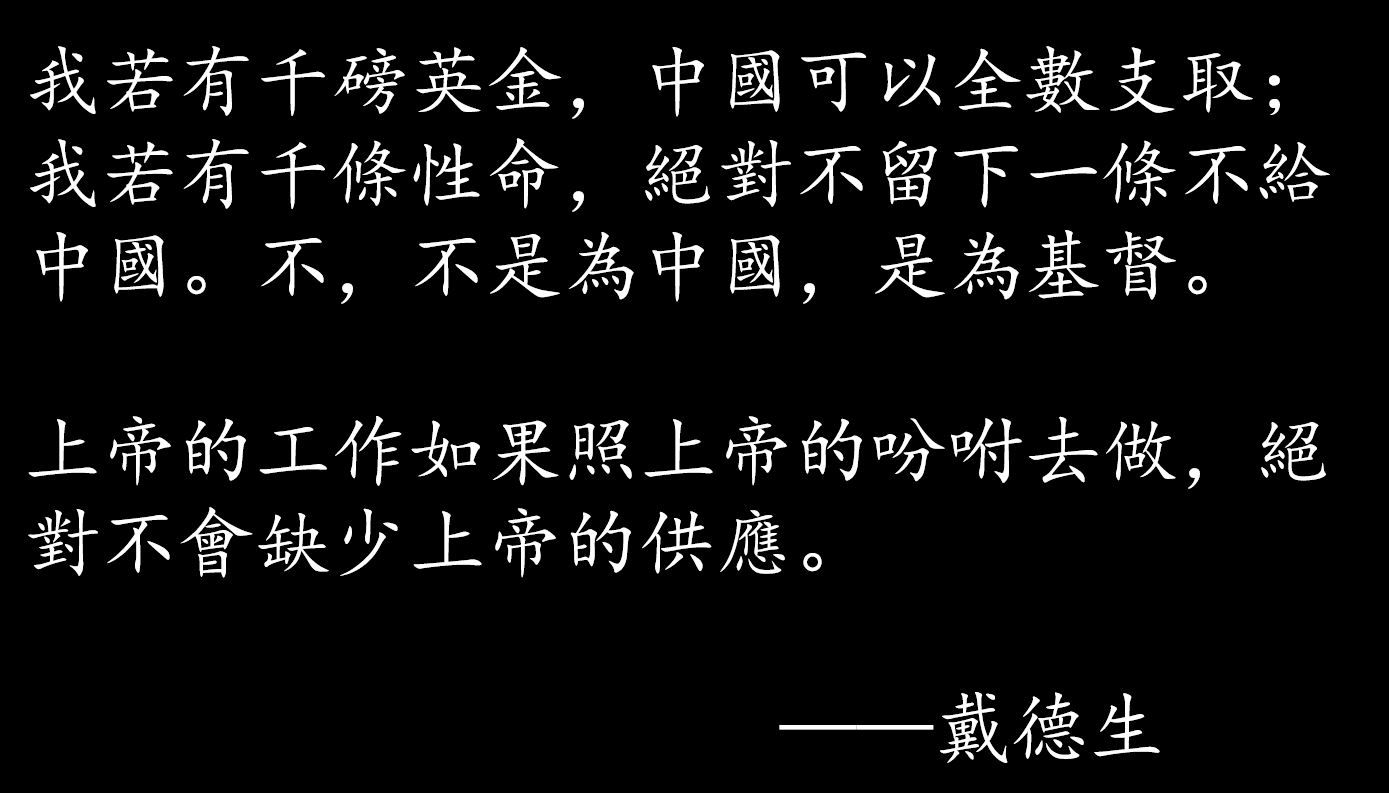最近,我的一個學生問我教神學多久了。 “十年,” 我說。但當我回到辦公桌前時,一個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經過這十年後我給學生留下了什麼?
在我自我中心的想像裡,我認為我是賦予學生滿車知識的人。但事實上,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將我的學生送進入現代事工風雨如磐的大海前,把教會歷史所傳下來豐富且通得過時間考驗的智慧交給了他們。
我教書的時間越長,就越能認同 C. S. Lewis 的訓誡:“現代教育者的任務不是在於砍伐叢林,而是要灌溉沙漠。” 然而,在神學院教育領域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沙漠,尤其是在整合大量基督教偉大的傳統方面。
多年前,作為新教神學院的一名神學博士生,我收到了一份必讀清單。在128本書中,只有三本 (!) 是出自現代化之前的作者(寫於1世紀至15世紀)。
甚至當我因學位研究需求要跨入歷史時,研討會也是從教父時代直接跳到了宗教改革時代,又再直接能進入美國歷史。但因為教會歷史有一半的時間 —— 是的,一半 —— 是發生在中世紀,我的這個教育缺口就像一個大峽谷。所以我請求學校讓我做對中世紀神學和歷史的獨立研究。
那麼,神學教育到了今天有什麼改變嗎?
克里斯托弗·克利夫蘭(Christopher Cleveland)記錄了福音派神學院如何試圖用保守的神學家取代自由派,且在這個過程中 —— 由於忽視或刻意迴避 —— “ 產生了一整代對初代教父時期、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正統思想不熟悉的福音派學者” 。
作為新教徒,我們之中許多人都被教導說,基督教的一切都輝煌的始於初代教會,但隨後教會就進入了 “黑暗” 時代。慶幸的是,宗教改革家們重新點亮了燈,建立了自使徒時代以來失傳了的真正教會。
我們錯誤地認為宗教改革家追求的是完全且徹底地與過去決裂—— 一場開創了新教的反叛 — 而不是尋求去更新那唯一的、神聖的、大公的、使徒性的教會。
這種心態的實際影響很嚴重:今天大多數新教徒不知道約整整一千年間教會發生過什麼。然而他們對一件事有信心:現代化前的時代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認識,它們只會腐蝕基督教。
這是許多日常去教會的人的心態,其來源至終是從台上的講道中流傳出來。而且由於大多數牧師都在神學院接受過培訓,問題的根源往往始於新教的學術機構觀點。
福音派圈子之外的人經常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他們之中許多人就讀於世俗機構,在那裡,這種知識的斷層是無法想像的。我但願我可以說這一切只是行政上的疏忽,但事實並非如此。所有的信念畢竟都是有後果的。
那麼,我們如何改變現狀呢?答案與謙卑有關。
我們都知道魯益師 (C. S. Lewis) 的名著《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該書強調了他對正統—— 即古典基督教 —— 的堅定委身是不容改變的。
然而許多人忘記了,在這部經典的護教學書中,魯益師用了整整兩章來檢索尼西亞信經的錯綜複雜及其關於聖子永恆受生的教義。他還為基督教歷史上的一部偉大著作,東方教父亞他那修的《論道成肉身》寫了一篇序言。
魯益師建議 —— 不,甚至是懇求 —— 他那一代的現代人要閱讀更多的舊書。他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現代化前的作家沒有缺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點。但他們的盲點並不一定會跟我們的盲點一樣。
“我們誰都無法完全擺脫這種盲目性,但如果我們只閱讀現代書籍,我們肯定會增大盲點,並削弱我們對它的警惕,” 魯益師說。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幾個世紀前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腦海,而這只有通過閱讀舊書才能做到。”
例如,魯益師經常深思以上帝為中心的中世紀神學觀,他認為這是對他那個時代盛行的充滿懷疑的現代主義對世界幻滅的解藥。正如傑森·巴克斯特 (Jason Baxter) 在他最近的書中指出的那樣,魯益師認為 “他的責任不是拯救這個或那個古代作家,而是拯救漫長的中世紀的普遍智慧,然後將其白話化講給他的時代。”
在現代主義對世界幻滅的威脅下,魯益師對他那個時代“貴今賤古”的風氣沒有耐心。由於擔心這樣的懷疑主義會破壞基督教正統本身,魯益師認為這種自命不凡的態度不僅無知而且不敬虔。
而我們也應該如此。
對於自認什麼都懂的人而言,懷念傳統並不是值得吹噓的事。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需要帶著謙卑之心願意停止說話— 無論我們有多沉迷於自己的聲音,轉而聆聽。
G. K.柴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在《回到正統》裡說:“傳統拒絕屈服於那些只是碰巧遇到他們的人的小而傲慢的寡頭統治”。柴斯特頓和魯益師都呼籲他們這一代人謙卑自己,聆聽 “死者的民主”。否則,教會只會落入各種新、舊的異端。
許多我們信仰的先驅也都有類似的心態 — 包括新教改革的領袖們。
當時,羅馬教廷指責宗教改革領袖太過標歧立異,因此是異端—— 並將他們與當時的激進派混為一談。這些激進分子認為,從使徒時代直到激進分子到來前,教會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們聲稱只相信聖經,並唾棄古代思想家。激進分子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教會。
宗教改革領袖對激進分子的傲慢感到憤怒,對被誤認為是他們的一份子感到沮喪。與激進派不同的是,宗教改革領袖不是一心只想分裂教會的叛逆者或革命者 ——那些本質上的分裂主義者。打從一開始,宗教改革領袖的目的就是更新教會,他們認為羅馬教廷不能壟斷信仰的普遍性。
正如我在《作為更新的改革》中解釋的那樣,宗教改革領袖不斷的訴諸聖經,但他們通過援引過去的神學家來證明他們對聖經的解釋是正確的。聖經是他們上訴的最終法庭,但不是他們唯一的權威;他們相信教會需要對信經負責。這些信經保守了教會忠於聖經本身的見證。
雖然他們在救恩和聖禮等教義上對羅馬教廷表達嚴厲的指責,但他們也對羅馬教廷許多其他的教義表示同意。若非如此,他們的正統觀念也會令人質疑,因此而更加證實教廷對他們的指控。
研究宗教改革的專家理查德・穆勒 (Richard Muller) 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宗教改革家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義。”
雖然救恩論和教會論等教義需要認真糾正。然而,作為基督教核心的教義 “上帝、三位一體、創造、天意、預定論和末世論在被權威的宗教改革家所接管後,幾乎沒有改變,” 穆勒說。幾乎沒有改變 —— 真正的新教教會能站立起來嗎?
新教教父們不僅繼續擷取初代教父的神學,而且他們受惠於包括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在內的中世紀經院學者遠比人們認為的還要多。
在教會歷史上,很少有神學家能像阿奎那那樣,將關於上帝和基督的正統且符合聖經教導的教義長遠延續下去。
正因如此,我經常在我任教的福音派神學院的三位一體論課程中提到阿奎那。每年,學生們都興奮地向我報告他們有些諷刺的發現:他們發現阿奎那在三位一體論上比一些當代福音派更正統。
但有一天下午我走進教室,發現講台上有一個巨大的念珠、十字架和這一類的東西 —— 上面寫著 “給巴雷特教授” 的字條。這想傳達的信息很明顯:會把阿奎那的書指派為教科書的教授一定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如果不是因為替這個匿名的學生感到難過,我會笑出來的。作為新教徒,我們是否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於我們無法受益於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其中一位思想家 —— 尤其是在像三位一體論這樣重要的教義上 —— 僅僅因為我們可能會在救恩論和教會論上不同意他的觀點?
甚至宗教改革先輩們在他們的新教信仰中也有足夠的信心在無數領域使用阿奎那的神學 —— 從釋經學到上帝的屬性,從三位一體論到倫理學和末世論。改革宗神學家不僅用阿奎那反對羅馬天主教徒,而且邁克爾・霍頓 (Michael Horton) 也證實,宗教改革先輩中的許多人甚至比他們的對手更加的是托馬斯主義(Thomistic)的跟從者。
那些避開阿奎那的現代福音派神學家通常會借鑒清教徒思想家約翰·歐文 (John Owen) 等新教經院哲學。然而,新教經院的研究方法和神學之所以忠實於聖經正統正是因為他們是阿奎那的學生。
他們之間的關聯是如此無法反駁,以至於福音派出版商 Crossway將要出版《為新教徒編寫的阿奎那合輯》套書 —— 由一群新教作者團隊聯合撰寫。
歸根究底,我們並不打算供奉阿奎那或任何其他思想家。相反,當阿奎那揭示他那跨越時代、卓越的思想時,我們將批判性地但謙卑地聆聽,這些思想有助於我們在這逐漸幻滅的世界中重新找到上帝永恆的良善、真理和美麗。
福音派,有著所有現代文化的傾向,經常喜歡充當法官,將基督教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區分開來—— 只為了尊崇前者而消滅後者。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會無情的偶像化和抹黑歷史人物。
這種心態不僅助長了分裂的宗派主義 —— 除了我們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教會 —— 並且缺乏同理心。我們無法理解過去的人、運動、機構和整個時代的複雜性,更不用說從中學習了。在這種論斷主義背後隱藏著我們自己的不安全感、暗藏的議題和派系思想。
俗話說,人們總是對其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懼。這種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被掩飾在敵意的言辭中,轉化到未來的教會領袖的課堂上,再進一步影響平信徒。
我最近與一位對今天的福音派深感灰心的年輕人進行了交談 —— 因為福音派轉變為原教旨主義者,對所有現代化之前的事漠不關心或抱持懷疑 —— 他想知道福音派教會是否還有任何真正的歷史根源可以提供。
如果今天的福音派領袖不能追隨他們新教先祖的帶領,去擁有那大公的教會 ,下一代會去尋找一個能如此做到的教會。
雖然改變路線絕非易事,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從魯益師開出的治療方法開始,透過閱讀讓正統的乾淨海風吹過我們的腦海。
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是《簡單的三位一體:不受控制的父、子和聖靈》的作者,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神學副教授,以及《信條》播客的主持人。
翻譯: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