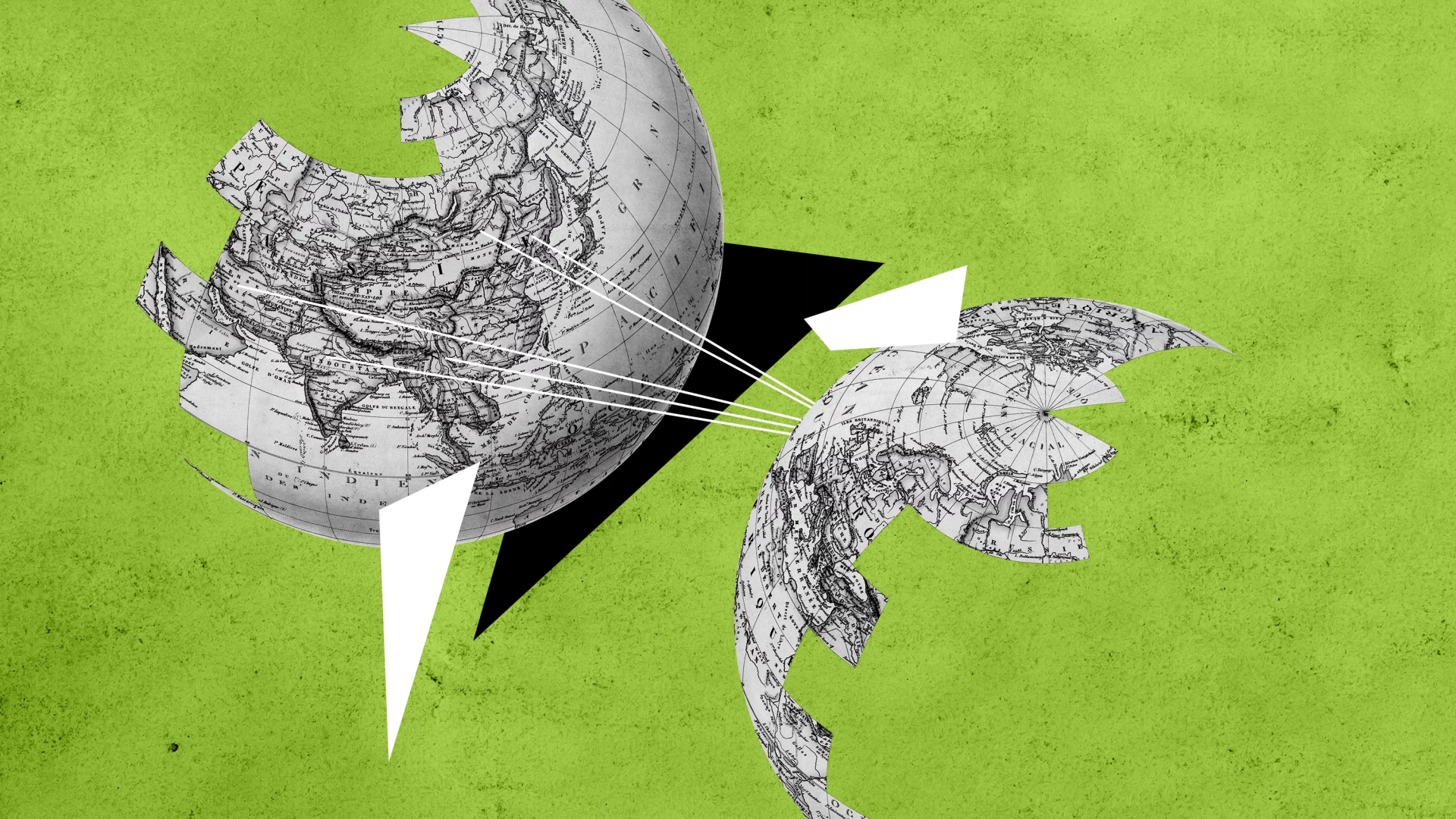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況遠去,以及世俗和宗教領袖皆呼籲民權和結束白人統治,全球對種族的看法開始改變。 雖然歷史學家在敘述美國民權運動時通常很少提及更廣闊世界中的事件,但這一時期的宗教和世俗領導人卻是將該運動放在更大的、反對全球種族主義的運動中來理解的。
種族優越感在整個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白人的殖民統治也被視為種族主義世界觀的體現。 1942年,一個新教領導人的合唱團開始呼籲“在各地和全地的種族平等”。 1947年,戰爭結束兩年後,路德派神學家奧托·弗雷德里克·諾爾德(Otto Frederick Nolde)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張全球種族平等,並呼籲教會引領潮流。
基督教的福音事關所有人,不分種族、語言或膚色。 … 支持某個種族自以為是的內在優越性是沒有任何基督教依據的。 所有土地上所有人的權利都應得到承認和保障。 我們需要國際合作來創造條件,使上述種種自由成為現實。
追求種族平等是“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獲得自由這一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1948年,全球社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這是世界範圍內反對種族主義鬥爭的一個分水嶺。 美國新教傳教士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行文措辭有很大影響,他們還是宗教自由以及全球人權的積極支持者。 那時西方世界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而傳教士正在幫助引領這一方向。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許是最著名的美國民權活動家,而將其理解為呼籲結束全球種族主義和白人壓迫的先驅更為恰當。 雖然杜波依斯是無神論者,但在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時,他與西方傳教士通力協作,他也表示了他相信西方傳教士在結束全球種族主義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種族主義仍然是一種可接受的過失,甚至在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中也是如此。 在20世紀上半葉,像“色條問題”(problem of the color bar)在一些基督教傳教會中就是個問題。
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研究了非洲大陸20世紀最大的新教傳教機構的組織。 它在如何處理1950年代的種族融合問題上就陷入了混亂。 它的一些傳教士建議它可接受 “有色族裔的福音派”作為傳教團體的正式成員,而管理層對此表示反對。 其總部的行政人員在積極探索(主要是在閉門會議上),如何解決同工同酬的問題;如何解決美國黑人傳教士的孩子想和他們白人同事的孩子一起上學時,可能出現的問題。 而該傳教團體當局建議,也許他們可以在非洲建立單獨的傳教站,“完全由黑人擔任工作人員”。
由此可見,一些傳教士在努力改變國外的種族主義態度,而另外一些則對組織內部既有的態度保持克制。 但當我駐足探索那些塵封的檔案時,我愈加意識到:不論一些傳教士和 傳教會有多麼試圖只專註於福音宣揚這項主要工作,對全球人權和白人統治議題的這些不斷變化的態度,始終是他們的危機。
舉個我最熟悉的傳教團為例,在20世紀50年代的茂茂衝突(Mau Mau Conflict,約1952-56年)期間,由於民族主義和反白人情緒的上升,它被迫重新定位。 當時,席捲非洲大陸的變化造就了將社會所有領域(包括教會)“非洲化 ”的政治壓力。 在肯尼亞脫離英國獨立后的十年裡(獨立的要求大約始於1958年,並於1963年宣布獨立),非洲教會領袖向全白人傳教團要求和平移交其財產和權力,但傳教團一開始頂住壓力拒絕了。 儘管有其他方面的保障,但傳教士們擔心他們會持續受到壓力而離開肯尼亞(從而結束他們的工作)。
在非洲教會領導人威脅要進行強行接收后,該傳教團終於在1970年代放棄了其權力。不過直到1980年,那位非洲教會堅定的主教實在厭煩了“傳教團駐地心態”,在他的強烈要求,移交才真正完成。 (傳教團駐地心態指的是傳教士未能與非洲教會完全 “融合”。)白人的外來控制——無論是在國家、教會還是傳教會——都與時代脫節。 即使有些傳教組織沒有完全適應非殖民化帶來的時代變化,也不得不進行調整。
對於從事世界宣教的西方基督徒來說,重要的是要理解所有形式的白人至上主義已經被非西方世界所拒絕。 在20世紀後期,在非西方世界服務的傳教士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全球性的情緒。 在20世紀下半葉的整個非洲大陸,殖民地在爭取人類自由和結束全球種族主義的鼓舞下,反叛了他們的西方主人。 隨着前殖民地的獨立,來自各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傳教士被迫放棄了教會權力。
各宗派“從傳教到教會”的過渡(被稱為“移交”)往往是緊張的和不平衡的。 傳教士圈子裡的進步聲音呼籲儘快下放權力。 例如,從1936年至1942年擔任劍橋大學聖三一教堂的牧師,從1942年至1963年又擔任教會傳教士協會總書記的馬克斯·沃倫(Max Warren,1904-77),就極具說服力,他在倡導全球宣教界適應非殖民化的全球浪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大多數情況下,傳教士和傳教團體由於擔心被可能敵視西方工作者的新政府驅逐(如1949年在中國和1960年在比屬剛果),他們往往迅速作出反應,儘快為當地領導人準備好(教會的)權威職位。
在允許傳教社團繼續工作的新獨立國家,傳教士有時擔心會被認為是反政府甚至是種族主義者,不得不放棄對教會的控制。 南非的情況甚至更加複雜,教會和國家在私人和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1994年)后,種族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中國和印度,由於反西方情緒的影響,大多數西方傳教士在1950年就已經迫於壓力回國了,傳教團體別無選擇,只能將教會的領導權交給本土領導人。 在拉丁美洲,雖然各國在一個多世紀前就經歷了政治自由,但在20世紀中葉,人們對教會等級制度所表現出的精英主義的失望情緒不斷上升。
基督教領袖,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通過支持解放神學來表達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聲援。 這種形式的神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出埃及記》的主題,認為上帝的使命是讓他的人民在精神 和 政治上同時獲得自由。 解放神學的話語體系往往是反西方的,解放神學部分批評亦指向那些被視為新殖民主義的西方傳教士。 從20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傳教士團體迫於壓力都得適應他們周圍迅速變化的世界。 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形式的 “白人統治 ”都被拒絕。
2006年在肯尼亞休安息假期間,我了解到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發展,也了解到非西方基督徒對西方傳教士的很多看法。 我在肯尼亞時進行的一個研究項目表明,非洲人不僅對西方控制和種族主義的遺產感到不滿(這並不令我吃驚),而且他們還認為傳教士團體表現出文化和種族優越性。 許多非洲人認為,西方傳教士不願意為當地領教會領袖提供充分的牧養方面的準備,是文化和種族優越感的表現。
那年,我在內羅畢福音神學院(Nairobi Evangelical School of Theology)的教會歷史系講課時,一位來自烏坎巴尼(Ukambani,肯尼亞Machakos附近)的牧師在一天晚上來到我的小屋,送來一本喬·德·格拉夫特的文學名作 《蒙圖》。 這部非洲戲劇於1975年在內羅畢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聚會上演出,現在被認為是非洲文學的經典。
在劇中,當非洲的兒女們正在為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務而相互爭吵時,水路來人(Waterpeople)到了這裡。 “第一個水路來人”是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他來到非洲佈道;第二個是名商人,他設立了一個買賣商店;第三人是一名尋找土地的白人定居者;第四人是一名殖民者,計劃建造一條出口黃金的鐵路。
這些水路來人揮舞着火槍,甚至連傳教士都無疑是個厲害的射手。 遞給我劇本的非洲牧師解釋說,德格拉夫特的作品將幫助我了解許多非洲人的心態,尤其是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我了解到,非洲的基督徒記得西方的傳教士、定居者、商人和殖民者一起到達,往往是在同一艘船上。 他告訴我,一些更具辨識力的基督徒明白,傳教士有不同的目的。 然而,他也說,對於我而言關鍵是得明白新一代的非洲領導人已經出現,他們不會容忍任何類似於西方優越感的東西。 他希望我明白,白人統治在非西方國家的終結,也意味着白人統治在非洲教會中徹底終結了。
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希望與西方世界的教會合作,在全球宣教事業中成為福音的同工。他們也值得被西方世界作為同工來對待。 非西方世界的教會領袖敏銳地意識到他們及其祖先所承受的被征服的歷史。 他們不希望被西方教會忽視、繞過、看不起,或受其庇護,他們不希望西方教會來到他們的國家獨立開展工作,好像實際上沒有非洲、亞洲或拉丁美洲的教會存在。 他們希望西方教會與他們一起服侍,共同見證。 他們還希望西方教會領袖承認他們,尊重他們,並傾聽他們的意見。 他們希望西方基督徒首先了解他們的需要,然後來和他們一起服侍。
我們很容易把非西方世界的人們對西方遊客的友善誤認為是心甘情願的順從。 但關鍵是要明白,對北美人和歐洲人的態度在20世紀已經發生了變化,即使是好客的主人也意識到文化和種族優越感已經存在了不短的時間。
奧斯卡·穆里烏(Oscar Muriu)主教是非洲大陸上有影響力的基督教領袖,他也成了我個人的朋友。 我曾多次接受過他的盛情款待,他也不止一次到我家裡做客。 我們曾一起享用美食,一邊敞開心扉討論。 在我們最近的一次交流中,我就一個與傳教有關的問題請教他,他(再次)認為, “所有來自西方的白人 … 都夢想着要在白人世界外的其他各個角落傳教。”
我們的非西方教友希望我們參與宣教,但他們也不希望被忽視,特別是當我們在他們自己的後院計劃宣教活動時。 正如肯尼亞活動家和攝影記者博尼法斯·姆萬吉(Boniface Mwangi)在2015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意見專欄文章中所說:“如果你想來幫助我,先問問我想要什麼 …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工作。” 拯救世界不是“白人的負擔”,而是整個教會的責任,要把整個福音傳給整個世界。
改編自《世界基督教和未完成的任務》,作者為里奧奈爾·楊(F. Lionel Young III)。 經Wipf and Stock出版公司許可使用,www.wipfandstock.com。
翻譯:黃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