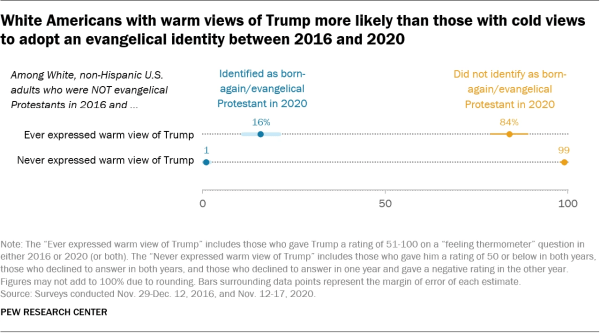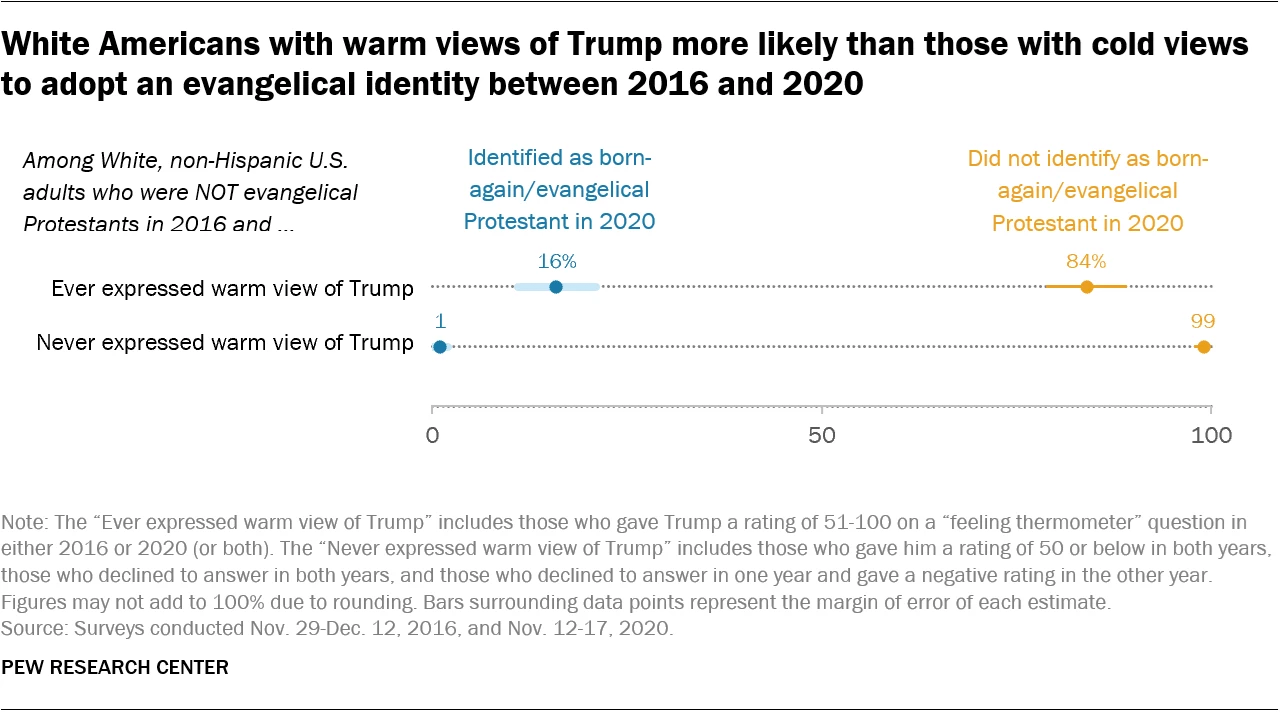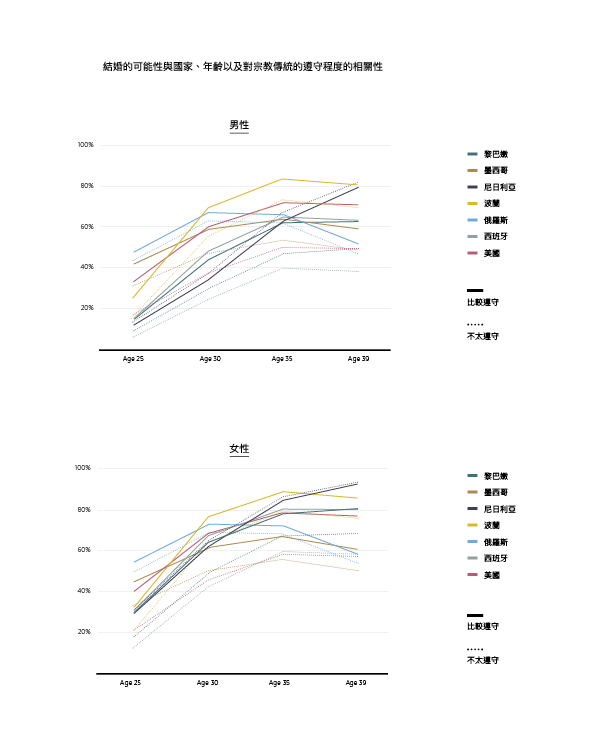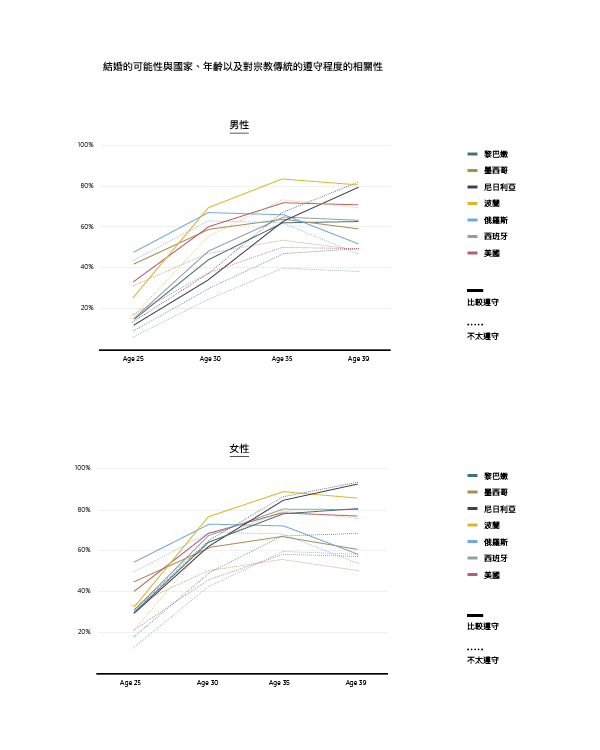本周,羅伯特·李(Robert E. Lee )終於從里士滿撤走了。 里士滿紀念碑大道上這位聯邦將軍的雕像被從基座上移走,該市的市民在街上歡呼。 看着吊在空中的花崗岩灰色戰馬,促使我想到我曾經有過的一次談話,是關於神學院寢室里一張李的照片是該留還是該拿掉。
一個學生曾寫信給我,詢問關於他擁有的一幅李的畫 —— 我相信這幅畫是一份家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甚至可能與李本人有家族關係。 他說,一位非裔美國人神學院同學,在神學院公寓的走廊上看到這幅畫時,皺起了眉頭。
這位南方的白人學生問我:“我應該把它拿下來嗎?”我回答說,應該。然後我給出了符合《聖經》和歷史的理由,說明我為什麼認為李和其他邦聯領導人不值得尊敬。
不過有一個人,我想徵求他的意見,那就是肯塔基州亨利郡的吟遊詩人: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
大約在我給這位學生髮送回復的時候,我正在這位詩人兼小說家的農場。在他的廚房桌前,我尷尬地提起了李的話題。 我說“尷尬”,是因為我很確定貝里會不同意我的建議。 畢竟,我剛剛讀過他為李做的辯護。我相信他一定會認為這幅畫的移除是又一個例子,顯示一個流動、無根的現代社會甚至拒絕記住過去。
然而,除了那篇短文之外,我真的沒有理由去猜測他的反應。 畢竟,雖然貝里是一位農耕作家,但明顯不屬於“月光和木蘭花”(moonlight and magnolias)型的南方農耕主義那種。後者往好里說是粉飾,往壞里說,是浪漫化南方舊時(old Dixie)暴力性的白人至上主義的種姓制度。 恰恰相反,他寫下了關於白人至上主義的“隱性傷口”及其所造成傷害的深刻文章。
不過,我還是發現作者在1970年代關於李的文章立場前後不一致。 他把這位將軍描繪成一個在原則和社區之間面臨選擇的典範。當時他辭去了美國陸軍的軍職,加入了南方邦聯的事業。 在貝里看來,李的動機不是捍衛奴隸制,而是拒絕對他的親屬和弗吉尼亞家園開戰。 作者的結論是,將軍是對的。
“作為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貝里在談到李時寫道,“他不能放棄自己原則的基礎。 由於他致力於這一基礎,他把對在自己所在地區復興原則的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在我看來,他的選擇是一個堪稱典範的美國選擇,它將傑斐遜式的紮根於社區和祖國的願景,置於抽象的‘美國公民的忠誠和義務感’之上。”
在我看來,貝瑞是對的,道德最好建立在他所說的“成員資格”上,而不是抽象概念。 但他錯誤的地方,在於怎麼看這個成員資格的界限。 李為之奮鬥保存的那種邪惡,正是這樣一個社區,在這個社區里,一些人被看作是成員,而另一些人則被看作是可以被剝削和折磨的財產。
李在這個故事中的位置,可以從他決定拿起武器反對聯邦、捍衛奴隸制度中看出。 但更明顯的是,這樣做,他的形象已經成為白人反對黑人民權的 “失落事業(Lost Cause)”的偶像。
在2017年的“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集會上,白人民族主義者湧入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的原因,就是為了南方邦聯的紀念碑。 那些舉着提基(tiki)火把的人的動機不是為了拓寬社區的視野,而是為了限制它。 “你們不會取代我們;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他們高呼。 “我們”這個詞的定義是關鍵。
相比之下,基督教對於成員資格的看法是對“血與土”(blood and soil)這種“社區高於原則”的觀念的否定。 它不是用一套 脫離 社區的原則,而是用一種全新的社區意識來代替。
在家鄉的會堂里宣布他的事工后,耶穌的第一個行動是重新定義社區,使其包括外邦人——撒勒法的寡婦,甚至包括可怕的敘利亞人,如勇士乃縵(路4:25-27)。 在短期內,這個決定使社區分裂,因為“怒氣滿胸”,他們想把他推下懸崖(28-29節)。
但這種分裂是必要的,因為在這個王國里,“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3:11)。
當西門彼得拒絕與加拉太的外邦人一起吃飯時,他可能認為他是在選擇社區而不是原則,因為與那群人一起吃飯會冒犯他自己的猶太民族。 但實際上,他的行為“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加2:14)——不僅背叛了基督教的原則,而且背叛了由聖靈排除萬難,通過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定義為兄弟姐妹而組成的社區。
在他作品的其他地方,貝里完全理解並預言性地設想了那種有原則的社區。 例如,他寫道,煤炭之鄉的人們勇敢地站起來——有時是獨自站起來——抵制山體剝離式開採和其他破壞生態的活動。 他指出,變化往往來自於邊際人群,即那些來自於那些遠離既定正統觀念(即既定社區)的人,他們帶來對其它未來可能性的重新認識。
在這種情況下,推崇羅伯特·李的神話就是聲稱自己是“失落事業”的成員。 但這也是拒絕加入一個更廣泛、更豐富的社區——在其中,當一個人被殘害、被強姦、被綁架、被奴役或被處以私刑時,社區整體都會受到傷害。
當我向貝里詢問李的照片時,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談論其他相關問題,直到談話內容遠離學生關於肖像的問題。 很快,我們就開始談論其他各種問題。 但當我準備離開時,這位雜文作家俯身說:“我會把那張照片拿下來;你不會嗎?”
他那次是對的。 我希望,當貝里看到一個城市擺脫了曾用於傷害他人的紀念碑時,他將看到的那些歡呼的人群——黑人、白人、亞裔和西裔——視為他一直以來所希望的那樣:同一個社區。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一位公共神學家,也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學項目的主任。
翻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