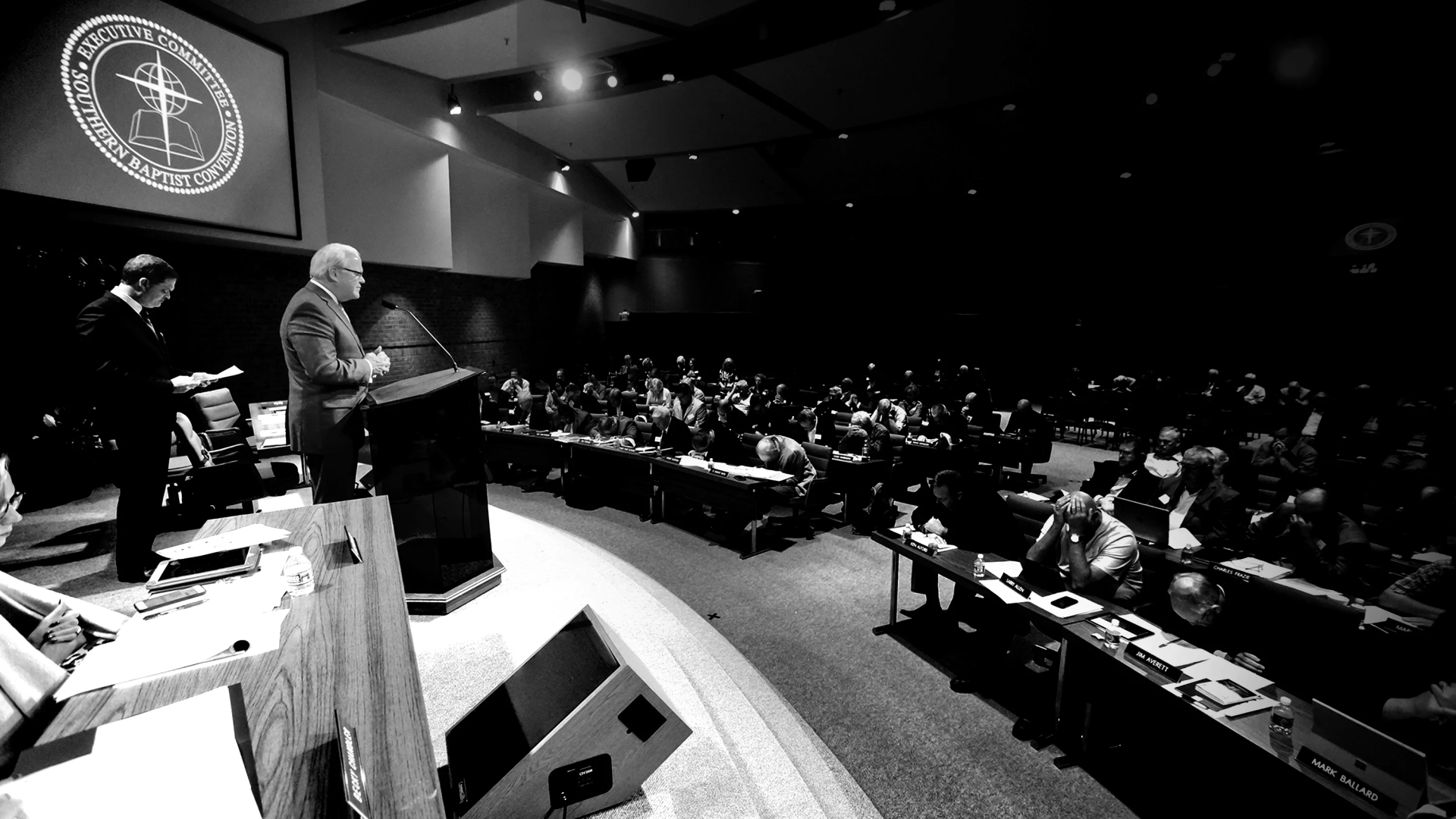戈登·康威爾神學院 正在出售其主校區——這個我居住和讀書的地方——在過去10年裡,他們的招生人數持續下降了50%以上。
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繼續認定自己為福音派,他們的神學院衰落的原因似乎成了一個謎。一種解釋是一些福音派人士認為神學院是一個障礙,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必要的障礙。
在我大一和大二之間的暑假,我被邀請參加當地一個剛植堂的教會的周一晨會。他們的士氣很高漲,因為他們的主日崇拜的出席率剛剛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他們翻看來訪者的卡片,驚訝地表示,剛植堂一年,這已經是他們 “最成功的主日”。
作為一個年輕的、有抱負的牧師,我對教會如何跟蹤和衡量進展感到好奇。因此,我問:“你們怎麼知道這是一件好事?” 牧師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嗯,只要健康的東西就會成長。這就是我們的哲學。”
如果這個人是對的,那麼人數增加無疑總是教會靈命成長的標誌,那麼我們不妨認為戈登·康維爾正在走向墳墓。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一件事的屬靈價值不能用Excel表格來決定,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和決定何為成長和復興。相反,我們需要一個古老的框架——一個將死亡轉為生命,敗局轉為勝利的十字架。
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可能在招生和預算方面都在緊縮,但它仍然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地方,在那裡靈魂會變得專註,靈命變得活潑。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神學院繼續做好他們的工作,來提醒我們計算器無法解釋的奧秘。
長期以來,神學院一直被理解為培育牧師的地方。我現在在讀道學碩士,按計劃一旦你完成道學碩士這一步,你就能成為牧師。但事實上,現在的福音派教會已經越來越不關心這一步了,所以有抱負的牧師們被告知,讀神學院是沒必要的,甚至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
我自己也得到過這樣的建議,其論點通常是這樣的:“何必要讀神學院?這在經濟上是不負責任的,你有精神耗盡的風險,要吃很多苦的。”是的,這些都是很好的觀點。但是,如果這些成為你的做決定的關鍵,我必須問,你為什麼要追求全職服事?
如果你希望一生都在事奉中,委身於三年的全日制神學院課程是完全合乎期望的。想想醫生或者律師,你不會讓一個自學成才的醫生鋸掉你的腿。同樣地,神學院是一種正式化你的呼召的手段,也表達了你對你的業務水平的委身。但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你一生蒙召成為牧師的獻身和忍耐的軌跡。
然而,在福音派的世界里,當一些人談到對牧師接受正式培訓的期望時,他們的態度是變得越來越不堅持,越來越不冷不熱。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呼籲警惕這個問題的時候說到:
“很簡單,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相信一個訓練不足的牧師會損害他們的救贖;但人們確實相信一個訓練不足的醫生會傷害他們。因此,人們更關心誰是他們的醫生,而不是誰是他們的牧師。當然,這種情況表明,無論我們自己如何地認為自己是認真的基督徒,我們也完全有可能同時過一種背叛我們的信念的生活,背叛‘神對我們是至關重要的’這個信念。”
現在,在神學院之外獲得牧師的初等知識和技能並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上已經有人做到了。但信息時代帶來的便利並不足以證明正規的神學教育是無用的。即使是市場上最好的聖經參考工具也不能提供與神學院學位相同的全面的培訓。不僅如此,自學也不會有對等的時間和金錢的犧牲。
雖然人們對於參與更多非正式神學培訓的興趣增加是一件好事的,也是教會所需要的,但它不能取代合格的神學院所提供的:一種可靠和全面的方法來確保一定程度的能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堅定一個牧師的獻身。
全職侍奉這個呼召沒有捷徑,即使是那些沒有上過神學院的人也是如此。為牧師做準備需要大量的學習和靈性操練。對於那些有條件的人來說,神學院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可以做到這一點。正如澤娜·希茨(Zena Hitz)所堅持的,“智力工作所需要的專門的退修去委身”,這不一定是一種逃避,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創造 “有益的距離,一個可以把我們私人的議程放在一邊,考慮屬靈世界真實的地方。”
說到底,神學院是一個獨特的靈性成長機會。它提供了所需的空間和時間,讓我們能夠深入專註和培養深刻的不被打擾的能力,而這是正常生活通常無法提供的——讓神學生有機會在一個受到鼓勵的環境中“恐懼戰兢”地做成信仰的工夫。
對一些人來說,許多學生在神學院里所經歷的屬靈考驗和信仰危機可能被認為是挫折,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最終目標的實現。但是,一個人並不能通過逃避(神學院)可能導致自己變得憤世嫉俗的環境,來避免自己變得心灰意懶。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牧師的工作不是躡手躡腳地躲避苦難和懷疑,而是用恆切禱告走過苦難和懷疑。
這項工作從牧師自己開始,從他們面對自己的包袱時開始。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惡魔》中的名言所說: “如果你想戰勝整個世界,就要戰勝自己”。因此,對於牧師來說,如果你想照顧你的羊群,就要照顧你的靈魂。在漫長的學習時間裡照顧好它。當受到疏離和驕傲的試探時,要與神摔跤。你的事工將永遠從這裡開始:面對試探,與神摔跤。
就像保羅對提摩太的指示一樣,牧師們必須準備好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準備在人生的每個季節奉獻自己。中世紀天主教神學家克萊爾沃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 區分了運河和水庫的差別,前者是 “把收到的東西倒出來”,後者是 “把滿溢出來的東西排出去,但自己卻並無損失”。他觀察到,“水庫”在他那個時代的教會中 “太罕見了”。今天的教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20世紀的法國激進主義者、哲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在她的《等待上帝》一書中認為,“做基督教研究的關鍵概念是認識到祈禱必須專註。”她認為,在一個人的學習中(無論是數學還是神學)學會關注,本質上是對祈禱的操練。畢竟,如果沒有專註的能力,你怎麼能“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馬太福音6:6)
我們來到神學院不是為了“效法這個世界”,而是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2,NRSV)。通過這項更新的工作,牧師們如黎明興起,不為滿足世界和它的成功標準,而為帶領教會和上帝的子民走基督的道路。
神學院是一個學習放下生活中的一些東西和“成長”的地方。正是在這一自我衰微的任務中,我們才有機會發現上帝轉化一切的榮耀。這個作為人生中一段插曲的季節不是一項要完成的任務,而是一個目的地。這就是為什麼神學院不僅僅是一種手段;它也是目的本身。
如果有人預測戈登-康威爾和其他福音派神學院都終將關門,那是他的自由。但我們仍然會在這裡——寫我們的論文,愛我們的鄰舍,並等待上帝。
Noah Karger是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博士生和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
翻譯:伊莎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