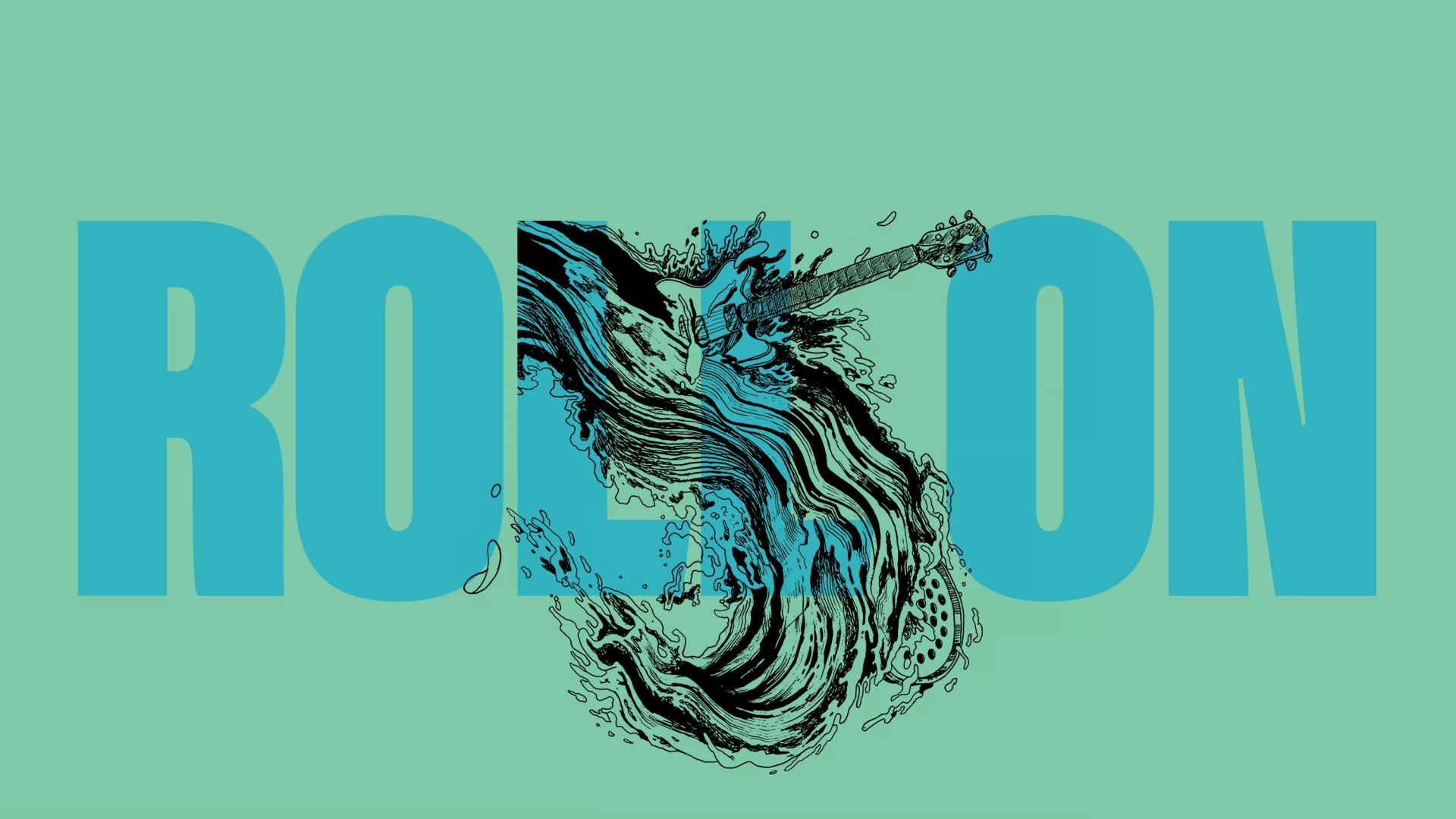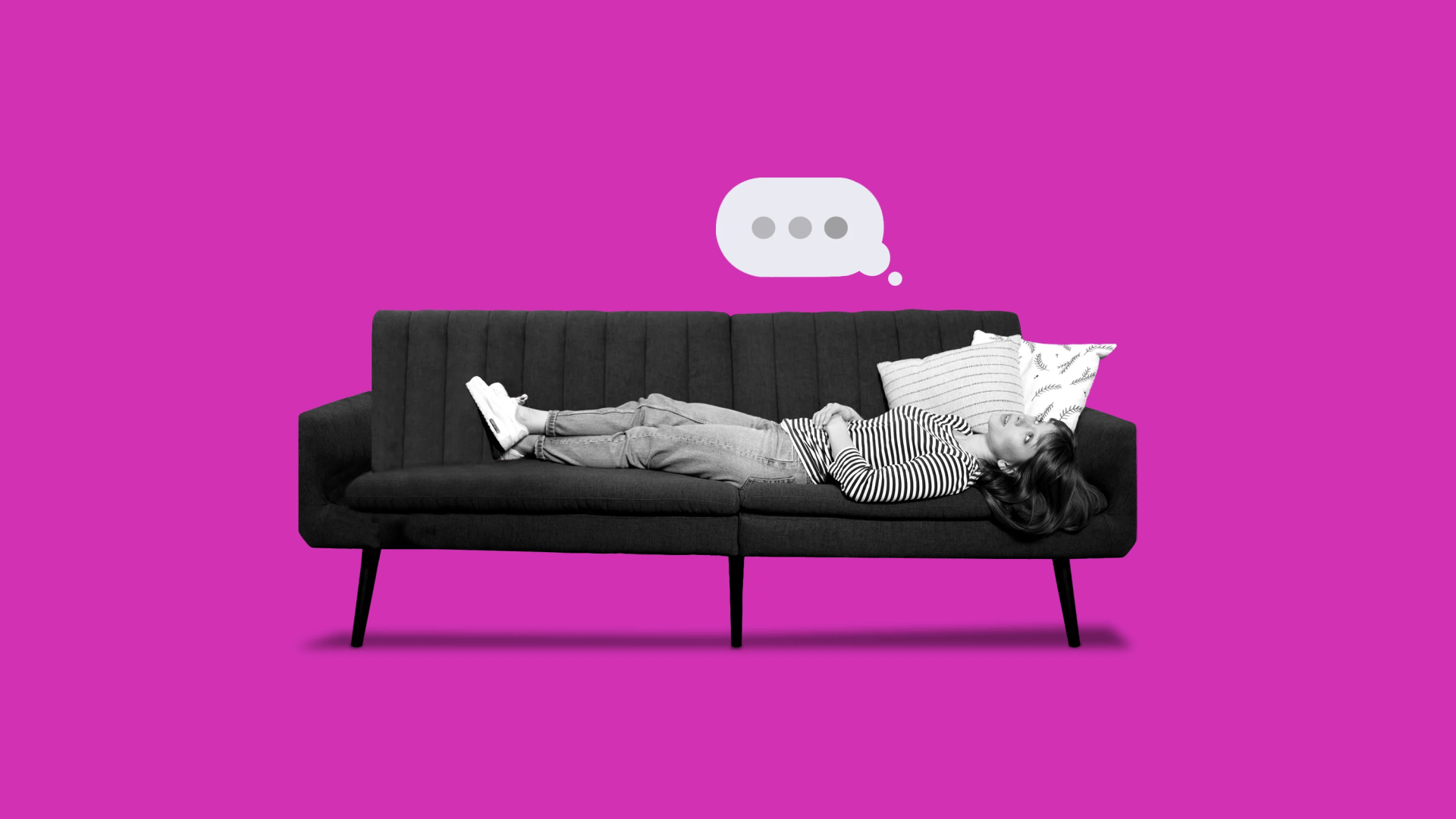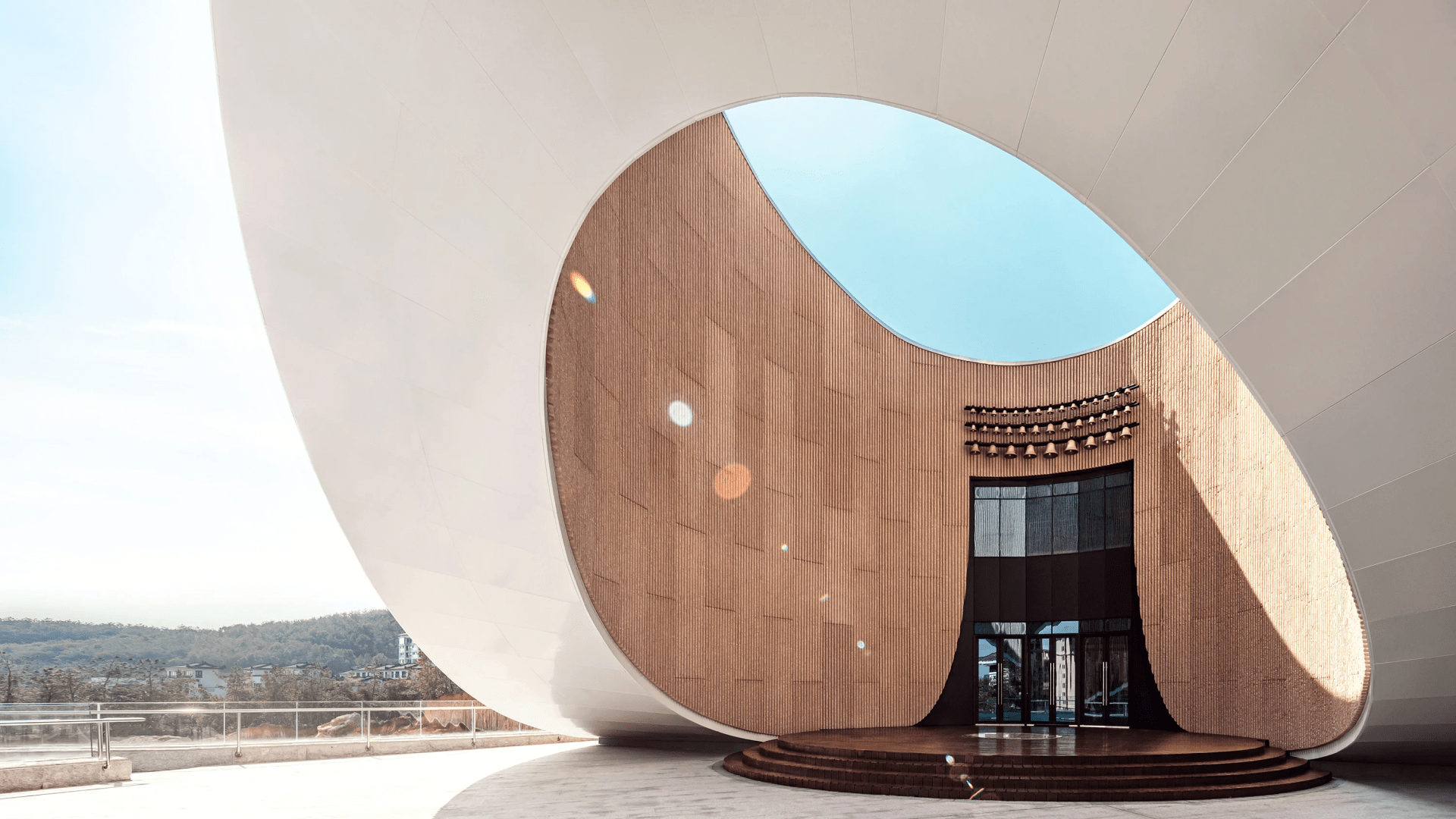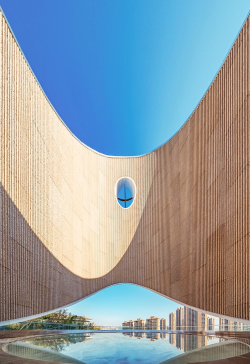在過去的25年裡,美國的福音派發生了一些事——在我看來,是一次大規模的世代轉變。我想描述一些我看到的變化,並請教大家是否也觀察到同樣的改變。
首先,讓我形容一下我看到的場景。我所描述的對象是美國各派基督教裡較不重視宗教儀式的新教教會:通常以聖經、傳福音和個人對耶穌的信仰爲中心;普遍(不全是)為不隸屬任何教派的教會。對聖禮、儀式和教會權威的重視程度較為謹慎(或甚至幾乎不看重)。這些教會帶有美國靈命大復興時期的特色,在性、婚姻和其他社會議題的看法上持保守立場。從歷史上來看,這些教會的成員主要以白人中產、中低產階級為主,但教會整體其實並不像人們通常以為的有高度的同質性。許多像這樣的教會在過去三十年內成立,他們通常喜歡較長的講道、較現代化的敬拜方式、每領月一次聖餐,教會內有很多燈。
就是在這些教會之中,我觀察到一種我形容為「逐漸鬆動」的轉變。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不為人所覺察,或至少是非人為計劃的。這種鬆動並沒有一致性,也不是意識形態的轉變;因為它並非某種事工項目或政治宣言。它本身甚至與保守派或自由派無關。我這篇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對這種變化作出全面性的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這種鬆動包括逐漸放下一些曾經的潛規則──至少不是明文規定的──教會內的社會規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喝酒的看法。眾所周知,過去幾個世代的福音派基督徒對喝酒持非常高的警戒心,有時甚至到了絕對禁止接觸酒精的地步。在我青少年時期,這種情況仍然存在。當我聽說某陳弟兄或某林姊妹喜歡睡前小酌一杯時,通常只能是私下流傳的八卦消息。陳弟兄或林姐妹絕對不會在公共場合喝酒,更不會在自家車庫釀啤酒,然後在小組聚會中讓大家試喝。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我所知,這種對喝酒的禁忌幾乎已消失殆盡。在我任教的私立基督教大學裡,校規包含教授不能跟學生一起喝酒,但僅僅12年前,教授甚至不被允許喝酒。像這樣改變了校規的福音派學校非常多。
讓我們再想想美國福音派中其他陳腐的禁忌──紋身、跳舞、賭博、抽菸,甚至是妻子在外工作。紋身不再是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福音派中「很酷的」知名牧師的專利。如果我問我那些敬虔的基督徒學生,他們是出於何種神學考量決定擁有多處紋身的,他們甚至不會以一堆足夠反駁他們祖父母輩對利未記19:28過時解經的論述來回覆我。他們只會給我一個白眼:紋不紋身跟信上帝有什麼關聯性?
或者,觀察一下基督徒們在休閒娛樂選擇上的改變。教會和基督徒家長現在仍會監管孩子瀏覽內容的恰當界限,但容許的範圍已大大地拓寬了。曾經,人們甚至會對迪士尼電影小心翼翼的,因為大家曾深信大銀幕上的性、不當語言和暴力畫面是導致青少年出現問題行為的危險因素。但現在,福音派基督徒在網飛(Netflix)或HBO的瀏覽清單與其他普通用戶似乎沒什麼差異。有些人甚至把收看《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或《黑道家族》(Sopranos)當作參與在文化裡的必要任務。他們會說:我只是在履行我的福音使命,如果血腥、殘忍和裸露的畫面冒犯了你的基要主義背景,我很遺憾,這個世界對你——信心軟弱的弟兄——而言還有更多更可怕的東西。(林前9:22)
相似的鬆動也正發生在教會內。我原先認識的美國福音派長期以來對天主教的一些作法嗤之以鼻,無論是正式的儀式、祭袍、聖禮、根據教會年曆慶祝宗教節期,複誦使徒信經⋯⋯等。長期以來,這些天主教儀式被視爲聖經教導外的習俗,有模糊福音焦點的危險,僭越基督的主權,或是會助長一種毫無生氣、有名無實的信仰。
然而今天,我注意到各種福音派機構以令人驚訝的步伐朝著重新發掘這些以前由天主教制定的習俗的方向邁進。以前曾拒絕承認復活節有別於其他星期天的基督徒們,現在甚至會開始紀念四旬期/大齋期(Lent)。曾因信仰原則拒絕各種信經的教會,現在每個星期天都會背誦「使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曾堅持相信聖餐只具備紀念意義的教會,現在在聖餐中會特別談及基督的真實同在。(在英文裡,福音派教會開始以「Eucharist(聖餐)」一詞來稱呼聖餐,而不僅僅是「the Lord’s Supper(主的晚餐)」)。
這種鬆動甚至延伸到福音派神學院的課程和講道研究中。神學院教授和牧師們開始參考福音派以外(甚至新教之外)的作家和思想家,更借鑑天主教神父、中世紀東正教修士以及教父時期的主教和大公會議的觀點。與我前面舉的其他例子一樣,這樣的轉變並非屈服於神學上的自由主義。某些神學操練──尤其是誦讀信經──是種保守的變化,以教義教導(catechesis)作為防止神學偏離的堡壘。
現在,我稱這種鬆動爲「世代轉變」。某種意義上而言,確實如此。但據我觀察,並非只有40歲以下的人參與在這樣的轉變裡。如果僅僅只有年輕人的話,即使是個重要的變化,也可能只是孩子們反叛、擺脫父母輩的行事方式的正常反應而已。
相反的,我看到的是,這種鬆動不只發生在千禧世代和Z世代,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也正在轉變。許多以前完全禁酒的人現在開始喝酒了,曾抵制迪士尼的人開始訂閱網飛(Netflix),以前對任何有賭博疑慮的活動持警戒態度的人現在會邀朋友一同舉辦撲克之夜。
如果我的觀察是正確的,那麼,這其實是種天翻地覆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微小的變化。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讓這麼多福音派基督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脫離這麼多對外在行為和宗教儀式設下的禁忌?
在我大膽地提出我的想法前,我必須說這只是我自己的推測。我沒有圖表來支持我的論點或有數據證實我的想法。但正如我在前面分享我所觀察到的「鬆動變化」——我想知道其他基督徒是否也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現在,我想提出能解釋這些變化的想法,也許也能引起其他美國福音派基督徒的共鳴。
首先,這種鬆動對我來說意味著,美國福音派許多不成文的規範和標準並非全然由教義、教會的權威或聖經教導所支撐。反對「喝酒、紋身、正規的宗教儀式」等不成文的規範能有如此強大及一統性的力量,還需倚靠教會周遭環境的文化。
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外部環境的支持包括國家的角色。在過去半個世紀,一些規範這些「世俗的行為」的法律——例如關於酒精、離婚、毒品和曾經非法的性行為的法律,已像多米諾骨牌那樣紛紛倒下,而這些法律的改變與教會規範開始鬆動的現象同個時期發生並非巧合。有時候,法律是文化的下游產物,有時則是上游源頭。但無論如何,教會都是這條社會河流的一部分。
其次,美國文化的基督教色彩越來越淡,世俗色彩越來越重,這為一般基督徒帶來改變的動機和壓力。如果非基督徒之中的多數的人都相信或參與某件事,那麼繼續拒絕做同樣的事(絕不妥協)的基督徒的門徒身分就會更加醒目。這讓許多基督徒,包括牧者們重新思考,喝酒真的是上帝所禁止的嗎?這種規範是否真的白紙黑字、明白地寫在經節裡面?如果不是,我爲什麼要因禁酒遭受鄰居或同事的嘲諷?再說,反正大家都知道某個弟兄或姊妹家裡的藏酒十分豐富,讓我們加入他們吧!
第三,當聖經在某些問題上確實無特定立場(教會內有各種不同立場),但教會身處的更廣泛的外圍文化有十分明確的立場時,一般來說,牧師或教會機構有責任領導會衆拒絕(或接受)所處的文化的標準。但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美國牧者本身的權威性一落千丈、教派身份/忠誠度消亡、以及基督教組織的信任度危機不斷上升。
以前常聽人掛在嘴上的「長老們都這麼這麼說」或「某某牧師說的一定不會錯」已經很難再拿來應對當前的環境了。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用腳投票,直接加入另一間牧師有不同看法的教會,畢竟,「某某牧師有什麼資格決定這段經文的意義?他不是曾教導我們,所有基督徒都有能力自己解釋聖經嗎?以及,除了聖經,沒有任何權柄有關於信仰和道德問題的終極權威?他自己也曾說,所有聖經未提及的議題都是『非至關緊要(無關乎救恩)』的問題,取決於個人良知去跟隨?」
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在後基督教時代(post-Christian)的戰場上,不再有教派之分。儘管這聽起來違背常理,但那股引導福音派開始喝酒、刺青和收看HBO的力量,同時引導著他們背誦基督教信經、接受在額頭上畫聖灰(教會歷史上的復活節傳統之ㄧ)並閱讀教皇本篤十六世的文章。當整個世界文化都不利於人們信實地跟隨基督時,你需要所有能和你站在一起的朋友。ㄧ些和當前的文化爭戰相比而言較輕微的教義上的分歧,例如關於嬰兒洗禮的爭議,並非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需要對付的議題,這些教義的分歧在緊要關頭可以暫時放下,但當然,這種放下不包含關於性和性別議題於神學上的分歧。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開頭說,我看到的鬆動現象並非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或背後有什麼意識形態在推動的計劃。這種鬆動自然地、有機地、同時在多處浮現,有時還以明顯矛盾的方式發生。正因如此,要評價這種鬆動並不容易。我自己是在沒有嚴謹的宗教儀式或喝酒的家庭文化下長大。但現在,我禱告前會在胸口劃十字架,也會和父母一起喝酒。另一方面而言,我對大、小螢幕媒體(無論是串流影音或TikTok等app)對基督徒休閒時間的逐步佔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媒體內容的無所謂態度/識讀能力感到悲傷、遺憾。
無論每個具體的鬆動現象是好是壞,或是尚待確定,我所知道的是,與這種逐步鬆動同時發生的,還有教會出席率的下降、伴隨而來的孤單感,以及會衆拒絕教會對其成員行使權威的情況的增加。對ㄧ些人來說,這似乎是基督教信仰正在進步的跡象(也許教會權威的減少意味著屬靈濫權/屬靈虐待情況的減少),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是基督信仰的損失(在迷途中的基督徒需要有人下猛藥來幫助他們步入正軌)。
無論如何,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當下,美國福音派正在發生變化。當這一轉變結束時,美國福音派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只有上帝知道。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柏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他撰寫了四本書,包括《教會:上帝子民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和《給未來聖徒的信:給精神飢渴者的信仰基礎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