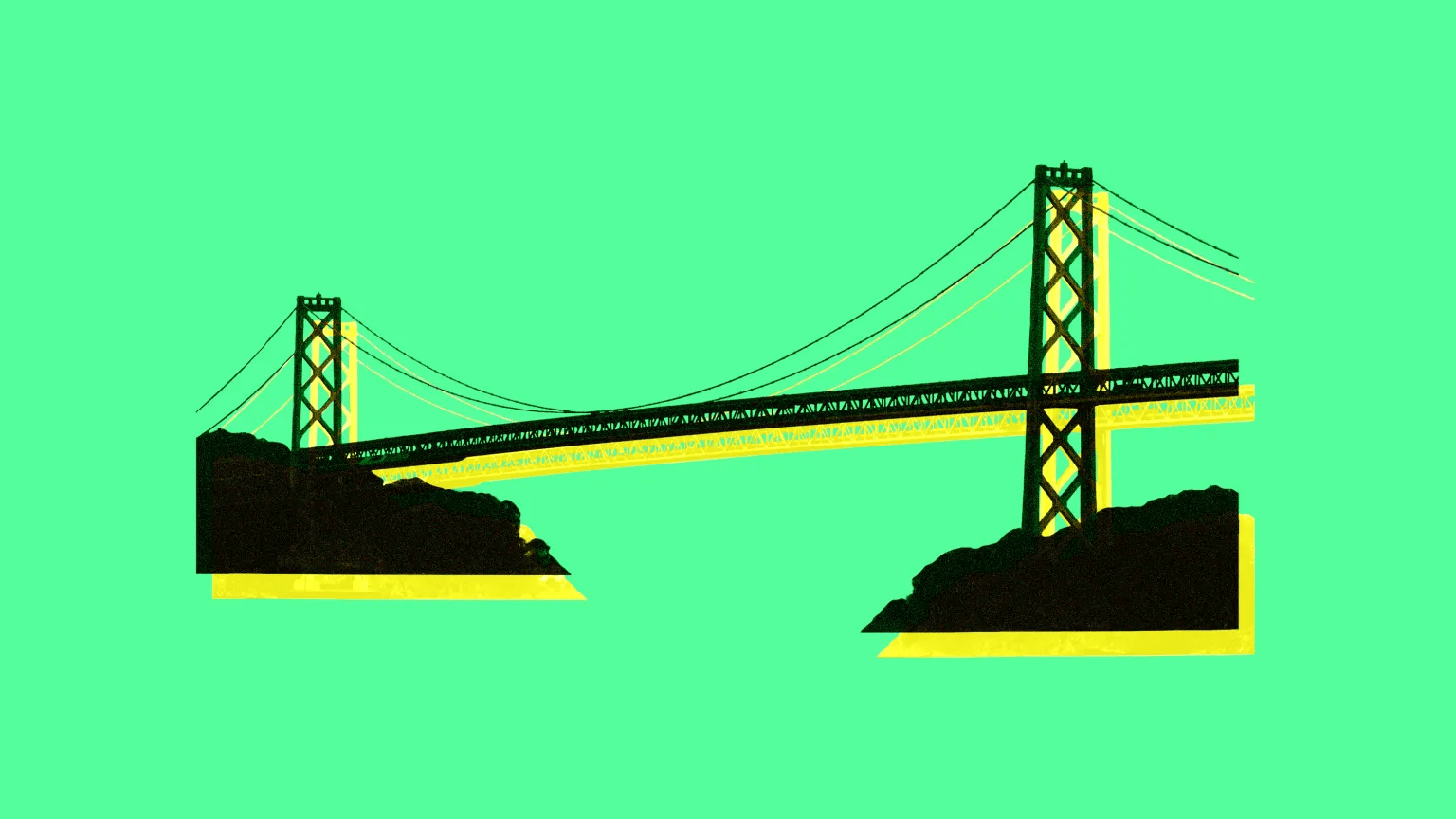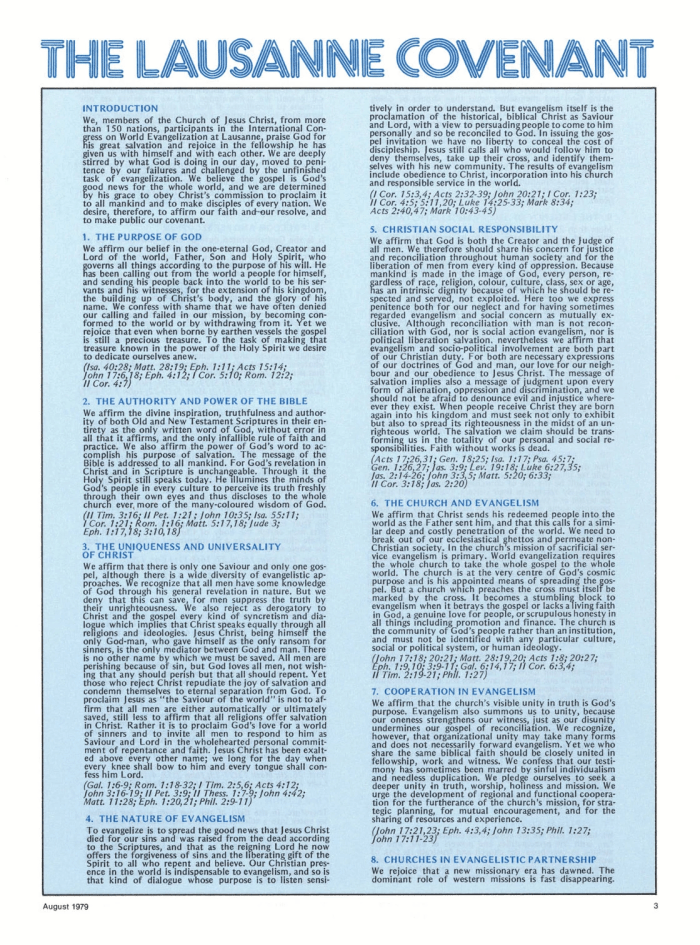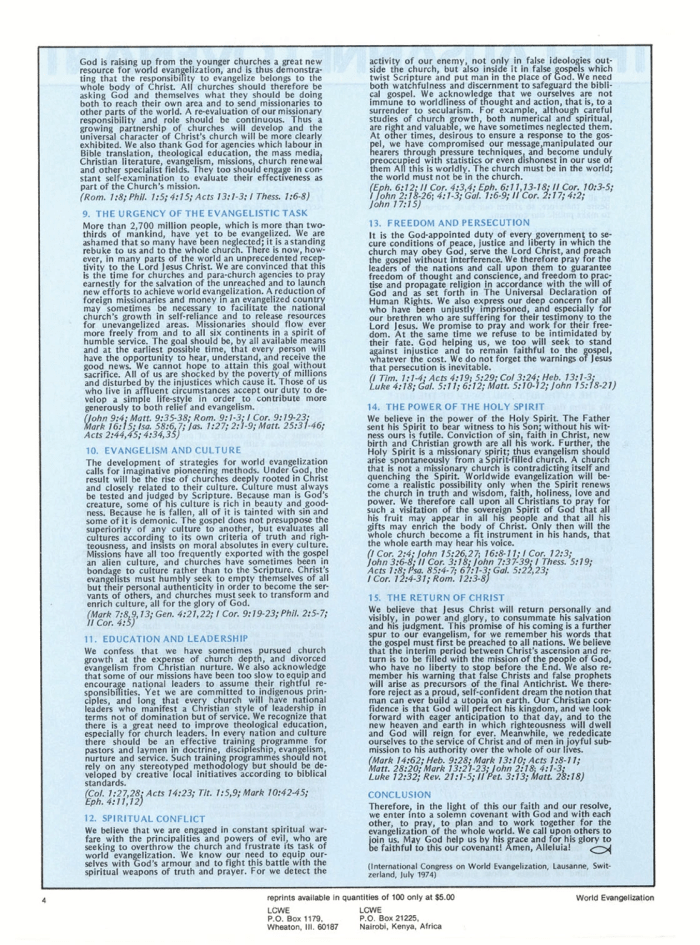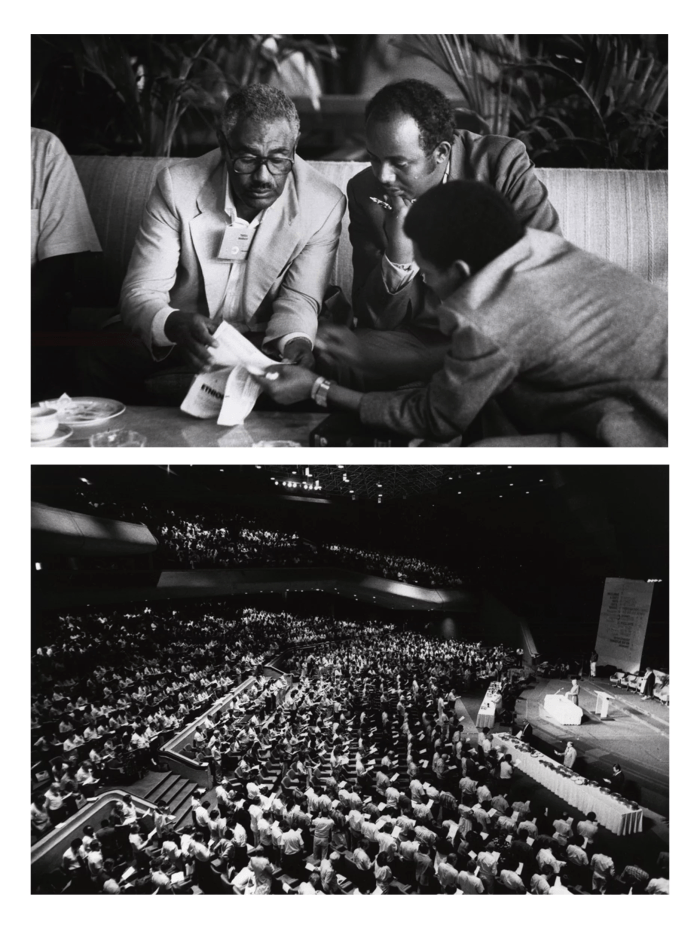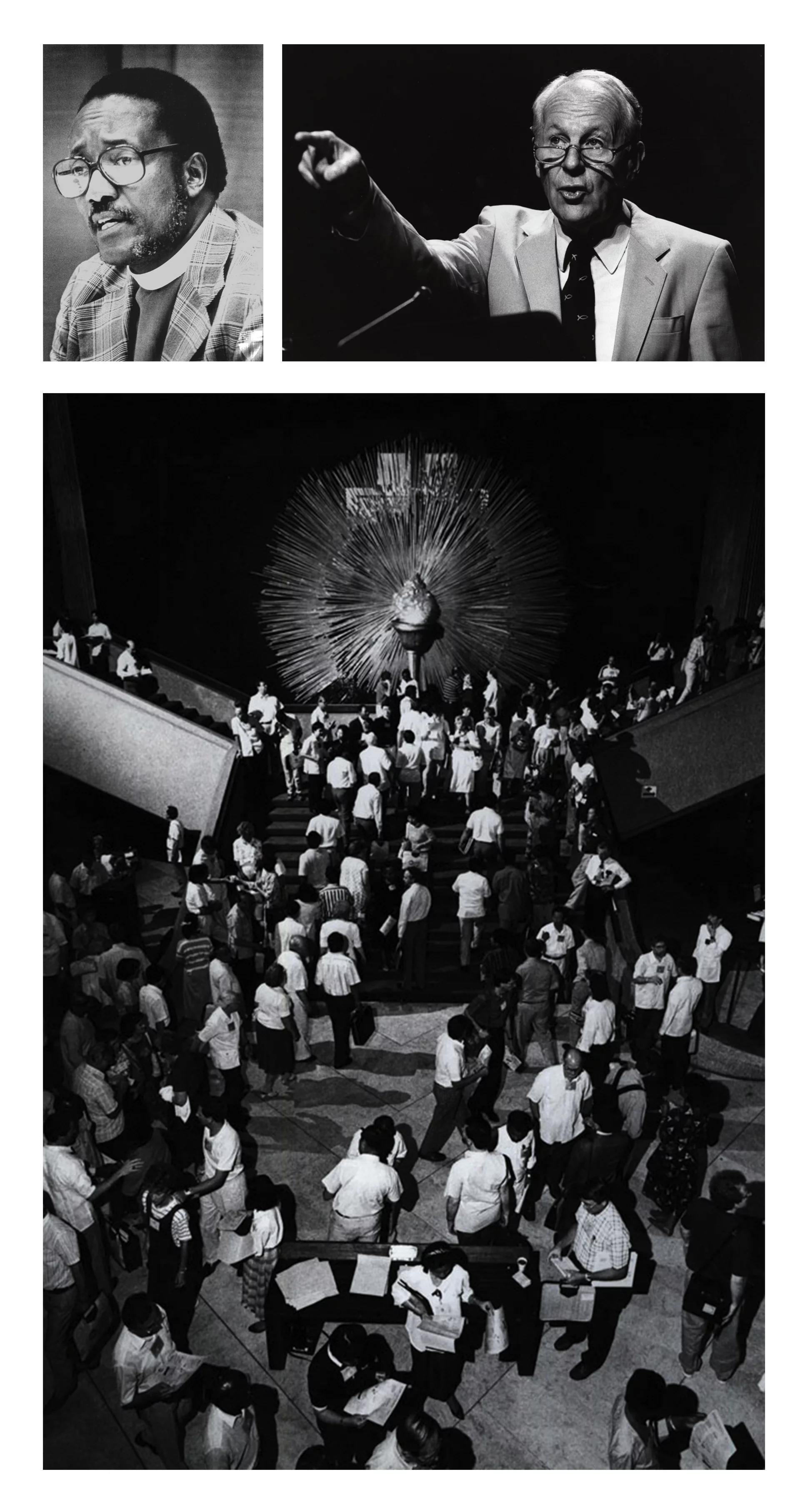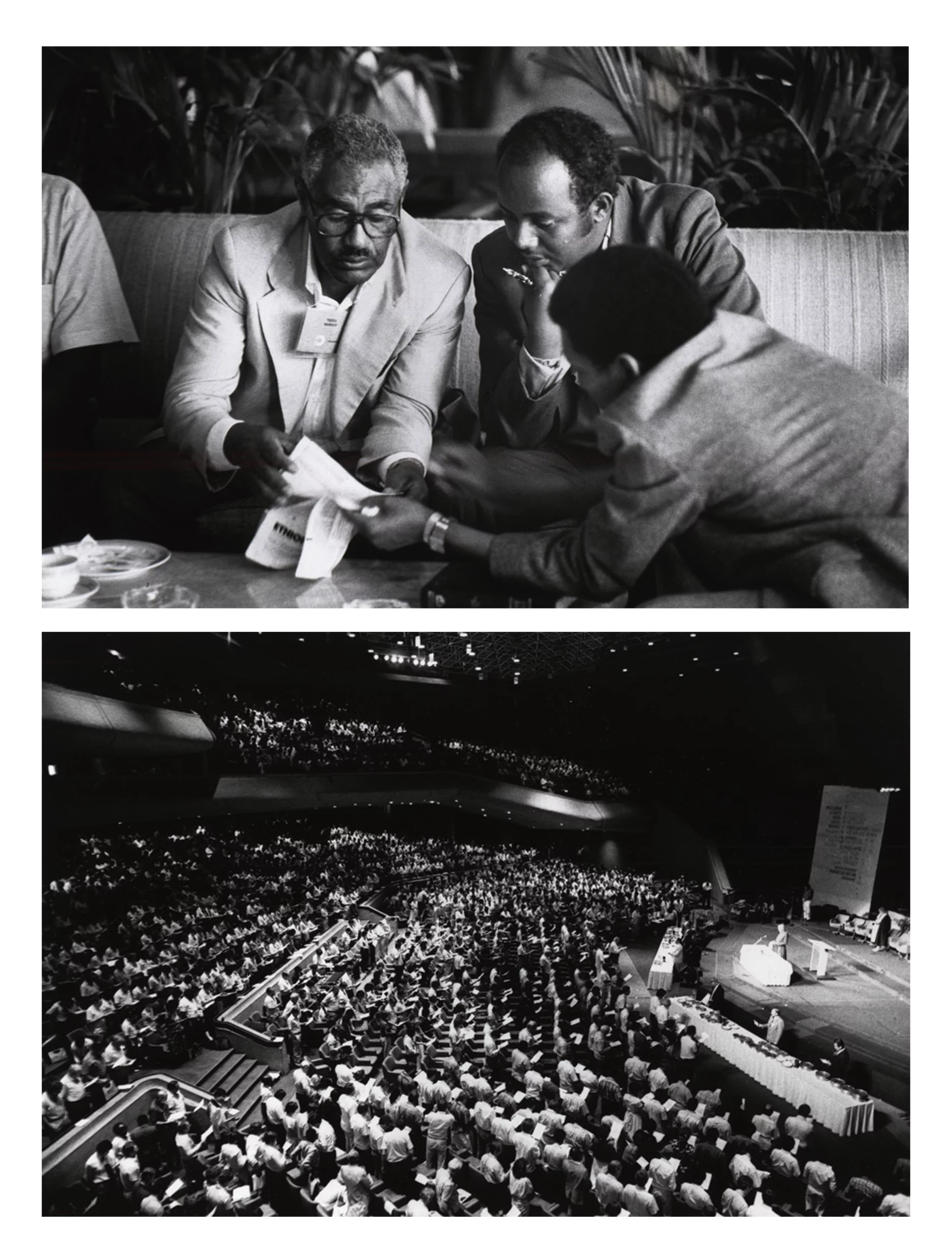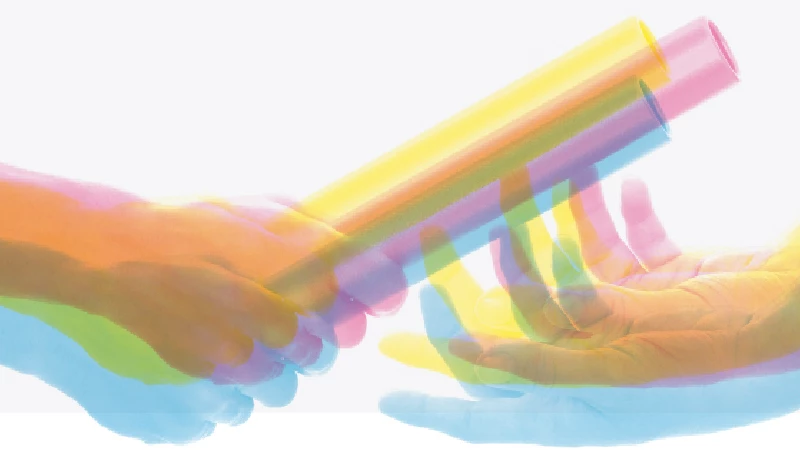我在加州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一間小型福音派教會長大,教會裡的藍領人士比白領人士多。每個星期天大約有25個家庭來到教會;他們充滿愛心、慷慨且善解人意。我們曾在內華達山脈露營,背著背包穿越優勝美地,在半月灣設置捕蟹籠。我們會一起研讀神的話語、和遭遇經濟困境的朋友分享食物,教會結束後一起去了手指數不清次數的速食店。那是陽光明媚的加州風格的福音派信仰,保守的立場展現在T恤配衝浪褲的穿搭和輕鬆愉快的態度上。
每當我回想那間教會,儘管它並不完美,我總是滿心感激。它使我對隨後多年裡常聽到的「有毒的福音派」刻板印象產生免疫,尤其是在世俗大學裡——福音派教會常被描繪成「無知且充滿偏見」的堡壘。
當我在2009年選擇離開學術界時,ㄧ部分的原因是幻滅。人文科學院對知識探究的興趣似乎遠低於對意識形態一至性的要求。我清楚地記得在一場博士研討會上,我的一位同事將整個基督教傳教史貶斥為純粹貪婪的殖民主義。我同意那段歷史裡有許多值得哀嘆之處,但難道我們無法同時承認,肯定有某些宣教士,在那時期的某些時候,確實是帶著善良的意圖出發的?
從學識研究的正直性來看,這種想法似乎應是和我對話的人至少能接受的。但相反的,她卻把我告到教授面前,指控我犯了「為邪惡機構辯護」的思想罪。
這只是我一連串類似的經驗中的一個例子。有太多的講座讓人覺得更像是在為政治計畫招兵買馬,有太多的研討會讓人覺得像是在比賽誰最先表示自己「感到被冒犯」。提出一篇違背人文學科當下的政治正確的論文,即使有再多的證據和論證也不足夠;而提出一篇為人所愛的論文,則幾乎不需要證據和論證。畢竟,一旦你決心放棄這世上存在單一真理的概念,何不直接選擇一個為你和你的部落/群體服務的敘事呢?當你能為人「伸張正義」時,誰還會在乎你的準確性?
於是我離開了學術界,幫助創辦一間新媒體企業。如今回想起當年隨著部落格圈子和社交媒體的興起而抱有的理想主義,也覺得實在諷刺。當時,我以為在數位領域裡,我們可以重新想像一場富有愛心、知識淵博且敢於挑戰黨派成見的公共對話。我以為,或許基督徒可以塑造一種公共參與的形式,在捍衛基督教價值觀的同時展現基督徒的美德。或許社交媒體可以成為學術圈本應有的樣貌:一個思想自由流通的市場,在那裡,最好的論點能憑其優點勝出。
然而,在隨後的幾年裡,新媒體企業建立了能激勵人類最惡劣行為的賺錢模式。通往財富與影響力的途徑就是病毒式傳播,而病毒式傳播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煽動部落/群體間的敵意。科技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稱之為「抵達腦幹底部的競賽」。肯定你受眾的既定偏見和預設,激起他們的恐懼,再一起蔑視其他部落——你就能收穫大量激情且不斷增長的追蹤者,然後就能透過演講和寫作獲利。
換句話說,建立讀者群的最快方法,不是透過長期忠實的工作來建立專業知識和可信度,而是透過迎合某一群體的部落敵意來獲得病毒式傳播的名聲。最初旨在吸引人注意力的行為變成煽動憤怒的農場。
在病毒式傳播文化的初期,各陣營的分界線劃在保守福音派和進步的主流派等大群體之間。但最後,社交媒體平台顯然可以藉由將讀者分為更狹小的子類別,進一步提高平台的參與度,並投放更精準的目標廣告(也就能賺更多錢)。擁有共同信念的大型社群開始分化,細分為彼此交戰的陣營;每個陣營都有自己的資訊來源,並對周遭的人抱持相同的敵意。我們對所謂背叛我們部落的人所感到的憤怒,遠多於我們對那些一開始就不屬於我們部落的人的憤怒。
所以,我們來到今天的局面:福音派在嘲諷的市場中被買賣,並彼此對立以謀取利益。作家/內容創作者和觀眾都沉迷於製造分裂所帶來的多巴胺反應。這種情況就像我曾經生活和工作的人文科學院。
一切都被簡化為政治立場。只要敘事符合你的部落的利益,事實就不重要了。我們事業的成功不在於愛與理解他人,而在於嘲諷和扭曲地描繪他人。
需要澄清的是,《今日基督教》從未主張基督徒應該退出政治生活。雖然政治不能使死人復活,但卻能服事活人。
問題不在於基督徒身處衝突之中,而在於衝突進入了基督徒的內心。我們與彼此、與社會互動的方式應該跟隨基督的模式,而非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文化模式。
《今日基督教》從未完全符合任何一種群體的政治議程,因為我們對上帝國度的委身遠超過對任何黨派或國家的利益。我們這樣的作法讓那些試圖定義他人政治/神學派別邊界的人感到挫折,但我們認為這是我們使命的核心。我們拒絕參與憤怒的循環。
我們的呼召是推動上帝的國度的敘事和理念。無論這些故事是鼓舞人心的,還是艱難的,我們都會講述。我們邀請正統基督教會的聲音來為不同觀點辯護。我們努力理解並向社會示範在我們的時代跟隨耶穌的真正意義。《今日基督教》由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董事、行政人員、職員、作家和讀者組成。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優勢,而不是弱點。
我們在加州中央山谷教會唱過的一首詩歌是《他們會因我們的愛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曾經深刻經歷到基督身體的愛,在我的靈魂上留下了印記。正如耶穌在約翰福音13:35所說的:「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也如祂在約翰福音17章的禱告,正是因著教會的合一,「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彼此表達的愛、向世界展現的合一,見證了基督的神性和上帝的愛的真實性。教會應向世人展現基督的形象,然而今天這形象卻充滿爭議且四分五裂。
上帝的國度總是顛覆世人的期望。在祂的國度裡,祂將被世界顛倒的秩序重新恢復到正確的狀態。在祂的國度裡,祂高舉謙卑的人勝過驕傲的人、讓溫柔的人勝過強大的人、使無權無勢的人勝過有權有勢的人。祂的國度是最深刻的逆著世界文化而行的文化。
也許此時此刻,基督徒所能做的最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事,就是拒絕將彼此妖魔化。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靈性健全、頭腦清晰的基督徒對「何謂彼此相愛的心」會有不同的想法。你的良知要你支持哪位候選人,你就支持他,但讓你的愛依然是你起初的愛(啟2:4-5),並讓我們彼此的愛成為向世界見證基督在我們中間真實活著並工作的標誌。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