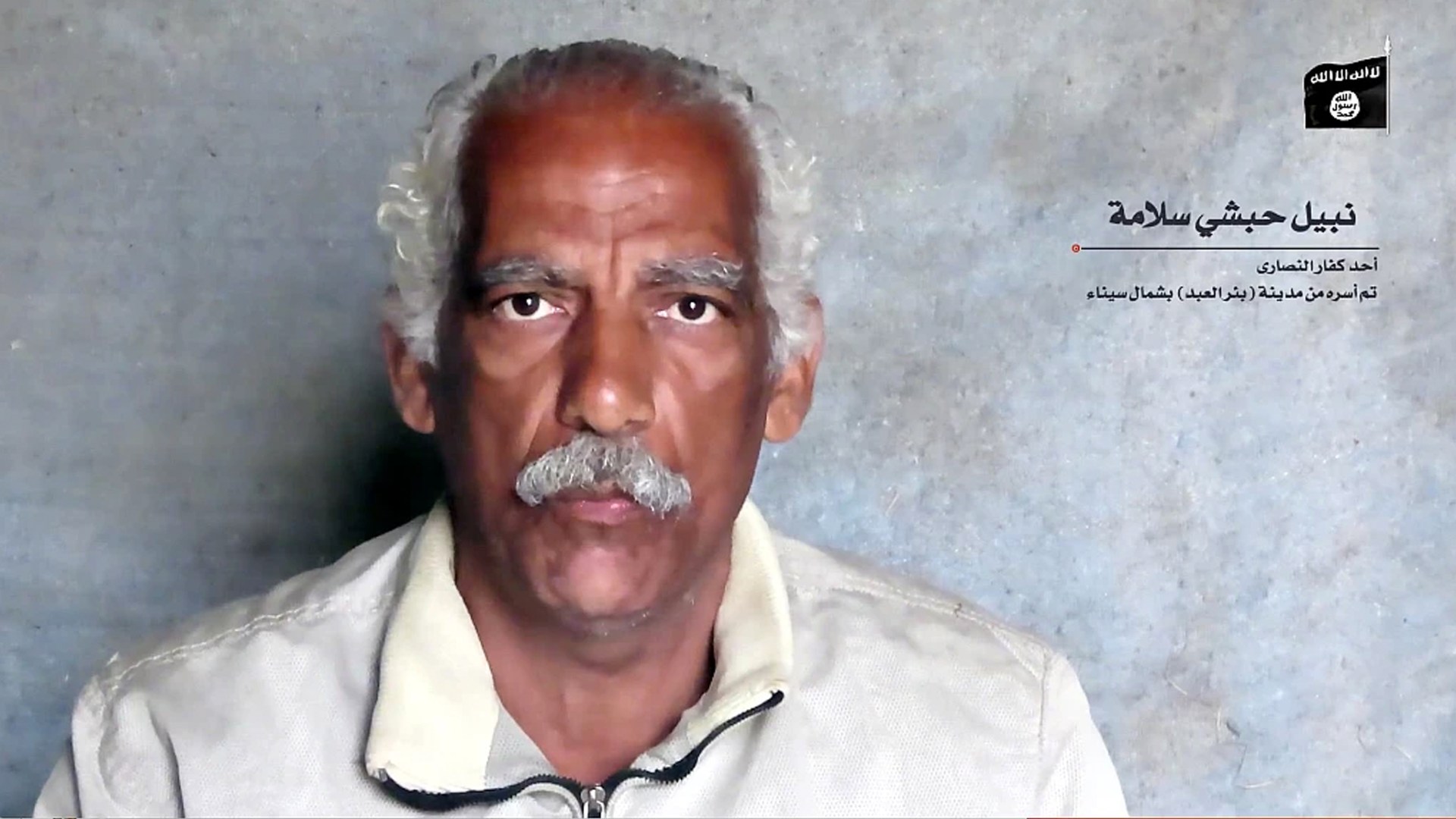華里克(Rick Warren)的馬鞍峰教會最近因為按立了三位女牧師而 上了頭條 。 聽到這幾位女性因著按立而得到大眾的認可和宗派的扶持叫我欣慰, 但是讀到報導後便深深地嘆了口氣:“哎呀!又來了。” 我早預測到女性在教會職責的議題會佔據一整個星期的版面,也預測到這些了無新意的論點。
有個公開的秘密:你知道誰最討厭談論女性擔任聖職嗎? 女性牧師們, 但不全都是。 有些女性特別有討論這項議題的恩賜,而我也真心祝福她們。
但現實生活中很少人是為了討論女性擔任聖職而去成為牧師的。 我們被按立,是因為福音佔據了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被按立為要見證耶穌的榮美和真理。 我們被按立是為了用道和聖禮服事教會。 (鄭重聲明,沒有比為了道和聖禮 更值得接受聖職的。)
女性接受聖職我以前也不贊同。 在我30多歲之前,我算是溫和互補主義者(soft complementarian), 但我同時也是以女性的身分在教會服事。 我教會的弟兄姐妹都以為我最終會嫁給牧師(算是平信徒姐妹非正規地進入帶職事奉的方法) 。 我曾在美南浸信會的青年團契和美國長老教會的慈善事工實習,在移民、街友和貧民之間服事。 我之後去讀神學院,發現自己有神學研究的喜愛和竅門,最後還當了幾年的校牧。
我花時間仔細鑽研按牧的爭議,這幾年 我的看法改變了。 而在這段神學研究畫下句點後,我決定按牧相較之下是自然又實際的。 我接受按牧,不是為了要證明女性也應該當牧師,也不是想為正義發表聲明。 我接受按牧,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女性(或男性)都有接受按牧的絕對權利。 我接受按牧,是因為我已經帶職事奉,並且對教會和聖禮都非常看重,使我的生活和我在教會的職分密不可分了。
我當時已經投入事工, 也開始教導和訓練門徒。 我希望能公開在聖徒面前事奉。
現在每當我講道時,每當我把手輕放在流淚姐妹的肩膀上、傾聽她的悔改時,每當我寫文章時,每當我和學生散步,回答對於聖經的疑問時,每當我在疲憊的弟兄姐妹面前舉起聖餐,用最清楚洪量的聲音宣告這是“神賜予祂子民的恩典”時,我心中想的不是女性接受聖職的議題。 我心中想的不是希臘文的動詞或聖經對女性的職分。 我默默禱告求聖靈吸引我們到神自己面前,來造就祂的教會,恢復我們的信心。
女性接受聖職無疑是一門重要的議題。 我非常感謝聖經學者和神學家們,他們認真鑽研聖經的論證(最新的是 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ison Barr) 和 威廉·維特(William Witt),都有出版關於這項議題的新書)。 我們需要這樣的對話。 我也會延續這樣的討論。
只是網上或是教會裡對這項議題的討論多於抽象。 對參與服事的我們而言,事工具體地根基於我們所愛所服事的人群之生命上。 雖然按牧的議題不常在需要受服事的弟兄姊妹間討論,但是人太想要花時間討論此事了。 就我所知,不論哪位女傳道或牧師,如果在飛機、火車、或是巴士上,如果被鄰座發現她的身份,後者總會以義憤填膺的顫聲發表長篇大論,直指女性受聖職之不是。
當教會一半的人想說服我們辭職時,有另一半人卻把我們當作擊潰父權主義的鬥士而拍手叫好。
剛按牧不久時,當我在會議休息空檔,穿著牧師服短暫進出附近文青風的咖啡廳時,看見用微笑加點頭熱切肯定我的客人,讓我很受激勵。 你們的回應我很感激。 真的。 但是我知道我對他們而言只是女權主義勝利的代表, 而不是福音的宣教士。 況且,我有時候只想要買杯咖啡好好讀本書,暫時放下神學家的帽子。 我像是種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 無論我是否願意,我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 (正是因為如此,我不再輕易穿牧師服公開現身了。)
我的存在給人麻煩,也給人鼓勵。 而且大家總是在我對《聖經》、性別角色或是耶穌的立場上有所揣測。
本來願意與互補主義支持論者合作甚至切搓的我們,對此感到事情的不單純。 我們熱愛教會和聖經,目的是“以和為貴”。 自由派認為我們“把敵人當自己人”,但我們從始至終沒打進互補主義的圈子裡。 因此我們總覺得自己在這樣的對話中格格不入,受到兩極分化教會雙面的衝擊,基督的福音在辯論時總是退居次要。
在我自己的宗派中,做牧師的姐妹們在各個方面常出乎意料地得做擋箭牌。 她們忠心服事教會, 順服教會領袖, 也常常得應付各種弟兄不必面對的批評:從說話語氣到神學立場各方面。 但她們依然繼續做牧師。 因為這是她們的本質:牧師、牧人、母親、僕人。
昨天,我們事工裡一位年輕姐妹坐在我辦公室的沙發上說,“我服事是為了看見人得著自由”。 畢竟吸引我們事奉的是耶穌和大使命, 我們不是為了第二波女權主義,或像阿爾·莫勒(Al Mohler)最近在對馬鞍峰教會新聞的回應中所形容的 “解放神學下的衝動”。 我們想要用神賦予的恩賜服事教會。
身為一名女牧師,我常認為自己被迫擔任專家的角色,參與到這場我認為無趣的文化大戰中。 我對事奉的熱情並非出於爭奪名份, 我熱愛事奉是為了能在耶穌的事奉上有份。
基督自己的作為才是最終吸引女性受聖職的原因。 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沒錯,我們得努力忠心傳講聖經。 沒錯,我們需要好好討論女性受聖職的議題。 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大部分的時間或精力耗費在來爭論姐妹 如何 在禾場上做工。 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福音上。 我們會不斷擺上,因為我們尋求跟隨的是收割莊稼的主。
蒂什·哈裡森·沃倫(Tish Harrison Warren)為北美聖公會的牧師,同時也是《樸實人的禱文》和《深夜中的禱告》一書的作者(校園團契書房出版社,2021年)。 在推特上關注她 @Tish_H_Warren。
翻譯:王寧揚
責任編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