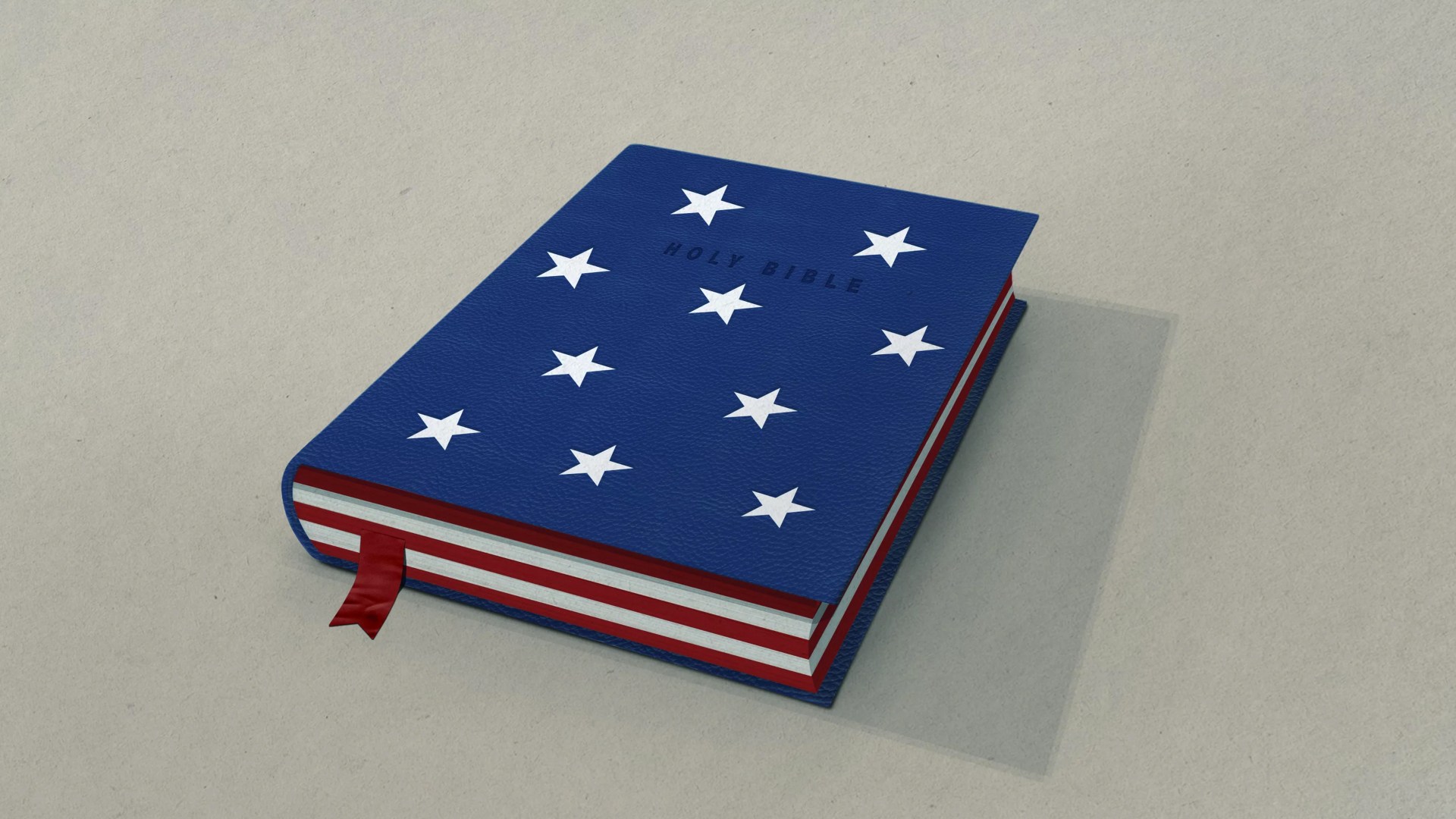在2000年代中期,記者和學者們擔心美國即將成為一個神權國家成為一種時尚。保守的白人福音派推動了喬治·W·布什的選舉,並幫助梅爾·吉布森的《基督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成為票房大賣。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了重新主導政治和文化。於是,書籍和文章傾瀉而出,警告 “統治主義”(Dominionism)、“基督教重建主義 ”和其他各種運動的奇特危險,這些主義合謀,要把基督教信仰強加給毫無戒心的民眾。
這種說法隨著巴拉克·奧巴馬的當選而轟然倒塌。幾乎在一夜之間,對美國淪為神權主義的恐懼消失了。專家們開始預測宗教右翼的死亡。曾經把小布什推上權力寶座的福音派 開始8年抗戰,轉為防守。福音派越來越多地把自己看成是世俗主義討伐的目標,而不是冉冉升起的執政者夥伴。
然後唐納德·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切。他出人意料的當選部分得益於白人福音派的支持。他重新喚醒了人們對宗教保守派會在神權主義旗幟下動員民眾的恐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的小說《女僕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梅開二度,被重新用作特朗普時代的警世寓言(及被Hulu用來製作一部熱門的電視連續劇)。小說(電視劇)想像了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反烏托邦荒誕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女性被強迫為男人繁衍後代。
然而,美國陷入真正的神權主義的想法缺乏小布什時期的(表面上的)可信度。儘管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熱情地將特朗普送入白宮,但特朗普缺乏個人的虔誠,這使他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徹底基督教化的聯邦共同體的統領者。大體上,他的福音派支持者也沒有將他誤認為是一位虔誠的政治家。與其說特朗普是大衛王,不如說他是居魯士——這位異教的波斯皇帝在征服巴比倫後,允許被擄的以色列人回到家鄉重新定居,並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不過,隨著特朗普上台,宗教保守派的政治命運似乎有所改善。這為一個新的新聞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點創造了條件:揭開白人福音派為何如此狂熱地湧向特朗普,支持他。這種類型的書籍和文章的典型特徵仍然是對保守派基督徒操縱權力槓桿的擔憂。但是因為穿戴全套神權統治服裝的戲景已經黯淡下來——而且特朗普更多是將自己塑造成擁護美國偉大的明君而不是伸張宗教信仰的平反者——這類書籍和文章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一種截然不同但有部分重疊的現像上:那就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特權與權力
與民族主義本身一樣,基督教民族主義也很難界定,特別是這個詞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又可以以貶義的方式被使用。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觸及到宗教、國家、種族或族裔認同的深流。然而,我們很難為它設定精確的界限,因為同情這種意識形態的人對其標誌性訴求的支持程度也不同。如果定義下得太窄,你可能會錯過一個重要的、由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敵人構成的矩陣。如果定義下得太廣,你可能會把那些根本沒有並肩站在一起的基礎的人歸為一類。
這樣的難題在三本從不同的角度衡量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新書中向我們展示出來。這三本書以不同的方式描繪了一個致力於維護自身特權和權力的運動,它偏向於土生土長的白人而非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利益,並利用法律權威把基督教化的道德秩序加諸於社會。這些書並不具有同等程度的說服力,但每一本都(以不同的方式)值得閱讀和思考。
社會學家安德魯·L·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塞繆爾·L·佩里(Samuel L. Perry)在《為上帝奪回美國——美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進行了公允的、以調查為導向的分析。懷特海和佩里將基督教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理想化的意識形態,它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文化願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美國的建國原則是神聖的(基督教的)”這一信念。對這種願景的委身表現在對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擁槍權的狂熱捍衛和關於愛國主義和美國國旗的爭議上。
最關鍵的是,它還表現為一種維護邊界(包括種族和民族的邊界)的本能。在作者的講述中,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目的是為土生土長的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積累或維護權力和特權。他們有一種“這個國家屬於我們而不是他們”的委屈感(“他們”的例子包括“穆斯林恐怖分子”或“暴力的墨西哥移民”)。懷特海和佩里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即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不成比例地認為移民破壞了美國文化。他們的研究還顯示出有這種主義傾向的人對跨種族婚姻、跨種族收養和執法中種族不平等的敘述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正如上述素描所示,懷特海和佩里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政治願景而非宗教願景。記者凱瑟琳·斯圖亞特(Katherine Stewart)在《崇拜權力的人——探秘宗教民族主義危險的興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一書中也做出了同樣的判斷。她寫道,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宗教信條”,基督教民族主義宣揚的是“美利堅共和國是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被建立起來”的神話。
懷特海和佩里努力追求社會學的精確性,而斯圖亞特則公開敵視這一運動及其目標。她對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警覺”",並一心想要抵制它。有時,她對白人福音派的戒心和陰謀感近乎滑稽。例如,本書以作者講述她在一間浸信會教堂參加一項“家庭研究委員會”活動時決定穿上“軍事迷彩服”(其實是“一件印花裙子”加一件粉色開衫)開篇。
《崇拜權力的人》指責福音派密謀“用一個立足於特定版本的基督教的國家取代我們的基本的民主原則和體制”。按照斯圖亞特的看法,這個陰謀是通過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的宗教自由訴求來推進的。她寫道,保守派基督徒“通過玩弄美國的司法系統來推進'宗教自由'的議程,實際上是為某一種宗教建立一套非常明確的特權。 ”
斯圖亞特的為她自己的研究添上了活動家的色彩,而學者杰拉多·馬蒂(Gerardo Marti)則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基督教民族主義。在《美國的盲點——種族、階級、宗教和特朗普總統任期》(American Blindspot: Race, Class, Religion, and the Trump Presidency)中,馬蒂探討了使美國成為種族、民族和宗教身份交織的沃土的深層動力。他認為,從一開始,界定“真正的”美國身份的努力就與“白人定居者優越性的合法化和建立明確的種族等級制度”密不可分。
馬蒂回顧了許多歷史時刻。這些時刻促使白人和新教成為美國身份的半官方標誌,其中包括內戰後未能保護美國黑人的權利,出於對白人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拒絕接納來自亞洲和其它地區的移民,以及在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中把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定為罪犯。後一項措施導致了今天移民家庭和社區所面臨的許多挑戰。
防范威脅
這三本書都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正在尋求保護,以防止他們的宗教自由、經濟地位和整體文化影響力受到各種威脅。然而,三本書都沒有能完整地講述其中的動機(儘管佩里和懷特海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種族的態度存在著很深的問題)。而在分析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主義的委身的過程中,這幾本書的作者們也背叛了自己的對真實的委身,這使得他們的判斷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偏差。
在宗教自由的話題上,斯圖亞特大錯特錯地將宗教保守派的主張框定為“滲透”司法機構、為宗教目的彎曲法律的陰謀。她從根本上歪曲了保守派法律努力的規模與反對它的團體的規模的相對關係。而且她沒有區分為宗教團體和個人活出信仰開闢空間的努力和將這宗教信仰強加於多元社會的企圖。
佩里和懷特海雖然分析得比較謹慎,但也陷入類似的困惑。他們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為一些基督教標誌在公共生活中尋求特權地位,因為後者認為其它宗教的信仰者(及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對美國作為基督教國家的地位的威脅。由此,作者得出結論: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詞典中,宗教自由只包括“做基督徒的自由”。但在公共場所展示基督教的標誌是否違反任何國家中立原則,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在2019年的一項涉及布蘭登斯堡(Bladensburg)十字架(一個政府土地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的裁決中,最高法院(以7票贊成、2票反對)裁定,一些宗教符號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產生世俗的含義,這樣的結果似乎是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實際希望看到的。
更明顯的是,佩里和懷特海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通過援引宗教自由作為“歧視性取向和性別少數群體”的藉口,來應對社會對婚姻和性的看法的變化。然而,他們的論點不僅僅是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宗教自由的理解的不一致或不連貫的問題。他們所用的負載太多含義的語言(如“歧視”)只是預設了涉及性取向或性別衝突的案件不應該以有利於宗教傳統主義者的方式解決的立場。
某些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強烈感受到的另一個威脅是失去經濟上的安全。馬蒂在書中批判了白人工人階級對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的移民的不滿。但他的分析從裡根總統任期直接跳到茶黨時代,忽略了理解這種怨恨的來源(無論合理與否)所需的(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關鍵時期。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工人階級穩定的基礎。特朗普獲得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誓言要支撐這些工作崗位。
馬蒂對資本主義持極端批判態度。他也敏感地意識到,福音派有時是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與上帝的照管等同的。然而,儘管他承認白人福音派多半“處於經濟光譜的中低端”,但他仍然不承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他們的吸引力。特朗普的經濟綱領背離了資本主義的玩法,攻擊企業通過將工作轉移到國外(尤其是中國)掏空了工人階級。你不必排除對移民的擔憂中可能有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但你可以承認這種擔憂可能有其它更值得同情的動機。
被焦慮包圍
然而,歸根結底,對威脅的感知是超越任何一個政治或文化議題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思想中瀰漫著一種焦慮的氣氛,擔心寶貴的東西被人奪走。正如這幾本書所指出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數量正在減少,文化影響力也在消退。白人福音派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受困的少數派。但2016年標誌著一個轉折點。他們沒有團結在一個在廣泛意義上跟他們目標一致的候選人周圍,(譯註:指希拉里也是一名廣義上的福音派基督徒)而是選擇了特朗普和他赤裸裸的保護支持者免受敵人攻擊的承諾。
這樣的焦慮根源於福音派自身的感情。我們是一群在每次佈道結束時都會聽到悔改信主的呼召的人。我們的敬拜“經歷”往往浸透著情感的狂熱。翻譯成政治術語,就是我們對宗教生活的熱情往往會流露為過分火爆的言辭。隨著政治危機感的加劇,許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加強了對各種形式的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委身,以及對支撐它們的文化和歷史神話的迷信。斯圖亞特正確地觀察到,在經濟不穩定和其它被認為是混亂來源的背景下,基督教民族主義為其信徒提供了“信心、身份,以及他們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安全的感覺”。
但我們很難說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是唯一被焦慮困擾的人群。這些書的作者們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他們自己的不安——不僅是對熱忱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而且是對任何自信的、基於宗教信仰的政治行為。馬蒂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由於“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充滿信心”,只歡迎“不挑戰他們的前提”的政治夥伴關係。懷特海和佩里也譴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所謂的教條主義,稱其“作用是抑制任何妥協的機會”,“不允許有其它觀點的可能性”。在斯圖亞特的理解中,美國不是陷入了一場文化戰爭,而是陷入了一場“關於民主未來的政治戰爭”。
然而,在拒絕宗教教條主義的同時,這些批評者卻有意無意地為它設置了一個世俗的對手,而後者的前提同樣是不可妥協的。斯圖亞特的“民主”理想似乎不過是多數人意志的粗暴主張。她聲稱,基督教右翼是“好戰的少數派”,但她的書卻高揚“我們現有的多數派”,它(帶著不祥的徵兆)應該得到“它所應得的權力”。
在這種擔憂的背後,是一種過於狹隘地關注權力的政治觀念。在這樣的框架下,某種信念是否真實的問題被安全地擱置到一邊,或者靠引用一些嚇唬人的話不屑一顧。例如,馬蒂提出,“對理想秩序的強制推動”不是源於理性的考量,而是“源於一套嵌入體制結構中的價值觀和話語”。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任何建議——比如降低移民率的建議,都不需要就其優缺點進行辯論,任何建議都可以被當成永久延續不公正的“結構”而得不到聽取。批評者指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顛覆民主準則,但將政治約化為生硬的強加權力也會帶來類似的危險。
傾聽與學習
福音派基督徒到底應該如何接受這樣的書?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尤其是因為福音派與這些作者所描繪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有著複雜的關係。
許多福音派——在被特朗普分裂的兩邊都有——至少會在這幅畫像的一部分中認出自己,即使他們與基督教民族主義最醜陋的傾向保持距離。畢竟,持有傳統的愛國情結而不神化國旗是可能的;承認猶太教-基督教對美國建國的影響而不把憲法當作神聖的啟示是可能的;加強宗教自由而不把非基督徒排斥在其祝福意外時可能的;同情白人工人階級的掙扎而不妖魔化移民或其他種族的成員也是可能的。然而,這些書所編纂的論點和證據,不能僅僅通過斷言白人福音派教徒不存在他們所描述的問題而被拋開。
這些書並沒有拿一面鏡子來反照保守派基督徒,而是通過一套帶有偏見的鏡片來折射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用謹慎、有愛心和謙卑的態度來閱讀它們。即使沒有別的理由,它們也暴露了潛伏在某些白人福音派團體中的盲點(借用馬蒂的書名)。認真傾聽有助於我們認識到那些從根本上與福音不相容的意識形態,並將自己從這些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這也能夠表明我們願意給予批評者得到公平的傾聽的機會,即使他們的批評本身不夠寬厚。
歸根結底,在商議性的民主制度下生活意味著我們不得不互相傾聽–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願意互相學習。如果我們想讓懷疑論者相信我們可以在遵守民主的規則的同時,在公共廣場堅守基督教真理的宣稱,那麼我們就必須從傾聽開始。
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是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是“如此基督教”(Mere Orthodoxy)的創始人。
翻譯:田禾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translation? Want to see CT do mo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u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Share your feedback here. Follow our best articles on Telegram or WhatsApp (English). 在WhatsApp上關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