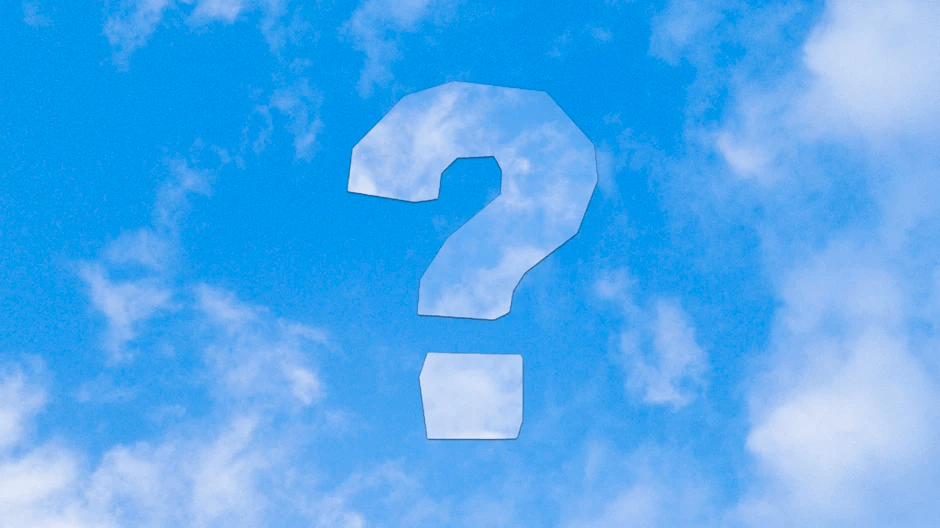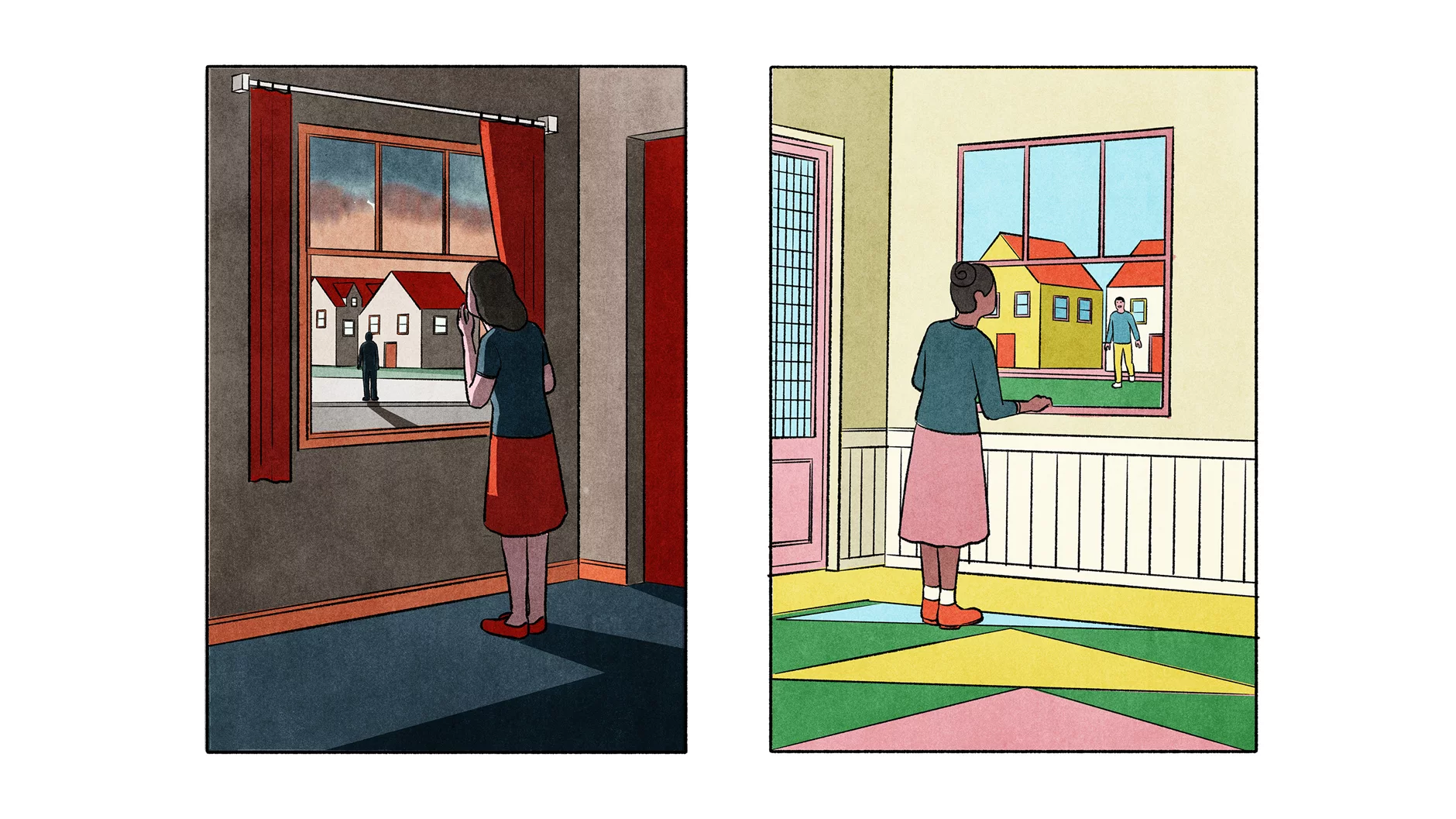今日,人們因為感到宗教裡的虛偽而懷疑自己的信仰並離開教會,已不是什麼秘密了——甚至最近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這一點。
這個不信上帝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注基督徒的信仰和行為是否相符。如果說近年來我們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僅僅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不一定意味著我們會去做」。
當然,這種虛偽並非宗教人士獨有。
我的姐姐是名護士,有一次,她正要離開醫院的時候,經過一些她認識的肺科醫生。他們站在外面抽著煙。她感到非常諷刺:這些醫生對肺病和吸煙的毒害瞭如指掌,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抽菸。
同樣的,在遵行上帝的心意方面,我們的意圖和行動也是天壤之別。然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卻認為,只要我們思考真理、神學化真理、談論真理,我們就是在遵行上帝的心意。這是錯誤的。對上帝心意的理性認識並不等同於真實的信仰,除非我們將這種認識付諸行動。
因為我們的「存在/實質生命」深受我們的「行為」的塑造,而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我們的存在能形塑我們的行為。例如,我們可能知道我們應該信靠耶穌,但這與我們主動去信靠祂是不同的。「想要」順服上帝並不等同於順服祂。正如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14:15)。
我們與他人的親情源自於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因為上帝讓我們成為守護我們兄弟姊妹和地球的人。這是祂的計劃。這不是一個關於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實際體現的問題:真正把我們自己放在對方的視角來看事情。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將目光投向基督——像祂一樣去行動、去理解、有祂的生命樣貌,並透過祂的眼睛和心思來過濾我們所有想法、行為和態度。透過效法基督,我們開始理解祂,我們的存在/生命本質也在這過程中改變。而當我們變得更像基督時,我們就又能更好地以祂看待和對待他人的方式來看待和對待他人。
我們對待他人的態度和方式會清楚地展現我們生命轉變的程度,以及遵行上帝心意的能力。對於那些和我們一起生活、工作和玩樂的最親近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善待那些和我們較少來往的人,比善待經常和我們有所互動的人更容易,畢竟後者更有機會踩到我們的紅線。
對我們的愛心的真實考驗在於,當沒有機會「展示」敬虔時,我們會如何對待他人。
無私的愛的反面就是我所稱的「Invictus-ing(無法被征服)」——也就是威廉·歐內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的著名詩詞《Invictus》裡描述的那種自我神化的姿態:
我為我無法被征服的靈魂
感謝諸神。
……我是命運的主宰、
我是我靈魂的船長。
這種自我統治的態度讓我們偏離上帝的心意,與死亡糾纏在一起(詩篇18:4),並可能會在我們的行為裡帶來破壞,讓我們為此付上代價。
如果我們真的愛上帝,如果耶穌確實在我們心中,那麼,當我們鄰舍的生命沒有蓬勃發展時,我們應該會感到難受。因為「凡自稱愛上帝卻恨弟兄姊妹的,就是說謊的」(約翰一書4:20)。
但是,僅僅在想像中愛我們的鄰舍是不夠的。如果有人詢問他們,我們的鄰舍會作證我們確實關心他們嗎?
不久前,我教授一堂大學生的課,當天的主題是墮胎。我向學生解釋墮胎的來龍去脈,談到墮胎診所的數量以及「存活能力」的概念。我也強調了在美國不同地區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
我每次教授這個主題時都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學生們都不會對嬰兒的人性(humanity)有所爭論,儘管他們可能會對生命從何時開始產生分歧。我總是鼓勵學生傾聽那些在墮胎議題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的意見,而不是互相妖魔化。
當學生們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時,一位學生開口了。她說:「我墮過胎。如果我生下孩子,我完全不可能繼續唸大學。我和男朋友養不起孩子。」全班鴉雀無聲;一些學生低頭盯著自己的桌子或手機,另一些學生則轉過頭來看著這位學生。她繼續說,「我的父母曾試圖勸我不要墮胎。」
然後她把一切都說了出來:
「我問他們是否會在我上學和工作時照顧孩子,是否會買衣服和奶粉,並幫我付保險給付之外的任何費用。我問他們是否會為我孩子的大學學費存錢,並幫助支付其他雜費。我還想知道他們是否會投票支持在孩子出生後為母親和孩子提供更有力的安全網的法律,而不僅僅是投票支持孩子有被生出來的權利。」
然後——靠著我在全班同學面前建立了近一個學期的信譽和信任——我問道:「妳介意告訴我們你父母怎麼回應嗎?當然,如果這個問題讓妳感到不舒服,妳可以不回答。」在我的課堂上,學生總是可以選擇不回答問題,以前也有一些學生選擇不回答特定問題或不參與某些討論。
在停頓了似乎一個世紀之久後,她說道:「他們沒有說太多,只說他們無法承諾做到所有這些事。顯然地,這些代價太高了。所以我墮胎了。就像我說的,我和我男朋友現在養不起孩子。」然後她補充道,「支持孩子有被生出來的權利的人把話說得很好聽,但一旦孩子出生後,他們就不想支持母親和孩子了。」
我無言回應。只能感謝她將如此私密的事和我們分享。
真的,我無法反駁她。她說的百分之百正確。為了使我們支持生命(pro-life)的立場有所信譽,美國的基督徒需要以不同的投票方式來關心母親、孩子和家庭。我們應該監督父親負責,監督我們在法律上的代表,要求制定全面性支持生命的政策。隨著住房、托兒、醫療保健、尿布和奶粉價格的上漲,人們需要更多的安全網。
但這需要我們付出代價。我們不僅可能要繳更多的稅,而且我們之中多數人甚至必須簡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負擔更多費用來支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真正支持生命(pro-life)可能意味著為單親母親提供住宿或幫助她重新站起來,也可能意味著設立一個特別的基金來支持我們教會裡陷入困境的家庭。
愛是以行動為導向的,而不僅僅是談論我們的信仰或我們有「多支持」某樣事物。如果我們繼續讀經和背誦經文,卻不將其應用到生活裡,那我們就會成為雅各在他的信裡強烈提及的那種人:「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什麼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5-17)。
基督教活動家兼記者多蘿西·戴(Dorothy Day)說:「我很早就相信,人們說的話從來沒有一半是真心的,最好不要理會他們的言論,只對他們的行為做出評斷。」我的學生就是這樣做的:根據她父母的行為(或者說,不作為)來評斷。
有時,生活裡最簡單、最基本的事——吃得好,經常運動,睡眠充足,不把日程排得太滿——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最難堅持做到的。因此,我們之中許多人降低標準,接受不佳的健康狀況或身/心失調。為什麼呢?因為健康需要我們付出代價、犧牲一些事、以及改變生活習慣。
同樣的,我們常常降低標準、失去全心全意愛上帝、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所帶來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平安,因為要學會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至少起頭很難,或是在沒有聖靈和智慧的朋友幫助下很難,在有毒的教會文化裡也很難。
但做到這一點是可能的。而且,如果我們希望為下一代恢復基督肢體的見證,這也是必要的。
我的學生認為,墮胎是她當時唯一的選擇,也是她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唯一方式。她不想在貧困中撫養孩子。如果我的學生向我們或我們的教會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該怎麼回應呢?我們的行動是否與我們說的話同步?
瑪琳娜·格雷夫斯(Marlena Graves)是紐約州羅徹斯特東北神學院靈命塑造助理教授,著有《Bearing God》和《The Way Up Is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