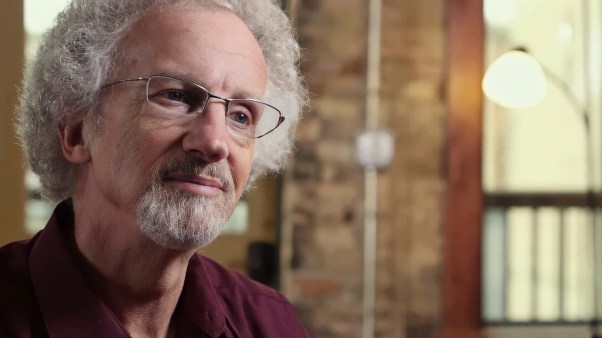近年來,同理心 (empathy) 這個詞很為流行。心理學家布魯姆 (Paul Bloom) 將同理心定義為「像他人一樣體驗世界的過程,或者至少像你以為的那樣去體驗別人的感受。對某人有同理心意思是設身處地地為她著想,感受她的痛苦。」
同理心與同情心截然不同,因為同情心通常是將自己置於他人之上,俯視他們,為他們感到遺憾。同理心則是我們去感受他人的感受,從而消除了身分差異。布魯姆所定義的教科書級別的同理心差不多就在這範圍內。
雖然富有同理心的認知是一件好事,但同理心需要背景和動機,好讓我們以基督的樣式愛我們的鄰舍,並最終跟隨祂舍己的榜樣。
基督教對同理心的理解與基督所教導的兩條最大的誡命有關:「你要盡心,盡性,儘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
當然,這兩種愛是錯綜相連的,因為如果不與愛的源頭——基督相連,我們就不可能以基督的方式去愛鄰舍。
基督教的同理心要求我們既要舍己,並且要是有意為之,因為我們要跨越自己的同溫層和經驗,同理那些被拋棄、被誤解、被虐待的人。當我們忽視或不珍惜所有人與生俱來的「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時,我們並沒有真正的愛上帝。
但這種愛以及與其相應的同理心是很難有的。我們常慣性倚賴刻板印象,忽視他人生命的神聖性,常有先服務和保護自己的衝動。
基督教教導的同理心超越了人類本性,和「僅僅只當一個好人」的最低要求。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歷史上最完整、最深刻的同理心。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我們共同經歷了人性的體驗——包括各種我們經歷過的痛苦,因為祂住在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1:14)。
聖經中有許多基督同理心的例子,但最令人感動的也許是在《約翰福音》里,基督在祂的朋友拉撒路死後的反應:「耶穌哭了」(約11:35)。
基督知道祂將會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所以祂哭泣不是因為祂朋友的生命走到盡頭。祂乃是與我們一同哭泣、為我們哭泣,在拉撒路的姐妹們身旁一同哀痛,感受她們的痛苦以及死亡的詛咒為全人類所帶來的痛苦衝擊。
祂的哭泣是這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憐憫和共情之舉,祂與墮落後的人類因著無可避免的苦難ㄧ同哀悼。在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基督對人類的同理能力達到完全的狀態。
基督擔當了人類的罪,為他們受苦,祂感受到人類的悲傷、絕望和他們自己造成的苦楚。我們與基督不同,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思想或生存體驗,但上帝卻命令我們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別人。
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的行為,我們需要想像力幫助我們彌合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距。
伴隨我們想像力的增長,我們需要一些故事來顯明我們蓄意而為,或是蓄意不作為的罪,使我們不被侷限在自己的視野裡,能看見我們鄰舍那美好而複雜的世界。在向我們顯明如何既認同我們的鄰舍,又彌合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差距時,基督講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同理心的故事,也就是路加福音10:25-37中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你可能還記得,這個故事是回應一位律法師向耶穌提出的問題而講的。就像那個富有的少年人一樣,這個人問耶穌,他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基督用一個問題來回答——祂反問這位律法師,「律法上是怎麼寫的?」。
這位律法師的回答了標準答案:「你要盡心、盡性、儘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回應他:遵守這些律法,就必得永生。
但這對宗教領袖來說還不夠;他想誤導和羞辱耶穌,所以他接著問:「誰是我的鄰舍呢?」
基督回答說,有一個人被強盜毆打後躺在路邊,急需幫助。兩個受人尊敬的猶太宗教領袖——祭司和利未人從這個受傷的人身邊經過,卻無視他的需要。他們不僅無視這個人,而且還故意「從另一邊走了過去」來避開他,畢竟眼不見為凈。
下一個路人是一個撒瑪利亞人,他看到這個受傷的人,就「動了憐憫之心」,不僅為他包紮傷口,還把他扶起來,放在自己的驢子上,把他帶到一家客棧以便照顧他。
他本可以只給他一些錢或處理傷口後就離開。然而他抱起這個人,帶他一起趕路,甚至一起在客棧過夜、照料他的需求。
第二天,他付錢給客棧老闆,讓他照顧這個被搶劫的人,如果照顧的費用超過所付的,他願意付老闆更多的錢。講完這個故事後,耶穌又問了那個考問他的人一個問題:「你認為,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律法師回答:「是憐憫他的人。」然後基督命令他「你去照樣行吧。」
基督命令律法師和任何聽到或讀到這個故事的人,要像撒瑪利亞人那樣,有憐憫的心,走捨己的路,而不是自私利己的路。反思出現在這個故事裡的角色,對我們理解這個故事非常重要:故事裡有兩個備受尊敬的猶太宗教專家,和一個「外國人」——撒瑪利亞人。
正如民權活動家霍華德·瑟曼 (Howard Thurman) 在他關於這個比喻的講道中所解釋的那樣,這個撒瑪利亞人無論從字面上還是象徵意義上都彷彿生活在「另一個地方」:他不僅在種族上與猶太人不同,他的宗教信仰也被認為是異教的、混種的,在猶太人眼中是不體面的。
然而,這個在人看來是被遺棄的人,這個不信教的人,卻是故事中唯一認出了受傷之人的光輝人性的人。宗教領袖們卻不想被這個人的事牽連;也許他們很忙,或僅僅不想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
但撒瑪利亞人卻冒了這個險。他放慢腳步,伸出手,把一個承載著上帝形象的人拉了起來。
本文摘自瑪麗-W-麥坎貝爾(Mary W. McCampbell)的《視鄰舍如同我們自己:藝術如何塑造同理心》,版權歸2022年堡壘出版社(Fortress Press)所有。經許可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