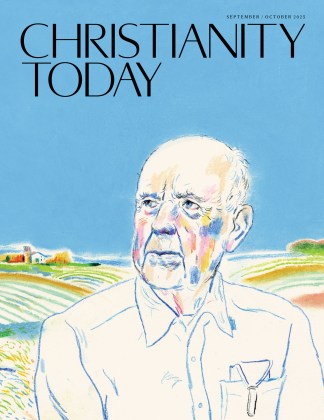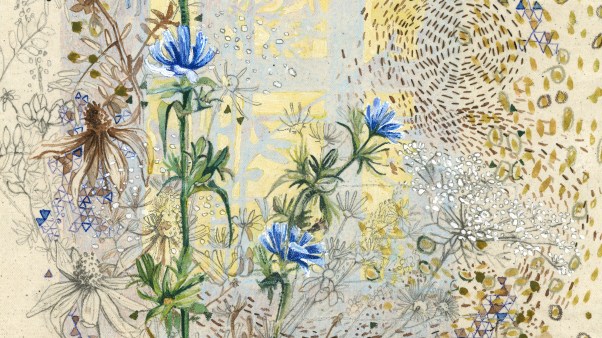我的孩子在學齡前就已接觸到一些我直到成年才遇到的事物。舉例來說,我的大兒子在5歲時就已熟悉大麻的氣味。一次家庭旅行中,當我們經過一名正在抽大麻的青少年時,兒子深吸一口氣,說:「啊,聞起來像家的味道。」
在我自己成長的過程中,父母、牧師,甚至教授們,都警告我要避開各種敗壞的影響:毒品、媒體、某些特定的人,以及危險的思想 (和提出這些思想的作者)。但對我的孩子來說,避開這一切並不在選項中,因為我們住在曼哈頓。他們一定會在街上或地鐵裡遇到令人不安的人。他們一定會遇見不同語言、宗教,以及各種另類的生活方式。身為父母,我需要引導孩子去消化這些經驗,而不是單純隔絕它們。
我從最初那種無法替孩子築起保護罩的狀態,逐漸轉變成正面迎擊地選擇讓孩子看見世界的複雜性。在必然的處境下,催生了一種價值觀:如果我們無法避開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那麼我們就不該避開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最後,我甚至開始對那些刻意把孩子與「現實」隔絕開來的父母,產生一種自以為義的批判態度。
所以,當我們從曼哈頓搬到鳳凰城時,你可以想像我有多驚訝。才搬來幾天,當我帶孩子去郊區的一間超市時,門口有人在乞討。沒多想之下,我帶著孩子繞到另一個入口。我避開了一個在紐約時的我絕不會迴避的互動——因為現在「我有辦法避開」,我就本能地避開了。在新的處境下,我產生了新的價值觀:如果我們能避開Target超市門口的乞討者,那麼我們就應該避開Target門口的乞討者。
在閱讀布米勒 (Brian Miller) 的《將郊區神聖化:郊區如何成為美國福音派的應許之地》一書時,我開始思考:這種傾向於迴避那些在身體、心理或靈性上看似有危害的事物,是一種郊區心態,還是一種「基督徒心態」?米勒身為惠頓學院的社會學家,視這種本能為「郊區文化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被福音派「施洗」後,納入我們自己的文化工具箱。他的書提出一個頗為合理的論點:許多我們以為獨屬於福音派的思維,其實起源於郊區。
隨著美國在20世紀下半葉變得更宗教化,美國同時也變得更「郊區化」。根據《全國社會調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長達45年的數據推估,福音派比其他群體更傾向居住在郊區。事實上,福音派進駐郊區的比例甚至高於一般人口。而那些塑造了福音派在社會、政治與神學上的參與的關鍵機構——包括米勒任教的學校——幾乎全都設立在郊區。
在這一切背景下,如果「郊區心態」沒有影響福音派的信仰與實踐,才會令人感到意外。正如米勒所主張的:「研究人員和評論者,若只考量福音派的神學立場與政治行為是不夠的;要理解白人福音派的整體樣貌,理解他們所處的空間脈絡 (spatial context)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追溯美國郊區的起源與歷史後,米勒提出引人入勝的質性資料來支持他的論點。他追蹤了20世紀芝加哥及其郊區的宗教遷移情況,發現「在1925到1990年之間,所研究的10個新教宗派中有9個宗派的教會變得更加郊區化」。透過繪製全美福音派協會 (NAE) 重要領袖的住址分布圖,他也發現來自郊區的領袖代表在數十年間顯著上升。在該組織1942年的首次董事會議中,僅有15%的代表來自郊區;到了世紀末,這一比例已成長至一半。
米勒綜合多個來源的數據,指出在美國城市整體變得「較不宗教化」的同時,「在更偏鄉和最小型社區中的基督徒比例 [同樣] 在下降,特別是福音派和主流新教基督徒的數量」。福音派正持續變得更不都會、更不鄉村,以及愈來愈郊區化。
米勒也描繪了三個郊區與一個小城市的案例,這些地方的福音派及其相關機構具有異常突出的影響力。這些社區分別在不同年代、不同條件下郊區化。其中兩個社區從一開始就有強烈的福音派身份認同,另兩個則是在近年才成為福音派的熱點。綜合起來,這四個地區匯聚了數千個福音派非營利組織,因此能在更廣泛的福音派群體中發揮超過其規模所應有的影響力。
當米勒談到「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時,這些數據的意涵就更耐人尋味。在社會學裡,「工具箱」的概念用來描述文化如何影響人類行為。文化並非單純提供一套價值觀,而是提供一系列行為的「工具庫」,讓個體可以從中選擇不同的行動路徑。
那些渴望推動社會改變的人,手上各有不同的文化工具可運用。他們可能選擇在「人際關係」的脈絡中說服他人,也可能選擇組織行動,推動法律與公共政策的改革。而文化會影響人們何時認為該採用哪一種工具。例如,歷史上,福音派基督徒面對種族不公時,往往採取人際關係的方式;但在抵制同性婚姻時,則傾向採取立法行動。
米勒的核心觀點是:「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似乎是依據「郊區生活」中常見的模式、經驗與願景調整而來的。他謹慎地避免斷言「郊區規則」與「福音派特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指出其中的動機、方式與機會之間的連結。
接受「較狹義」的米勒論點應該不困難:郊區福音派是在「日常生活的規律片刻,以及與美國郊區社會和物質實況的互動中」中所形塑的。但對許多人而言,要接受「美國福音派整體在本質上就是郊區化的,其價值觀與心態深受郊區影響」會比較困難。
這正是為什麼米勒對「福音派熱點」(evangelical hot spots) 的分析對我來說特別切題。如果大部分的福音派機構——大專院校、神學院、宗派總部、出版公司、植堂與宣教機構、課程公司等等——都位於郊區,那他們的員工很可能也住在郊區或附近。
這意味著,福音派基督徒的課程設計、研究問題與教學大綱,都可能受郊區師生所感受到的「需要」與「興趣」所塑造。出版商在掌握福音派讀者的脈動時,或許也會自然地以郊區經驗作為市場需求的基準。大型郊區教會經常成為教會課程、門徒訓練方法與牧養「最佳實踐」的範本。而關於教養子女、個人理財之類的建議,往往預設「郊區的社會現實」是普世適用的常態 (norm)。
總體而言,米勒認為,這些機構將一種根本上屬於「郊區」的視野,包裝並處方為一種「客觀上的基督徒視野」,進而引導福音派在所有環境下的信仰與實踐。對我而言,這一點並不牽強。我的事工經驗與專業工作,主要涉及鄉村與都會的教會。這些地方的牧師常哀嘆,他們所依賴的資源,明顯是根據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所設計的。至少可以這麼說:美國的事工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郊區經驗」所主導的。
《將郊區神聖化》是一部細緻嚴謹的學術著作。它避免了對郊區的刻板印象,並承認郊區在歷史、人口與宗教身份上的多樣性。它也提出一些明顯超出書本範圍、需要其他學者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涉及「種族」。米勒將「福音派新教徒」與「白人福音派」視為同義詞。將「(白人) 福音派新教徒」與「黑人新教徒」區分開來,使米勒能比較宗教與人口學的數據。這種做法很有幫助,因為它能具體指出:第一個群體比第二個群體在更大規模上逃離芝加哥並移居郊區,也顯示「白人外移潮」促成了郊區更具福音派色彩的現象。
然而,將「白人」與「福音派」劃上等號,對於解釋亞裔與拉丁裔福音派在這個故事中的角色 (無論在歷史脈絡還是未來發展) 就顯得力道不足。非白人福音派的人數正在增加,而郊區本身也日益多元化 (當然,並非所有美國郊區皆如此)。我很好奇,在這個更廣泛的種族意義下,「種族因素」將如何影響郊區與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
關於階級,我也有類似的疑問。我們在曼哈頓的經驗顯示,只要有足夠的資金,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替孩子築起保護罩。那麼,郊區圈內的經濟差異又將如何影響主導性的文化工具箱?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福音派郊區化的「完整範圍」。更深入的歷史檢視,也許會揭示郊區經驗對福音派的影響超越郊區的界限。例如,米勒的歷史回顧回溯到18世紀的倫敦,用以說明「人們對郊區日益增長的興趣,以及遷入郊區的宗教動機。」
倫敦西南部的克拉珀姆 (Clapham) 郊區,在18、19世紀是「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 的所在地。這群福音派聖公會成員包括推動廢奴法案的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以及其他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社會改革者 (這是文化工具箱中的一項);他們也把家庭遷往郊區,以避免工業化後都市生活所帶來的「腐蝕效應」(這又是工具箱中的另一種工具)。普萊爾 (Karen Swallow Prior) 在《福音派的想像力》中有力地指出,當代美國福音派的價值觀,其實承襲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價值觀的悠長陰影。而這些價值觀,很可能最初就起源於倫敦郊區,之後再被輸出到世界各地。
美國福音派一直都是一個多元的運動。無論我們嘗試闡述大家的共同點 (如David Bebbington提出著名的「四邊形」理論),或我們之間的分歧 (如Michael Graham提出的《福音派的六種分裂》),福音派往往專注於明確的信念與價值。米勒的社會學取徑,為這些分類帶來了急需的深度與維度。例如,我懷疑那些認為社會公義 (social justice)「對福音造成威脅」的福音派,與那些視社會公義為「福音本身的使命」的福音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區。若要理解為何福音派會在社會與神學的根本議題上出現分裂,未來的研究應該效法米勒的路徑,去追問:這些人住在哪裡?這樣的居住處境對他們帶來哪些影響?
當英國國會下議院在德軍空襲中被摧毀,需要重建時,邱吉爾堅持新建築要保留原本的格局。他認為,空間的配置會決定其中發生的治理型態。他曾說:「我們塑造了建築,之後建築又塑造了我們。」
美國福音派世世代代都高聲宣稱,要積極塑造我們所居住的環境。但或許現在是時候,更批判性地思考:那些環境又是如何塑造了我們。
Brandon J. O’Brien,是「Redeemer City to City」事工的全球思想領導資深主任,曾與Randy Richards合著《用西方眼光誤讀聖經》(Misreading Scripture with Western Eyes)。他與家人現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