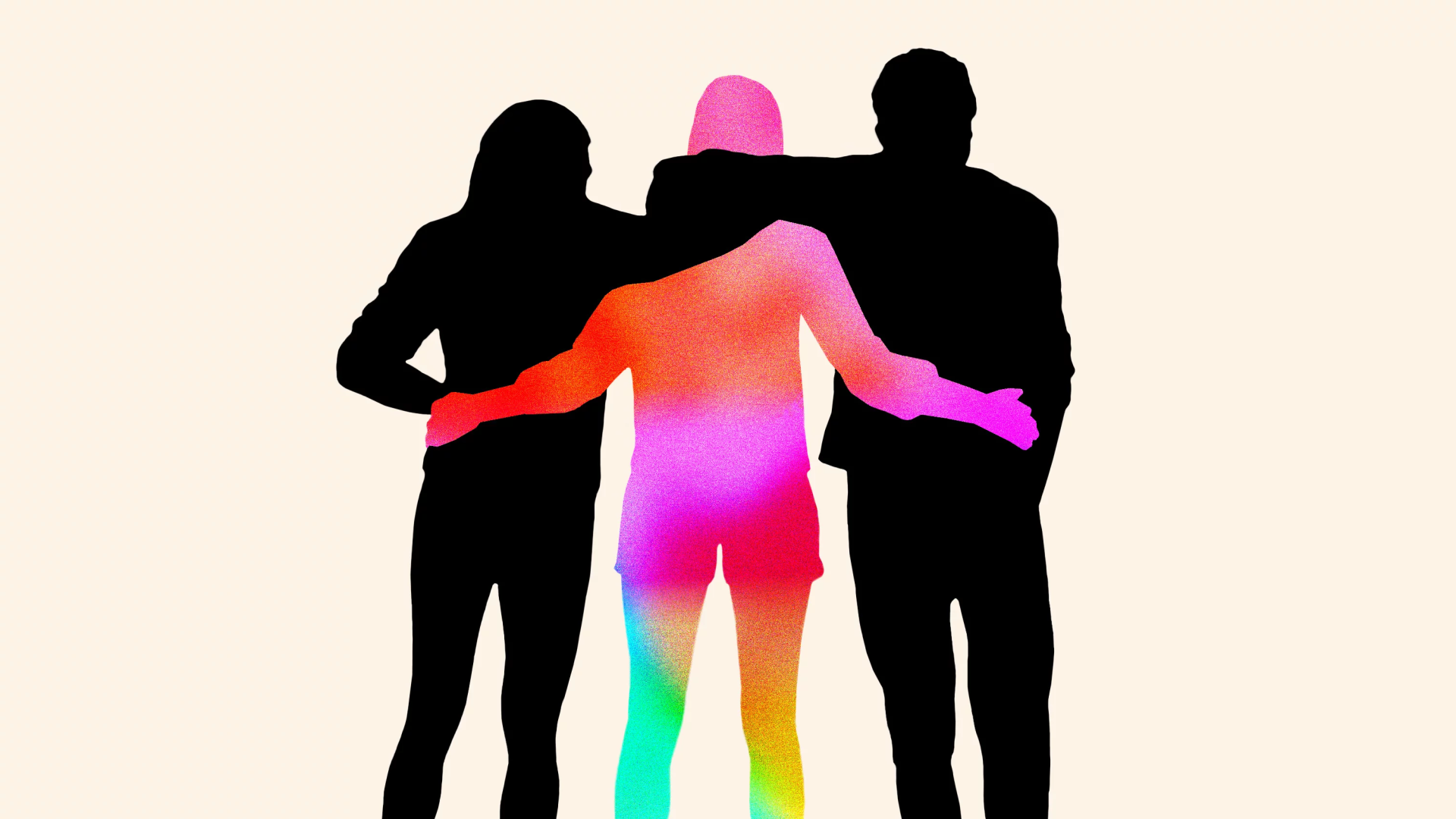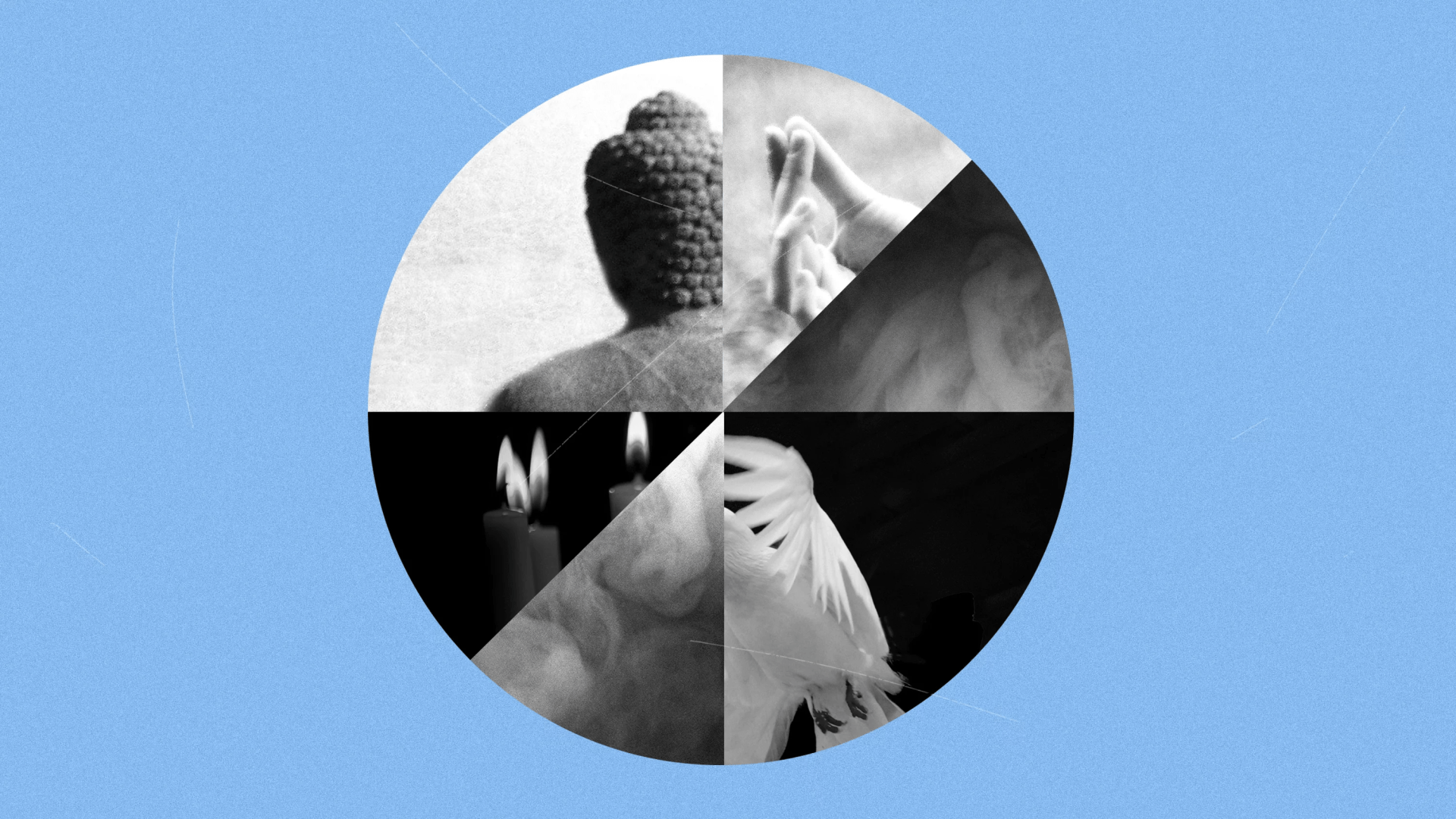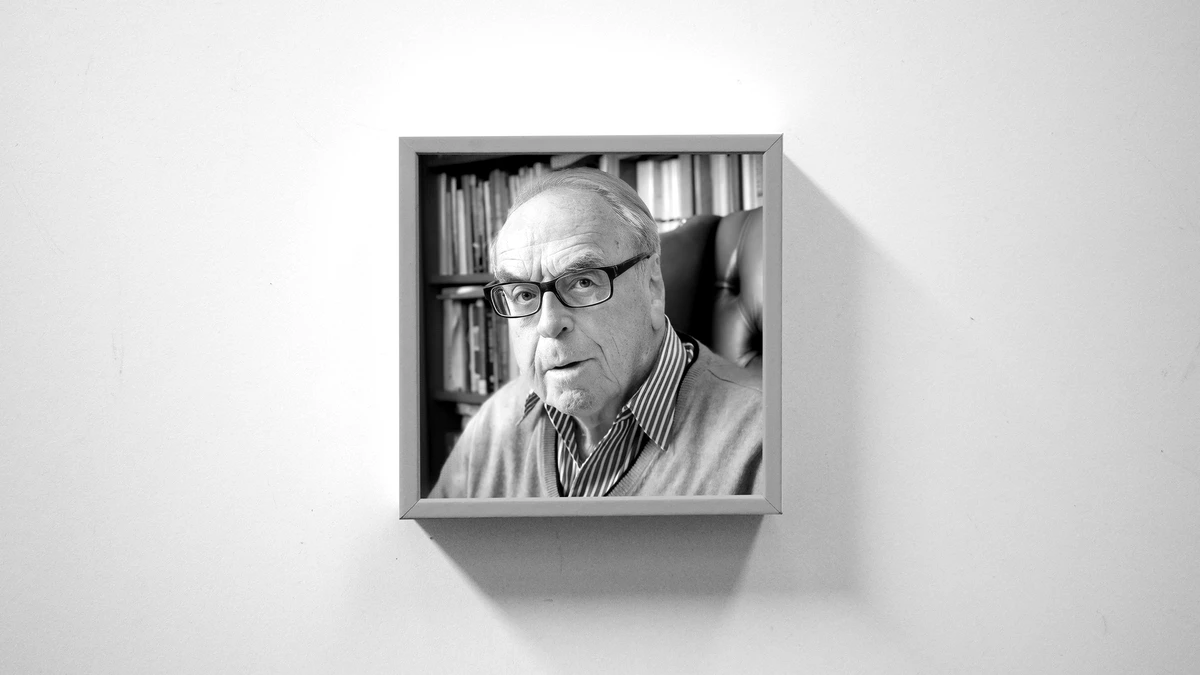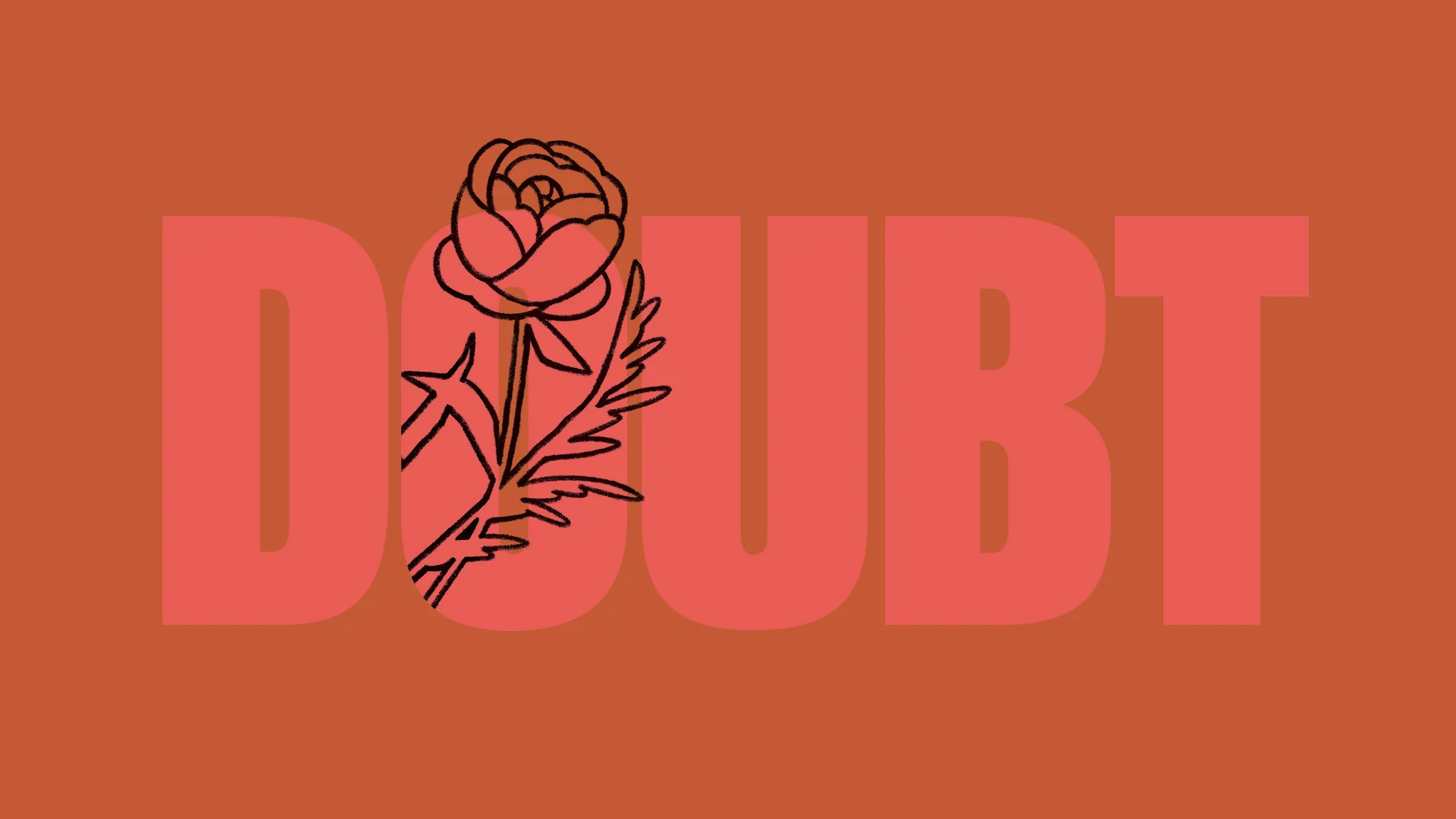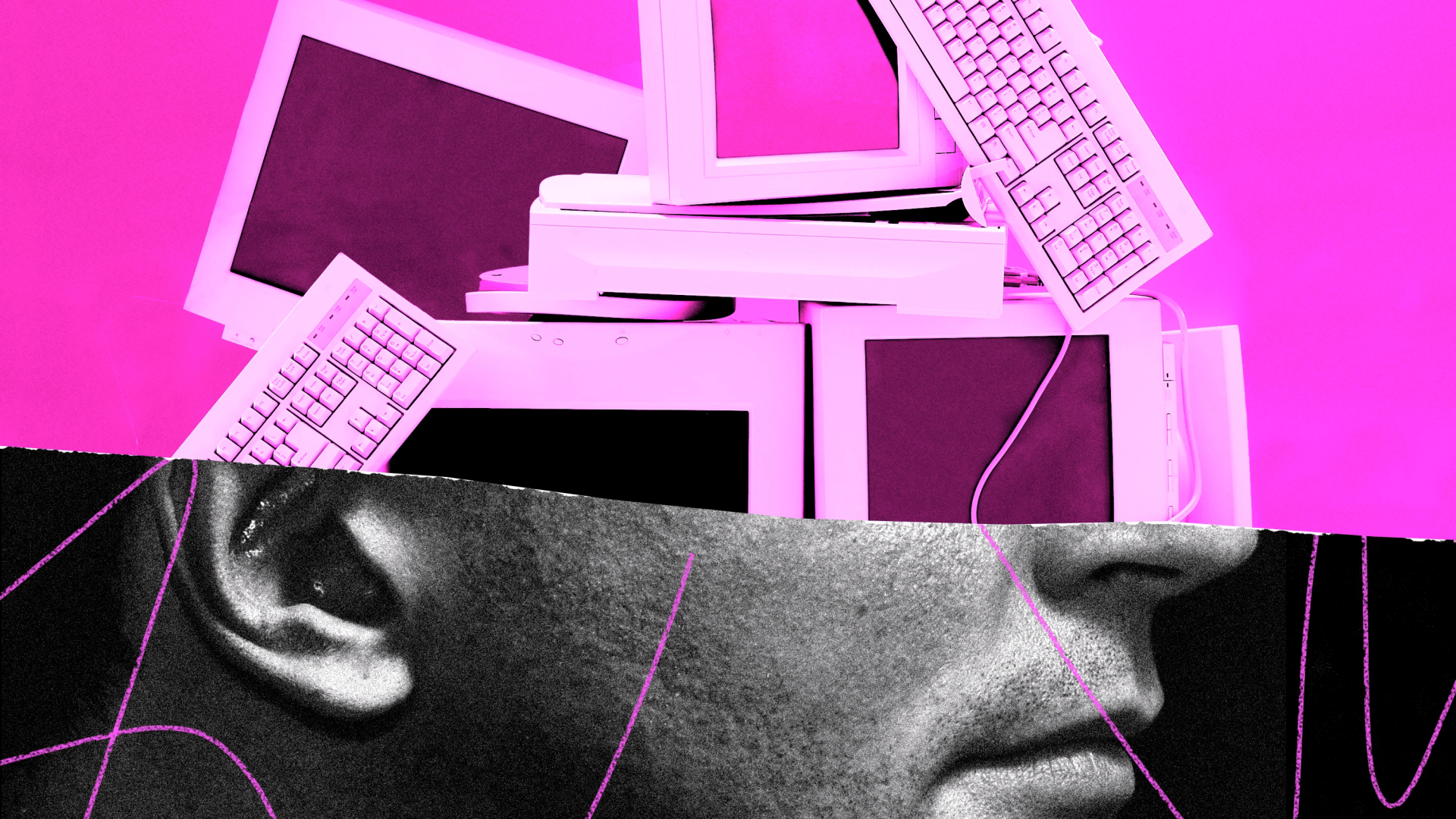當我們全家從華盛頓州搬到加州時,我的父母讓我和弟弟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尋找新教會可能會需要一些時間。但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天,我們就愛上一間新教會,15多年後,我們全家仍在那裡聚會。
離家去外州唸大學時,我盼望同樣的事也會發生。然而這次的情況卻完全相反。事實上,直到六個月前,我已經有六年沒有穩定地在一間我稱之為家的教會聚會了——而這是許多Z世代基督徒常見的經歷。
如今,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參加教會聚會的次數比COVID之前少。美國生活調查中心(Survey Center on American Life)在2022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COVID似乎已使那些原本對定期參與宗教活動的意願最薄弱的人——包括年輕人、單身者和自由主義者——完全停止參與教會活動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美國人。
在我尋找教會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自我懷疑的想法中掙扎,不知道自己是否才是問題所在:我是否太挑剔,對教會期望太高了?我是否是因著膚淺的原因而不喜歡某些教會?在當時的我看來,我之所以還沒有找到能稱之為家的教會,是因為在我的大學生涯中,有許多合理的因素同時發生。
大一的時候,因為沒有車,我感覺自己靠著公車試過幾百間不同的教會。大二和大三的時候,COVID席捲而來,我改為參加家鄉教會的線上禮拜。到了大四,我下定決心要找到一間歸屬的教會,並且不再奢望它會是一間和我家鄉教會相似的教會。
我開始通勤40分鐘到市區,尋找一間由各式各樣背景的基督徒組成的豐富社區——無論是種族、世代和社會經濟層面上。我決定無論要走多遠才能去到我所愛的教會,我都要委身於它。但我很快意識到,如果只有你一個人住在很遠的地方,要想融入教會群體是多麼困難的事——我無法像其他住在教會附近的成員那樣下班後路過教會和人一起喝杯咖啡。
與此同時,在一個又一個星期天過去後,我依然感受到「無家(教會)可歸」的孤獨感。
對我而言,找教會之所以這麼難,常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我拜訪的教會群體同質性很高,而我迫切希望能在一個多元的群體中學習和接受挑戰。其他原因則更為明確:例如,其中一間教會在收奉獻時播放嘻哈樂;另一間教會的網站使用人工智慧機器人來「帶我參觀」教會,但若我想更多了解關於教會的領導團隊和社區參與的訊息,則需要加入他們的Slack頻道(編按:Slack為美國公司常見的內部訊息app)。在我嘗試的另一間教會中,牧師在台上隨口說了一句話,但那句話對我而言是個巨大的紅燈警訊。
有些教會則讓我無法全然信任,部分原因是它們與陷入醜聞或否認教會內性侵事件的教派有連結。不幸的是,在這個時代,加入教會往往需要在信任教友和保持警覺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尤其是身為一名年輕女性,我希望有個地方能讓我安心地展現脆弱的一面。
即使我知道當整個教派掙扎於追求公義和問責的時候,仍有個別教會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該如何知道哪個聚會點或教會領袖不會成為下一則醜聞的主角,或者我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研究表明,有這種擔心的不只我一人。根據巴納(Barna)於2022年的一項研究,27%的人表示自己對基督教的質疑源自過去在教會機構內的經歷。根據統計資料及仿間的言談,我認識的許多Z世代年輕人都很擔心,在發生如此多醜聞以後,教會似乎已不再是個安全的地方。
關於人們不委身於一間教會的另一個常見原因是:在我的年輕人社交圈中,我聽到很多人表示自己只是「還沒找到一間與自己在所有信念上相同的教會」。
關於這一點,我想起魯益師(C. S. Lewis)在《魔鬼家書》裡發出的縈繞著我心頭的警告——「魔鬼」在信中對牠的門徒說:「你們肯定知道,如果我們無法治好一個人「想去教會」的毛病,下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忙於四處尋找『適合』他的教會,直到他成為教會的品嚐師或鑑定家。」
我也聽說有些人根本不認為教會是基督教信仰的必要條件。正如丹尼爾·K·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所寫的:「如果『不再去教會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對信仰的錯誤理解,而是福音派的神學本身缺乏對教會的重視呢?」威廉斯的論點是,福音派需要重新建構一個令人信服的教會神學──為「為什麼要去教會?」這個問題確立一個獨特的福音派答案。
對我而言也是一樣的,孤獨的謊言同樣無所不在。我有一段時間乾脆不再尋找教會了,我告訴自己教會不是必須的。有時,我引用馬太福音18:20來說服自己:當我與兩個或更多的人奉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時,我總是「在教會」。
在這一點上,就讀於一間基督教大學是把雙面刃。當你經常被基督徒群體包圍時,不加入一間地方教會似乎特別容易發生——畢竟你每週參加三次學校的禮拜,每天學習聖經課程。但每當別人問我去哪間教會聚會時,我總是感到羞愧,覺得自己是個不稱職的基督徒。似乎與地方教會的連結是檢驗我靈命健康的最終試金石。
然而,這些藉口都無法解決我對基督徒群體的深切渴望。無家(教會)可歸的狀態很孤獨,也是仇敵把謊言塞進我們心中的一個脆弱的攻擊點。撒旦知道尋找教會是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我們需要信心堅持不懈地尋找一間健康、能挑戰我們服事他人的心志,使我們在屬靈的道路上成長的教會。這就是為什麼撒旦經常「鼓勵」我們對教會冷漠或不再在乎教會,使我們遠離對神和基督徒群體的渴望——這一切再加上孤獨感,便是打擊我們靈魂的強力組合。
而教會終究是我們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何況,實體的敬拜聚會可以提高我們整體的健康狀態、降低我們的心理壓力。但是,克服「無家可歸」的問題需要時間、精神和情緒上的耐力。我們之中許多人很難有韌性地面對它——尤其是年輕的社青或單身者。
然而,在這種掙扎中也可能隱藏著祝福,如羅馬書5:3-5所形容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我最感激的事是,上帝在乎我們的苦難,祂親自看顧在苦難中的我們。
幾個月前,就像曾經嘗試了無數次那樣,我獨自一人走進一間新教會——即使我每一根神經都呼喊著「我再也不想自己一人走進一間教會了」——就在那時,我聽到腦海中一個寂靜而微小的聲音說了一句讓我立刻感到平安的話:「教會應該是個最能讓人安全地獨處的地方。」
從那以後,我參加這間教會的連結班,報名加入小組,並加入他們的婦女事工。我寫下每週遇到的每個人的名字,以此來提醒自己:我為「尋找基督徒群體」所做的禱告已得到了回應,這個星期天,我將帶著聖經和筆記本、我的優先事項清單,以及ㄧ顆開放的心坐在會堂裡——我身旁的「陌生人」將比上禮拜再少一些——我禱告這裡將是我紮根並茁壯成長的地方。
當我每週繼續出現在這裡時,上帝持續地向我彰顯祂的信實。每個星期天,我都感謝上帝賜給我對抗靈裡孤獨的力量;當我越投入在教會裡,我的孤獨感就越少。除此之外,我也感恩能有機會看到上帝的國度在我周圍運作,並遇見其他與我一樣,儘管有著自己的困擾/障礙,仍因獨特的原因每週出席教會的人。
這並不是說,再也沒有哪個星期天早上我感覺自己「不怎麼想去教會」。但當我回顧生命中一些最艱難的時刻時,當我發現當自己身邊沒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基督徒時,當我感覺自己離神最遠時——我走出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當我決定再給教會一次機會時。
事實上,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時刻,我仍然堅持著信仰的唯一原因是我知道有其他基督徒在為我禱告。在我對上帝感到不滿,或對我們這個罪惡的世界感到沮喪的日子裡,我知道有人在為我能重拾盼望而禱告。
因著這些生命歷程,我想提醒那些飽受教會無家可歸之苦的人,尤其是我的青年人及單身的同胞們:你們並不孤獨。並且,你們不必滿足於這種孤獨。你們可以頑強地、有韌性地持續尋找,直到找到上帝應許你們的那個家。
每當我們下定決心並努力在星期天早上參加教會聚會時,我們「出現在上帝的殿堂裡」意味著魔鬼沒有治好我們「想去教會」這個毛病。
米婭·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編輯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