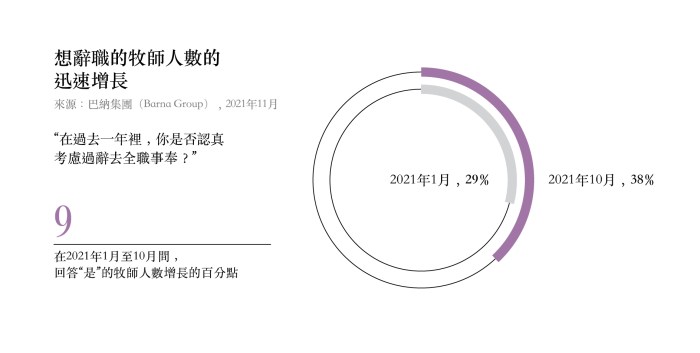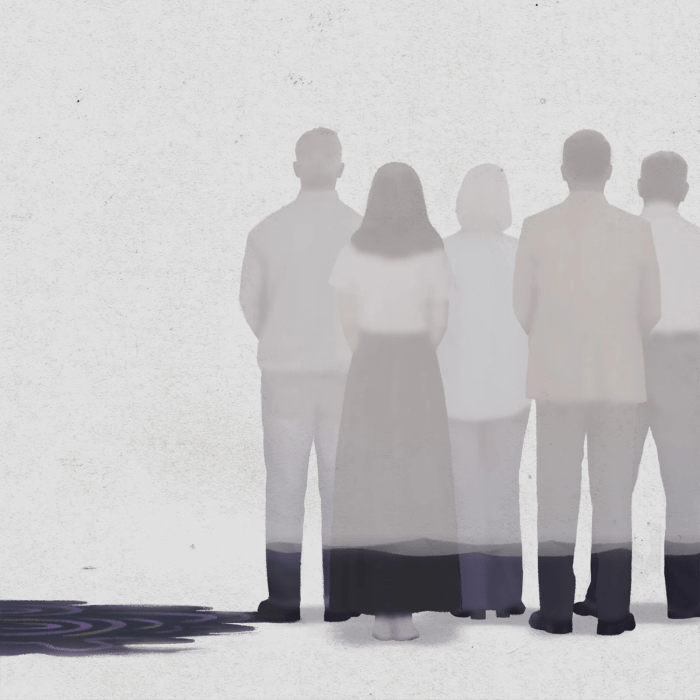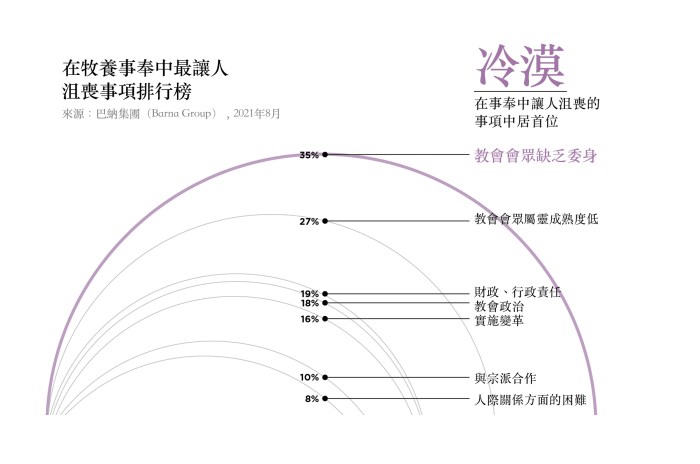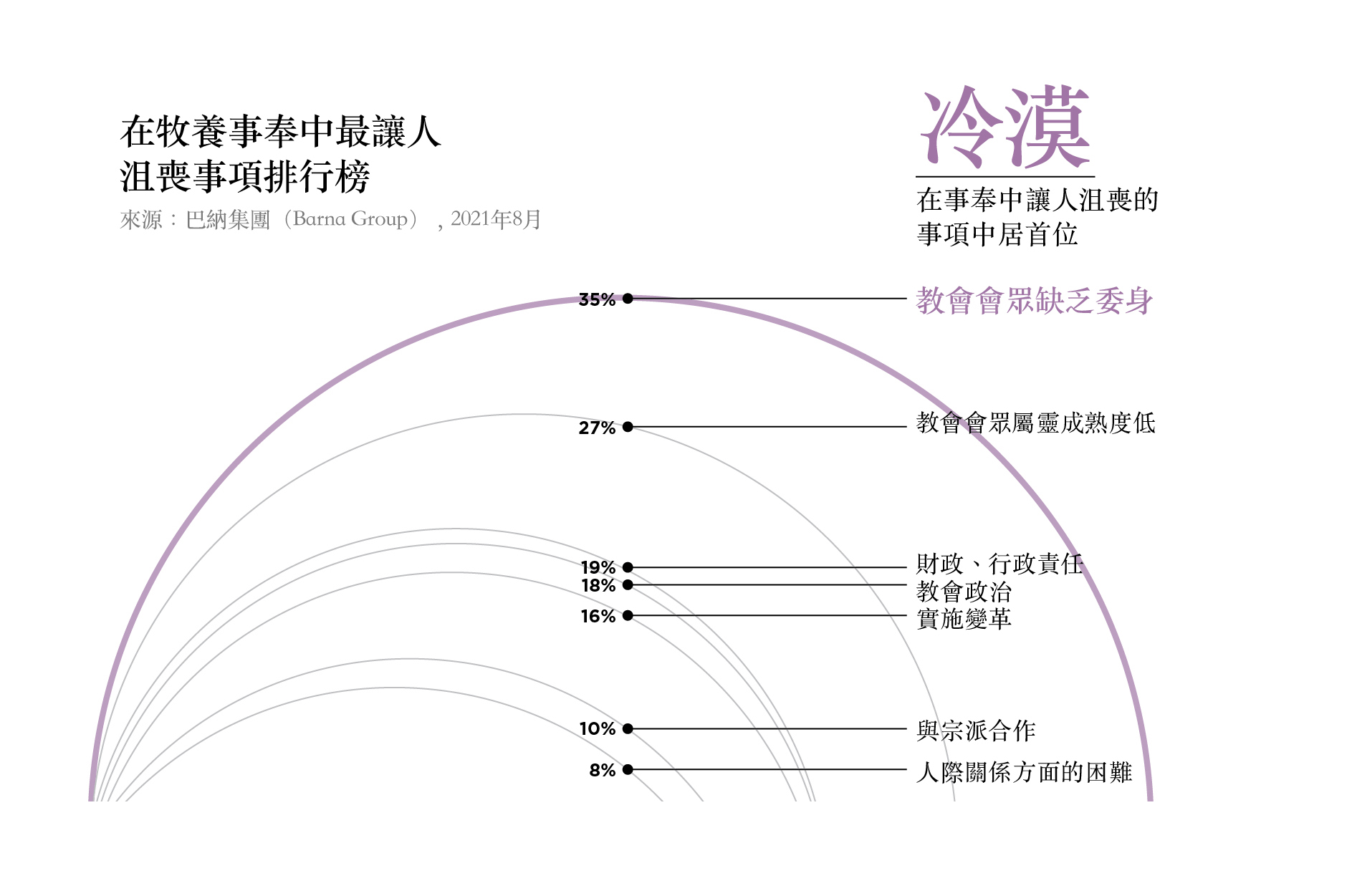當特蕾西·菲克森(Tracey Fixen)自願擔任她教會的主日學校長時,情況就像一塊乾淨的石板。 當時在北達科他州科爾法克斯(Colefax)的路德會“我們的救世主教會”(Our Savior’s Lutheran),從來沒有宗教教育計劃。
她說:“我開始時說,‘我們要看視頻,這樣,我們會有一些成人教育。’”。 這個擁有200人的教會現在每周主日崇拜前的一個咖啡時間提供課程。
菲克森說他們擁有的材料許多都是“過時的”——購買新材料不在當時的預算之內——但舉辦某種形式的主日學比許多教會目前做的要多。
隨著美國教會的出席率 仍然停滯不前 ,和會眾的焦點轉向查經班或小組,週三晚上或周日早上的宗教教育課程很多已經消失了。
此外,在COVID-19瘟疫期間,這些額外的聚會被擱置。 他們會回來嗎?
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的新數據 顯示,接受調查的教會中有一半報告說,他們的宗教教育計劃在過去兩年受到嚴重干擾,儘管福音派教會沒有像主流、天主教和東正教會眾那樣受到影響。
大多數教會在2021年提供較少的宗教教育課程,有四分之一的教會在今年3月之前彌補了部分損失。
研究人員這樣寫,在接受調查的會眾中,“有一些把課程合併和把年齡組合併,而另一些取消了周日課程,轉移到平日晚上全家的活動。 對一些教會來說,這些決定可能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但對另一些來說,它們可能是因為有需要應對不斷減少的人數。”
研究發現,大約六分之一的教會要麼在瘟疫之前沒有提供成人教育計劃,要麼已經停止了這些計劃。 它說,缺乏參與可能最終使主日學在更多的會眾中“不再可行”。
佛羅里達州薩尼貝爾島的薩尼貝爾社區教會(Sanibel Community Church)的副牧師道格·胡默(Doug Hummer)認為,主日學加上每周的敬拜聚會,是教會遵循《聖經》裏的命令,有關教導和門徒訓練的核心方式。
他說:“教會是門徒訓練的地方 … 就像在《太福音》28章說的,要使人做門徒,教導他們,訓練他們,給他們施洗。 如果你去掉門徒訓練的成分,你有教會嗎? 因為這就是教會與任何其他組織不同之處——我們被神的靈賦予能力使人做門徒,教導、訓練和裝備。”
教會還舉辦小組和查經班,但胡默說,他相信宗教教育課程是教會使命的必要組成部分。
在教會實施宗教教育課程的挑戰歸結為財務,資源,可用性,優先事項和時間——除了常規的教會聚會和小組外,每周加上另一項承諾。
雖然教會從 COVID-19 引起的出席率下降中恢復過來,但要忙碌的會眾報名可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但保羅·全(Paul Jeon)說,與其他聚會相比,主日學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這位華盛頓特區郊外的新城教會(NewCity Church)牧師說:“當有人來上課時,這並不是分享你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的場所。 上課的目的是學習一些東西 – 無論是技能還是特定內容。”
像許多其他會眾一樣,新城也很難找到人來領導小組或教主日學。 全說,許多人被嚇倒了,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來擔任這樣的職位。
據蓋洛普 報導,瘟疫也嚴重影響了全國的教會志願者人數。 年長的成員是 一些最忠誠 的主日學教師,他們有理由對COVID-19期間的實體接觸特別謹慎,有些人仍然對教導尚未接種疫苗的年輕孩子猶豫不決。
志願者短缺會嚴重打擊小教會。 在哈特福德調查中,少於50人的教會的成人教育計劃下降幅度最大,而大型教會的課程在增長。
在密歇根州羅克福德(Rockford)牧養80人會眾的克裡斯·麥諾(Chris Minor)說,周日晚上在他的教堂裡,他的教會致力於一種較休閒和教育性的風格。
麥諾說:“我並不是講另一篇信息,而是互動性地用問答來教導,更深入地研究早上的經文。”
一半的會眾(48%),如北達科他州的“我們的救世主教會”,利用視頻資源進行主日學和其他教育課程。
研究人員發現,視頻課程還允許教會提供混合節目,或者讓參與者“按需求”觀看,而不是固定每週一起參加聚會。
該研究發現,“有關用Zoom作為宗教教育平臺,同樣數量的受訪者稱讚它或譴責它的無效性”,並指出兒童課程比成人課程更難轉移到線上。 “儘管如此,看到各種規模的會眾,在面對瘟疫的現實以及教育其年輕和老年成員的需求時,所嘗試的廣泛努力和創造力,真是令人感動。”
雖然瘟疫代表了最新的一次循環,但也許主日學一直都有它的挑戰。 1959年CT的封面故事問道:“我們應該關閉主日學嗎?”
它這樣說:“雖然主日學似乎一瘸一拐地走著,但它經常創造奇跡。 只有全智的上帝才能利用未經訓練的志願者、微薄的設施和有限的材料來改變這麼多人的人生軌跡。”
翻译: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