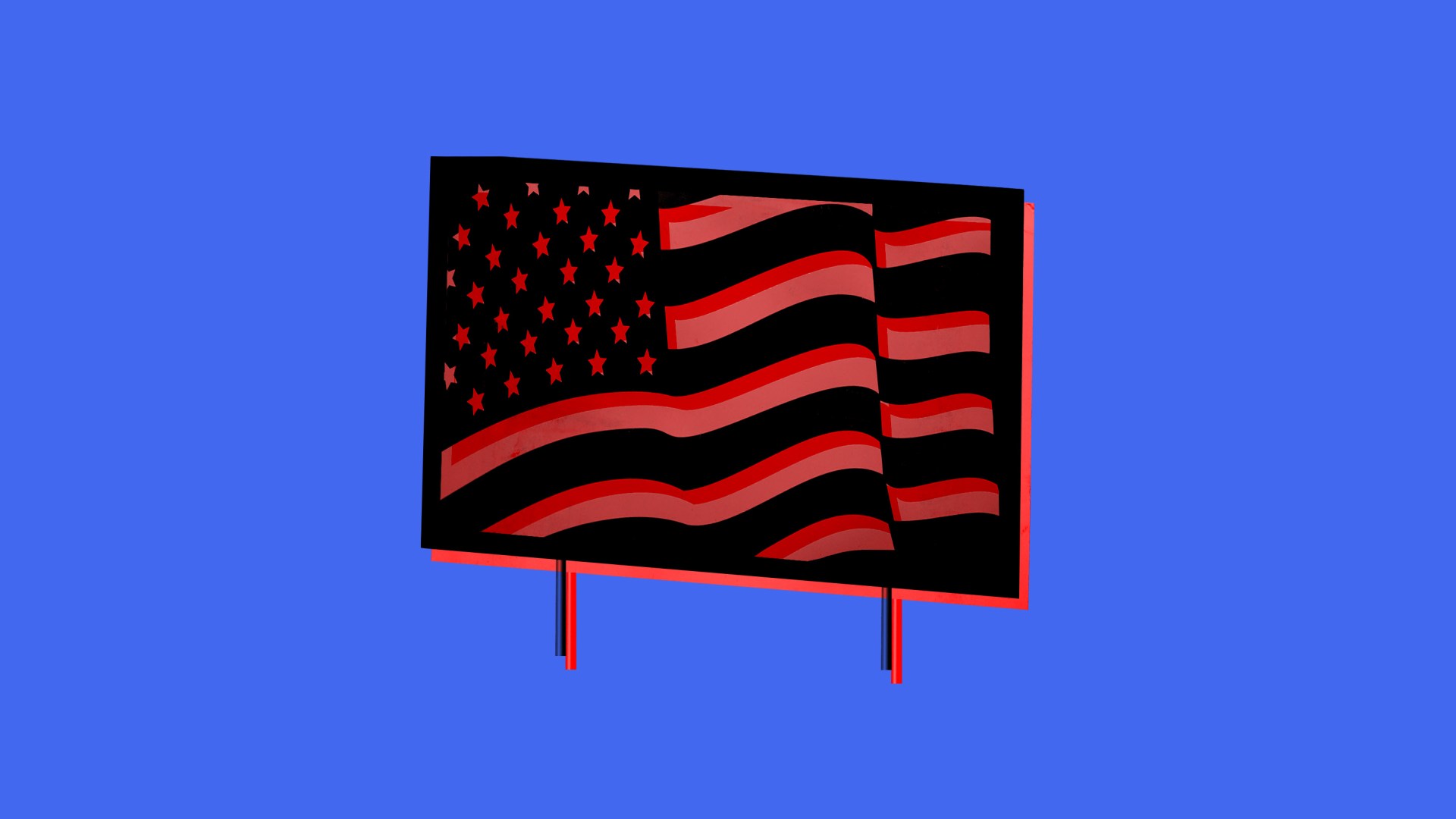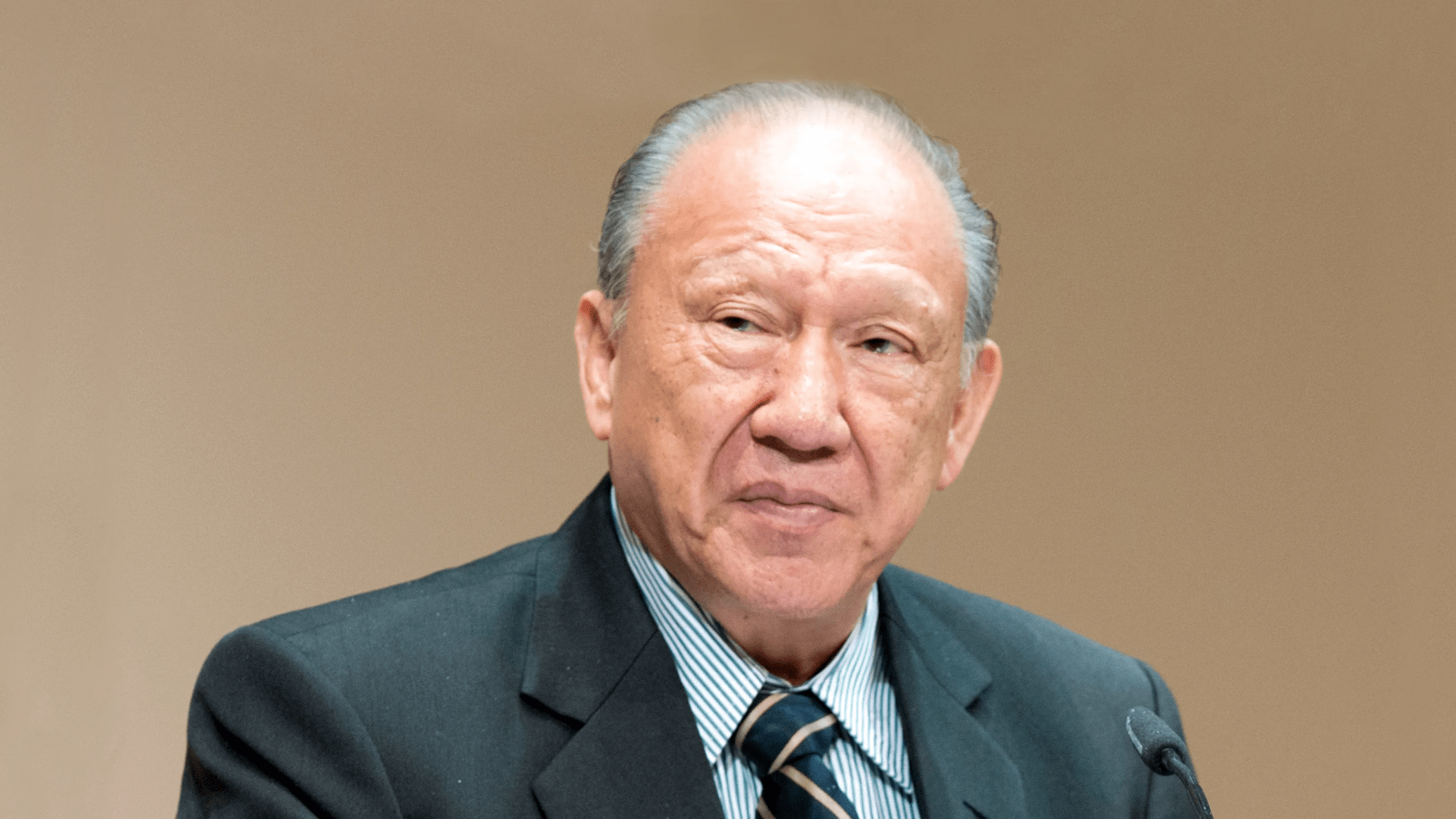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我們這些關心美國的人在選舉日臨近之際,往往會坐立不安。我們面臨著社會與日俱增的分裂,甚至是可能出現的暴力事件。
我的一位公共政策專家朋友最近提到,經常接收不同的選舉結果預測和相互矛盾的民調結果,讓她感到焦慮不安。「也許我該找些人們所說的『希望鴉片』來安慰自己,」她說。我能感同身受。
她所謂的「希望鴉片(hopium)」指的是那些能提供安慰、讓人相信一切都會好轉的好消息。這個比喻很貼切——尤其是在被鴉片類藥物困擾的美國——因為這裡確實有種讓人欲罷不能的「希望」正在麻痺我們,讓我們不去思考可能更慘淡的未來。
選舉日,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我們對更深層次的恐懼及擔憂的替代品——疫情、世界大戰、生態災難、人工智慧災難——誰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
關於選舉或其他事件,我往往傾向想像最糟糕的情況——比如選舉結果持平,269對269票,將已經憤怒且疲憊的公眾推向崩潰邊緣。但這種傾向也是一種反向的希望鴉片,試圖透過想像最壞的結局來阻止壞事發生,這樣一來,任何一種比這更好的結局都能帶來驚喜。
很多基督徒詢問我關於選舉的餘波(無論結果是什麼)時,會說:「能不能講一些有希望的部分?」通常,這些基督徒想聽到的其實是一種希望鴉片——希望在經歷過去十年所有的分裂和教會醜聞後,某種能修復一切的事會發生。無論是他們的教會、家庭或國家,他們都想回到2010或2015年的狀態。
某種意義上,在選舉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所能說的最有希望的話,或許就是鼓勵你放棄希望。
許多人熟悉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所說的「廉價的恩典」這一概念。我們首先要理解的是,廉價的恩典並非「過多的恩典」。恩典是無止盡的、無法量化的。廉價的恩典本身就不是種恩典。
不呼召人們懺悔或改變的恩典,最終無法實現安慰的目的。我們的良知知道——無論我們將這種意識埋得多深——我們最需要的,不僅僅是表面上見到的事。我們需要的是那種真正了解我們所有罪孽後,依然對我們說「你被赦免了」的恩典。
「廉價的希望」也是一樣的道理。它其實並非希望,而是一種「希望鴉片」。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警告人們,在一個每個人都是「基督徒」的文化中引入基督教,最初會讓人覺得有人正在「奪去基督教」。同樣地,向人們介紹「比絕望再陽光一點點」的那種盼望,一開始時也會讓人覺得失去了盼望/希望。
「盼望」當然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林前13:13)。然而,就像恩典一樣,聖經透過與其相反的事物來定義盼望。使徒保羅寫道:「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8:24–25)。當保羅呼召我們「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時,指出盼望是透過一種鮮少人會認為「充滿盼望」的方式產生的:在痛苦之中產生了忍耐,進而塑造品格,並最終帶來盼望(羅5:2–4)。
某些基督徒喜歡用印有耶利米書29:11的咖啡杯:「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這很好。還有些基督徒會引用更前幾節的經文:「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29:7)——這也很好。
然而,這兩節經文(一個為我們的信心帶來希望,另一個為我們的服事帶來希望)——都無法單獨脫離經文上一章的語境來理解。在28章,我們看到兩位先知展開一場對決。哈拿尼雅傳遞了「盼望的消息」:兩年內,上帝會打破巴比倫侵略者的統治,恢復所有被擄走的聖殿器皿。而耶利米似乎是那個「沒有希望」的人,他說:
阿們!願耶和華如此行,願耶和華成就你所預言的話,將耶和華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擄去的人從巴比倫帶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眾民耳中所要說的話,你應當聽。從古以來,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國和大邦說預言,論到爭戰、災禍、瘟疫的事。先知預言的平安,到話語成就的時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華所差來的。(耶28:6–9)
哈拿尼雅提供了希望鴉片。而耶利米提供的是唯一來自上帝的盼望——那種行經死蔭幽谷、十字架之路的漫長盼望。哈拿尼雅的希望是:「堅持住,一切就快結束了,你們會恢復正常生活。」耶利米提供的是另一種未來、另一種盼望: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29:13–14)。
這一種盼望才是能讓我們深吸一口氣,信任上帝,甚至喜樂的盼望——因為這種盼望向我們訴說真理。無論是從伊甸園到現在的任何時代,我們的處境實際上都比表面看起來更糟糕。然而,我們有耶穌。耶穌正是基督徒對未來的看法、基督徒的盼望的核心。我們的「未來」有個名字:拿撒勒人耶穌。「盼望」並非一種論點,而是一個人。祂就是盼望。
真正的盼望往往讓我們指向眼前,說:「我不確切知道我要去向何方,但上帝知道,而我與祂同在。」若由我們來定義,我們渴望的信心不過是眼目可見之事,我們渴望的愛也僅僅是肯定與認同,而我們想要的盼望則是我們所認為的最好的事能成真。
然而,無論我們如何自我安慰,希望鴉片都只不過是另一種絕望。讓我們放下它吧,我們並不需要它。
我們可以望向過去——如雲彩般的見證人和殉道者向我們訴說的真理。我們也可以望向很遠很遠的前方——眼淚將被拭去的那天(啟21:4)。我們只是看不見眼前的道路。但我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就像在遙遠的過去和未來那樣,祂永恆的膀臂始終會托住我們。
耶穌告訴我們,那些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先喪失生命;那些想要找到盼望的,也必先放下盼望。這在選舉日、審判日,以及在這之間的所有日子裡,都是真理。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總編輯,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