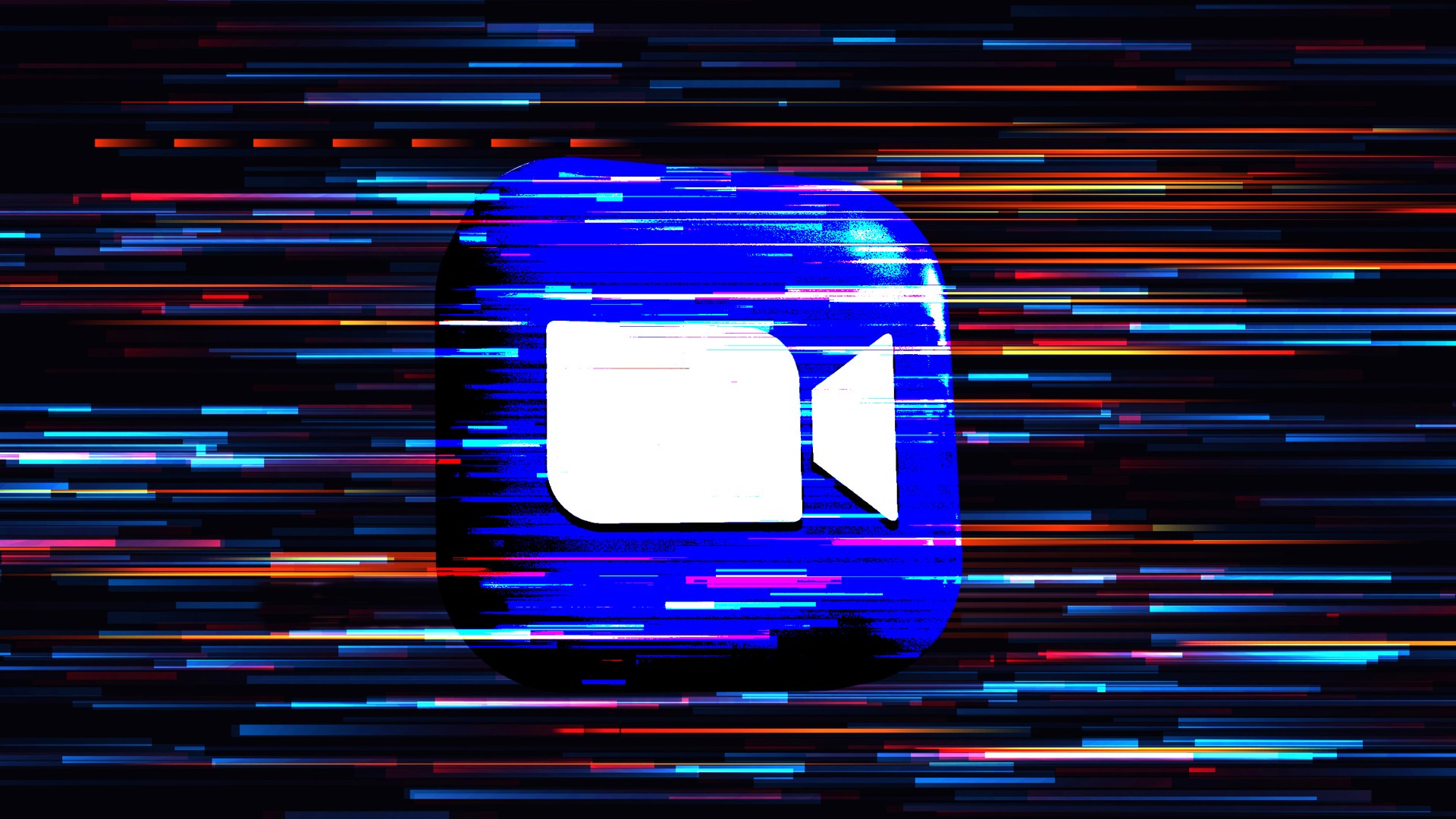八月一個炎熱的夜晚,中國北方一個大城市的家庭教會小組組長永韶正準備開始每週一次的Zoom查經班,卻收到多條小組成員發來的訊息,告訴他他們突然無法使用Zoom了。(出於安全考量,本文所有人名皆為化名。)
身爲IT業者的永韶進入了故障排除模式。他建議組員們更新Zoom應用程式,並改用手機流量而不是Wi-Fi上網。以前當Zoom出現故障時,這些方法都能解決問題,但這次卻沒有奏效。他們只得改用微信群來通話,但由於中國政府對微信的監控和審查,永韶的教會通常會避免使用微信。
慶幸的是,儘管他們在微信群的通話裡提到了「基督」和「永生」等敏感的宗教詞彙,他們的微信聚會沒有遇到任何干擾或突然被終止。但因爲微信將通話參與人數限制在15人以內,有些組員無法加入,而且小組帶領敬拜的人也無法分享他們計劃要唱的敬拜歌曲的音檔。
從那天晚上開始,永韶和他的小組的組員就不斷遇到Zoom的問題,無奈之下,他們只能繼續使用微信。
根據《今日基督教》對九位中國教會領袖和同工的採訪,我們得知在過去的三個月裡,中國其他基督教事工在使用Zoom時也遇到類似的問題。雖然Zoom尚未正式宣布被踢出中國(Zoom的網站顯示其在中國仍持續運營),但Reddit和Zoom網站上的用戶都有抱怨遇到類似的故障。(《今日基督教》聯係了Zoom公司,但他們尚未對我們的評論請求做出回應。)
由於包括Meta(Facebook母公司)、X(前Twitter)以及Google在内一些科技公司在中國被禁用,,Zoom成為家庭教會在疫情期間及之後轉為網絡聚會的「生命線」。Zoom不僅操作容易,且對於希望通訊不受政府監控的家庭教會來說也相對安全(儘管該公司為了持續在中國運作,同意抑制敏感言論)。眾所周知,微信會切斷通話或刪除帶有敏感詞彙的訊息,但基督徒在使用Zoom時並沒有遇到這些問題。
目前Zoom障礙發生的全部範圍尚不清楚。有些人說,他們發現去年在中國境外建立的Zoom帳戶現在在中國已無法使用。有些人發現免費注冊的帳戶無法參加Zoom會議。也有人懷疑,技術層面遇到的困難是否可能是Zoom「遵守中國地區法規」的結果。
最近幾年中國基督徒處於不斷變化的環境下,家庭教會已學會靈活地使用新的敬拜模式。如果Zoom不再能用,他們會尋找其他方法來聚集,敬拜上帝——無論是使用其他視訊會議平台、下載虛擬私人網路(VPN,也就是所謂的「翻牆」工具)來規避中國的網路「防火長城」,或者是參加實體聚會。
Zoom在中國面對的挑戰
Zoom是一家美國公司,在中國擁有相當規模的開發團隊,中國基督徒對這家公司並非沒有擔憂。根據CyberScoop披露的法庭文件,中國當局在2019年封鎖了Zoom,聲稱該公司在壓制反政府言論方面做得不夠。之後,Zoom的首席執行官袁征(Eric Yuan)訪問了中國,並同意對中國共產黨認為敏感的話題進行監控。Zoom稍後便恢復了在中國營運。
這種監控的證據出現在2020年,當時該公司在 “六四” (中國最敏感的歷史事件之一)週年紀念日關閉了Zoom上的紀念活動,並在中國當局的要求下暫停海外異議人士的Zoom帳戶。
Zoom在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中表述了在中國營運的風險:「中國政府有時會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關閉我們在中國的服務,並要求我們在恢復服務前採取某些措施,例如指派一名內部聯絡人來處理中國執法上的要求,以及將存放在美國的中國用戶資料轉移到中國的資料中心。」
自2020年8月起,中國用戶便無法直接向Zoom購買服務。他們需要透過當地的第三方合作夥伴購買服務。一些擔心政府監控的中國基督徒被迫在美國購買了Zoom帳號許可證。
儘管如此,Zoom仍成為中國家庭聚會教會開展事工的重要工具。中國北方一個小城市的傳道人劉傑說,除了查經,他的教會還用Zoom直播主日崇拜、線上靈修和生活實踐類的門徒訓練,主題包括婚姻、養育兒女和心理健康。COVID-19封鎖開始後,他的教會分成了幾個小組,並開始使用Zoom進行所有聚會。線上聚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擴大了教會的影響範圍,讓一些住在城市周圍的農村、鄉鎮基督徒和一些老人或病人也能夠參與教會。
然而從上個月開始,劉傑的教會同樣無法登入Zoom了。劉傑也懂一些IT技術,他最終不得不從教會微薄的預算中花了一大筆錢在網上購買了一種軟體,才得以繼續使用Zoom。(劉不願意透露具體的技術細節,因為他擔心那樣會讓政府知道,導致影响后续使用或无法再购买相關工具。)
李朔盟是服事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海外事工領袖,他在過去幾個月中聽到很多關於Zoom的抱怨。他說:「我認為這是中國『防火長城』的一部分,而且中國正在迫使Zoom遵守一些當地法律。毫無疑問,對中國境内的教會和機構而言,Zoom越來越難使用了。」
在中國東部一間神學院工作的Sarah Cheng也有同樣的經驗。她說,自8月以來,她的團隊為神學院和與之相關的家庭教會購買的20個Zoom帳號許可證已有18個失效。(到了10月份,剩下的兩個也無法再使用)。
Sarah說,5月時,他們花了2000美元在美國購買了這批有一年效期的Zoom帳號許可證。當她致電Zoom公司時,該公司稱他們的活動違反了中國當地法律——美國版的Zoom帳號不被允許在中國使用。Zoom公司也拒絕為剩下的9個月的許可證有效期退款。
最近,Sarah注意到,Zoom免費版的中國用戶在嘗試加入外國帳戶設置的Zoom會議時收到系統錯誤的訊息。她認為,中國政府正試圖迫使本地用戶使用第三方合作夥伴,而這將帶來更大的風險。Sarah說:「這樣做(使用第三方)的代價是,你所錄製的一切,包括誰加入了會議,這些資料都會儲存在中國。對我們而言,這是非常危險的。」
目前似乎只有Zoom的商業帳戶(要求用戶購買至少10張許可證)可以在中國正常使用。如今,Sarah服事的神學院主要使用Webex來開網絡會議,但這個會議平臺在操作上不如Zoom方便,尤其是在錄製和設定會議方面。
只有實體聚會的教會
並非所有的家庭教會都使用Zoom或其他線上會議應用程式。有些家庭教會甚至刻意避免使用線上會議。上海的始明牧師說,他的教會在COVID-19封鎖期間使用Zoom來聚會,但自2月恢復實體聚會後就不再使用Zoom了。他們的理由更實際,而不是出於安全考量:「只要Zoom還開著,就會有人找理由不來」參加面對面的聚會。
負責組長聚會的永韶也認為教會需要減少對科技的依賴。他認爲,家庭教會的牧師和教會領袖應該「盡可能多地進行線下牧養——即使能聚在一起的人少。傳道人應該多付出時間精力,多跑多探訪,盡可能照顧到每個信徒。」
趙亞倫是中國中部一個大城市的家庭教會牧師,他也贊同多在線下牧養,並說他的教會沒有用Zoom直播主日禮拜。不過,他的會眾仍會使用Zoom來開線上團契禱告會。當他們這樣做時,「的確有越來越多的人反應加入會議有困難,有時是無法加入會議,有時是沒有聲音或圖像等等各種情況」,但因為他們並不常使用 Zoom,這對他們的教會生活影響不大。
趙亞倫說:「如果最終Zoom在中國完全不能用了,我們可能會轉用其他會議軟體,但不會考慮國產軟體(如騰訊會議、釘釘等)」。他提到的這些應用程式受到中國政府的嚴格監控。他的教會會用需要VPN才能使用的墻外應用程式。
關於VPN的爭論
對於是否鼓勵基督徒使用在中國已經屬於“非法”的VPN(政府曾逮捕並罰款使用VPN的人,雖然那不是普遍的情況),家庭教會領袖們有不同的立場。
趙亞倫所牧養的教會是鼓勵會衆使用VPN的。趙牧師說,這有助於教會「一方面沟通没有障碍,不需要避讳什么敏感词,另一方面幫助信徒能有更多信息来源,兼听则明,不至于被国内媒体洗脑。」
但劉傑的教會並不鼓勵其成員使用VPN,即使劉自己會用。他說,這是因為他的教會的「牧養群體中有很多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村鎮居⺠,新app學習成本巨大……而且現在翻牆很有可能被監控到,翻牆工具本身的安全性」也是一個問題。
賽啞是住在中國東部的一名教會同工,他對使用VPN也持類似的保留意見。但他認為,家庭教會和團契使用VPN獲取所需的基督教資源可能是無法避免的。
「很明顯近年來一些教會使用較多的資源平台屢屢被封禁,而國內近年來幾乎鮮有基督教類的書籍出版,因此教會尤其是小組團契在獲取資源方面越來越困難,」賽啞說。「我希望國內的基督徒,尤其是參與教會服事的同工,不要總是閉門造車,也要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保持前瞻視野,才能對未來環境會發生的變化有一些預判,也能在事工上更好地做出相應的調整和預備。」
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切斷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教會不僅需要關注自身的日常運作,也需要學習如何在「越來越逼仄的網路環境」中對會眾進行門徒訓練,把當下的狀況當作可以更好地牧養會眾的契機。
「未來的環境可能會變得更嚴峻,甚至可能有一天連翻牆工具都用不了,那時可能中國的網路就是一個封閉的區域網路,跟Internet(互聯網)是脫離的,」賽啞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覺得牆外的基督徒能提供的幫助似乎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國內的基督徒在逼迫的環境下可以經歷靈命的更新。」
翻譯: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