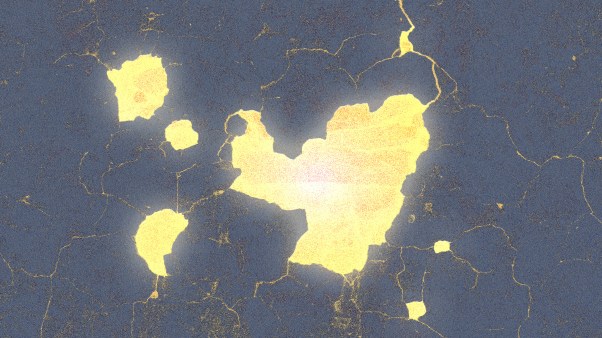當克勞利 (Rory Crowley) 終於弄明白的那一刻,忍不住淚流滿面。
他獨自坐在達拉斯一間昏暗的公寓裡,身邊只有一盞燈和一台打開的筆電,身子前傾,凝視著一張高畫質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片殘破的莎草紙。
紙上寫著希臘文,可能是耶穌受難約150年後,一位基督徒寫下的話語。克勞利與達拉斯神學院其他跟隨華萊士 (Daniel B. Wallace) 教授研究這片莎草紙的年輕同學,立刻認出了部分內容。那是《馬太福音》裡的登山寶訓;還有些段落與《路加福音》的「平原寶訓」相似 (路加福音6:17-49)。
但在紙的中間還有一部分,他們無法辨認出自何處。
「你戒斷,」上面寫著,「除非你……你永遠找不到,世界你……天父……飛鳥,如何……。」
他們反覆琢磨了數個小時、數週、然後數個月。直到有一天,克勞利突然意識到,這是來自《多馬福音》(一部非正典的耶穌語錄文獻) 裡的一小段話。眼前的文字與其中一段經文相符:「除非你戒斷這個世界」,否則你永遠無法找到上帝的國,也看不見天上的父。
無論是誰在莎草紙上寫下這段文字,他把來自不同地方的話語編織在一起,整理成耶穌關於「憂慮」的教導。而克勞利——因凌晨兩點睡不著,索性起來工作——在那一刻終於明白了。
「我哭了出來,」他告訴本刊。「我感覺自己正與一位基督徒做心靈上的對話。在我看來,這是一位忠心的基督徒,他知道有這樣一位極其奇妙的耶穌。」
克勞利和其他人於2012到2013年間共同研究的這份殘片學術報告,最終在2023年八月底正式發表,結束了學界十多年來的流言與揣測。有人曾說這是《馬太福音》極早期的抄本;也有人說它是從木乃伊的面具上剝下來的。兩種謠言都不是真的。根據參與研究的學者所言,真相更美好:這片殘卷揭示了公元2世紀末至3世紀初的人們是如何接觸並應用耶穌的教導。
「這片莎草紙讓我們得以一窺那個時代的信仰面貌,」伯特利大學聖經研究榮譽教授霍姆斯 (Michael Holmes) 說。他與華萊士教授,以及貝勒大學的費許 (Jeffrey Fish) 共同撰寫了這份報告,並致謝八位曾就讀於達拉斯的研究生。
「這段話是某個更長篇講道的一部分嗎?還是一篇私人默想?它太短了,人們只能推測,」霍姆斯說。「但在那個 (這片莎草紙撰寫的) 時期,聖經正典仍在逐漸成形。耶穌的語錄以口傳方式流傳,可能也有一些小型的書面彙編,然後才有了福音書。在第二世紀,這些東西是並存的,而且流動性非常大。」
這份報告的發表,在研究早期基督教文獻的專家之間引起騷動。這片如今被稱為 P.Oxy. 5575的莎草紙,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登山寶訓》的書面記錄;它也被認為是最早 (或至少是最早之一) 的《多馬福音》片段。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唯一已知的、來自那個時代的、將耶穌這些論述連貫並彼此互動的文獻。 在報告發表一個月後,北美基督教偽典文獻研究學會 (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Apocryphal Literature) 的成員在Zoom上聚集討論這份殘片。他們分析了它可能的文學體裁類型、成文年代,以及它與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獻的關係。

也有人對這片莎草紙的離奇歷史表示保留態度,質疑它為何會落到一群福音派研究所學生,以及三位皆與聖經博物館 (Museum of the Bible) 有關聯的教授手中。
而這段歷史的確不尋常。
這片殘頁最初是在一座有著希臘名字的埃及城市——奧克緒林庫斯 (Oxyrhynchus)的一個垃圾堆裡被挖掘出來。1897年的冬天,兩位牛津學者在當地開始挖掘,發現了因沙土與乾燥氣候而保存下來的、數量極其龐大的莎草紙文獻。
短短幾個月內,他們就挖出將近2000英磅的文獻。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們陸續將超過50萬片殘片運回牛津,存放在埃及探勘協會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簡稱EES) 的圖書館藏中。
截至今日,奧克緒林庫斯莎草紙大約只有1%已被出版。這些殘片包括收據、法庭紀錄、稅務文件與契約;也有古代的柏拉圖、歐幾里得、荷馬作品殘篇;還有一齣涉及薩堤爾的被遺忘的索福克勒斯戲劇;以及大量早期基督教文稿,包括禱文、聖詩、講章與聖經經文。
將近127年來,學者們一直在慢慢整理這批考古寶藏。然而,根據EES的說法,這龐大的珍寶對某些人來說實在太具誘惑力。身為館藏一部分負責人的著名莎草紙學家奧賓克 (Dirk Obbink) 涉嫌竊取超過一百片殘頁,將其中一些賣給正籌劃建立聖經博物館 (Museum of the Bible) 的人,並刻意隱瞞它們真正的來源。
2012年,這些殘片被送交給福音派學者,讓他們能在培訓研究生的同時進行原創研究。華萊士教授——同時也是「新約手稿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s) 的創辦人——收到一片大約寬4公分、長9公分的莎草紙,夾在兩片壓克力板之間保護。它被稱為「Matt Frag」(馬太殘片)。
無論是華萊士,還是他招募的八位達拉斯神學院學生,當時完全沒想到這是被盜的文獻。他們也沒想到它與奧克緒林庫斯的挖掘有關。不過,他們確實懷疑過,這段文字可能是從某個木乃伊面具裡取出的。
「奧賓克當時正在拆解木乃伊硬紙板 (mummy cartonnage),有點像紙糊工藝那樣,」當年是華萊士的學生、現為鳳凰神學院新約教授的格里 (Peter Gurry) 解釋道。「基本上,他會用水和溫和的液體清潔劑,讓紙漿慢慢分解成一塊一塊的莎草紙。結果,哇!有些莎草紙上竟然寫著文字。」
然而,學生們並不太在意它究竟來自哪裡。他們專注於學習解讀莎草紙所需的技巧。他們大約每週去華萊士家一次,進行高強度的獨立研究。
「光是辨識文字就非常困難了,」華萊士告訴本刊。「你不知道文字的左邊界,也沒有右邊界。你面對的是一個處在某段文字中間的殘片,你只能從一個詞的一部分開始。」
當他們一同解讀希臘文時,辨認出一些與《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非常相近的句子——包括不要為任何事憂慮、想想天上的飛鳥等等。他們也發現另有一部分文字,似乎和新約任何內容都不吻合。這片莎草紙並非全是《馬太福音》的早期抄本,但他們當時還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東西的部分內容。
研究小組的下一個任務,是確定這份文獻的年代。華萊士要求學生去查找其他古代手稿,對比不同的書寫風格,直到能把這片殘卷定位在某個特定時期的希臘書寫風格中。
「你必須在審視不只幾十份,而是幾百份莎草紙後,才會有把握,」當時也是華萊士的學生、現任改革宗神學院新約教授的科爾 (Zach Cole) 說。「你得觀察一個 α (alpha) 的形狀是怎麼寫的,然後漸漸培養出比較的直覺——但這理論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任務。」
在不斷比對、比對、再比對之後,八位學生各自寫下論述,提出他們判斷的日期。他們皆得出一致的結論:這份文獻的書寫方式最接近被定年在2世紀末至3世紀初期的手稿。
接著在2013年6月,克勞利終於將那些陌生的文字與《多馬福音》連結起來。那是在他花了數百小時,把這片殘片與其他古代莎草紙並列,逐一對照的某個時刻——忽然間,他發現它竟然對應上1898年出版的第一份奧克緒林庫斯文獻P.Oxy. 1中的一段經文。
「主啊,」克勞利說,「是祢讓我們找到了這個。」
直到幾年後,他和其他學生才得知,他們研究的這片莎草紙其實理應屬於EES,從來就不該流落到達拉斯。它從未是木乃伊面具的一部分,而是被放在牛津的一個箱子裡超過100年,直到被偷走。
聖經博物館後來歸還了被竊的文物,而奧克緒林庫斯館藏的負責人也大方地決定允許這群福音派學者繼續他們的研究。
對這些學者而言,如今回頭看,這幾乎像是一個神蹟,或至少是上帝奇妙運行的一種方式。
如今,隨著這片殘卷已被正式發表,他們意識到自己當時解開的謎題,只不過是更大拼圖中的一小塊。他們的研究會引起辯論,並激發更多研究——這正是學術運作的方式。
但他們也意識到,在那一刻,他們的研究跨越了千年,與另一位被耶穌深深感動的人產生了連結。
「這份手稿提醒我們,耶穌的教導對當時的人而言何等奇妙。而耶穌的教導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依然如此奇妙。人們自古以來總會為萬事憂慮,而耶穌教會我們以一種最深刻的方式看待這樣的憂慮,」格里說。
Daniel Silliman為本刊新聞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