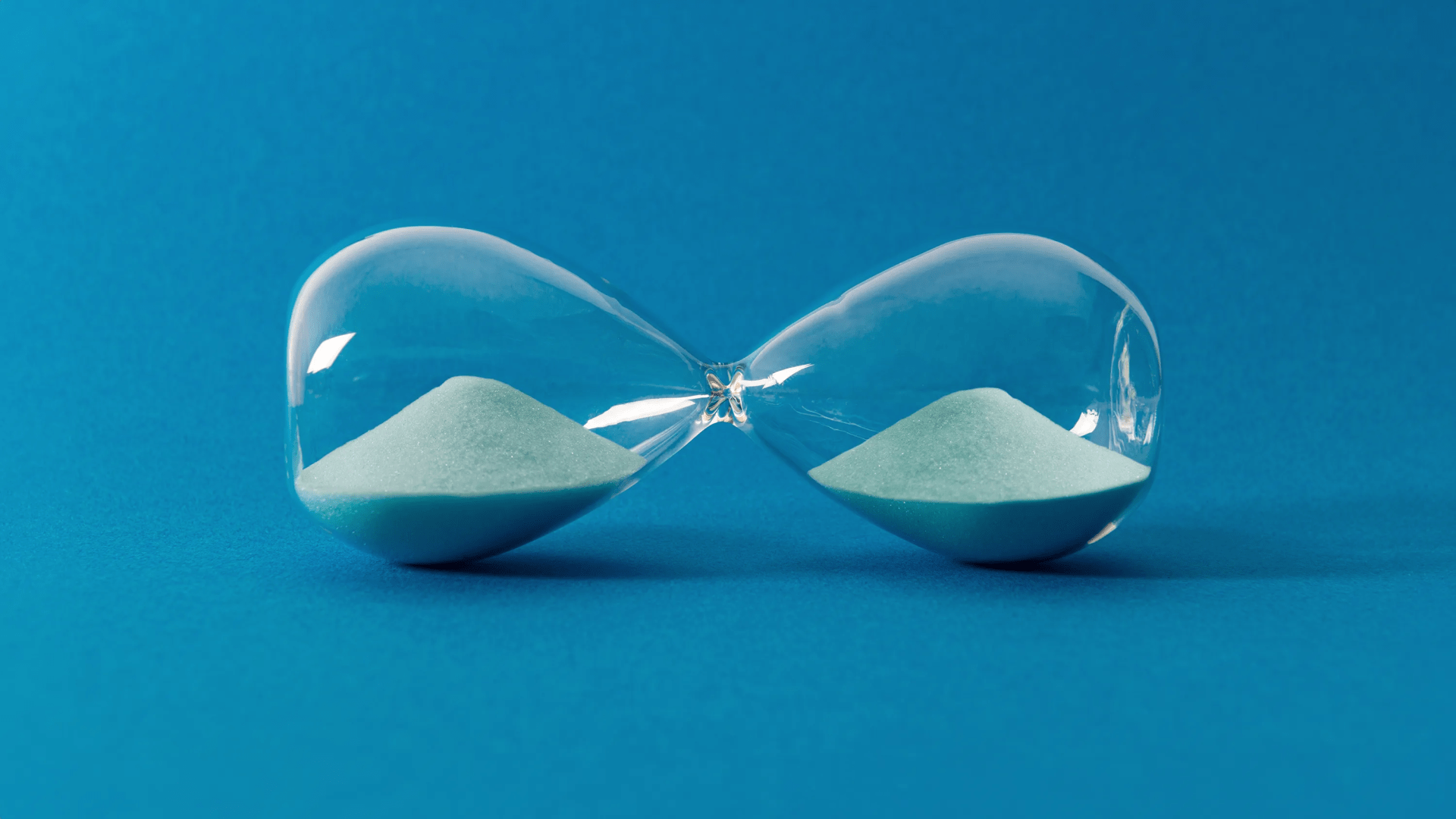如果摩西拿出他的手機拍攝荊棘燃燒的影片,而不是全神貫注看著它,他會錯過上帝對他說的話嗎?如果馬利亞在日常工作的休息時間滑手機,她會不會因為分心而沒有注意到天使的到來?
摩西和馬利亞見證了永恆打破世俗的那刻,見證奇蹟打斷平凡日子的時刻。他們完全活在那一刻時間裡。
我們能說自己也是這樣嗎?我們擔憂時間的稀少,渴望逃避會「浪費」時間的事物:電視和新聞、手機訊息和電子郵件。諷刺的是,當我們感到無聊或想要分心時,我們卻會使用這些科技來加速時間。手機內的影片和照片將我們從全然活在當下時刻的經歷裡拉出來
試圖囤積時間或浪費時間只會讓日子過得越來越快。就像底部有洞的沙漏一樣,時間不斷地流失,當我們注意到沙漏幾乎流光時,又十分地驚訝。但我們該如何修補沙漏,一粒一粒地恢復時間?
我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六年間,與時間的關係一直處在一種緊張狀態。我既希望它快一點,也希望它慢一點。當我步行、騎腳踏車或搭地鐵時,我會瘋狂地計算時間。如果我發現自己卡在某處——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或在公車上緩慢移動——我會馬上掏出手機,不斷地滑動畫面、一頁又一頁,試圖逃避時間,希望時間過快一點。我會直接沒看到燃燒的荊棘叢,從旁走過,或在被天使打斷後低頭回去看我的手機。
我與時間的衝突感讓我決定做些實驗。我熱切地嘗試操練安息日、靜默獨處、沒有手機的長途散步、以《公禱書》禱告,或禁用社交媒體。但這些嘗試永遠都不夠。這些練習常常讓我感覺只是要從塞得太滿的日程表中擠出更多時間的另一種要求。而且這些操練多數時候都是單獨進行的。無論是工作壓力、看Netflix、瀏覽社群媒體或閱讀新聞,生活就像我一個小女子在與整個文化搏鬥,一個要求我投注更多時間、更多自我的文化。我拼了命不想落後,跟上步伐,同時還要留出時間給朋友、家人、教會和休息——所有這些也開始讓我覺得是種義務。
我讀過足夠多的書,知道紊亂的時間關係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更是焦慮。但我沒有想過信仰群體可以如何在這件事上幫助我。原來,靠我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與時間的關係是不持久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需要教會的幫助。
我在華盛頓特區時參與的聖公會教會開始了一項新的計畫,叫做基督徒靈命培育小組。我第一次讀小組的承諾書時,立刻覺得「不可能辦到的吧!」。對於像華盛頓這樣的城市來說,這些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無法壓制內心催促自己參加這個小組的急迫感。
這個為期六週的小組計畫包括一長串靈修操練,分別為「脫離」和「依附」而設計,兩者相互作用。「脫離」的練習包括不使用社交媒體、不獨自使用影視串流平台(每週允許與其他人一起觀看三小時)、不聆聽聖經以外和以基督為中心的音樂以外的音訊,以及不閱讀聖經之外或符合腓立比書4:8教導之外的書籍。
「依附」的操練則包括每週參加一次靈命小組、每天以降服的姿勢禱告30分鐘、每天讀聖經,每週一次志工服事、每週禁食一次、每週招待「屬靈的朋友」一次、每週操練安息日一次、以及一次10小時的退修,並在完成六週計劃後的四個月內,每月參加一次靈命小組聚餐。
我立刻被這些操練與「時間」有極大的關聯性所打動。「脫離」的操練鼓勵我們減少花在心不在焉的時間上(或甚至不花任何時間在這上面)。「依附」的操練則鼓勵我們花更多時間與其他人、與上帝的話語、與聖父、聖子和聖靈交通。
對我們許多人而言,第一週會讓我們感到焦慮的問題很簡單:當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時,我要做什麼事?盯著牆看嗎?這個計畫要求我們事先做好準備,列出可替代的活動清單,以及在我們重新分配的時間內要為哪些人或事物禱告。
Andrew Root在《世俗時代的會眾》(The Congregation in a Secular Age)一書中指出,我們現代人對時間的感受有如一種饑荒——不只渴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而是渴求在每個流逝的時刻都有更豐滿、更有意義的體驗。矽谷要求我們創新、加速、最大化自己的能力,讓我們可以無止盡地處理多項任務,做得更多、更快。諷刺的是,聲稱可以節省時間的裝置卻讓我們覺得時間永遠不夠用。我們無法放慢腳步,聆聽自己的思緒,更遑論聆聽聖靈的低語。
這種狂亂使教會特別難引導會眾進入神聖的時間。取而代之的是「為了速度,時間被清空了」;教會存在的目的變成「改變人、強迫性的成長」,而不是「在聖靈裡的生命轉變」。我們需要教會逆著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為我們學習操練居住在神聖、神秘和永恆裡的地方。
加入這個計畫後,時間和我的關係似乎變了。搭地鐵的時間變長了,晚上在家的時間變寬裕了,每天早上30分鐘的禱告變成一種安慰,而不是一項任務。對我來說,一些「脫離」的操練還算容易。但像是背誦經文、志工服務和禁食等依附的操練,卻特別難塞入我滿滿的日程表中。有幾個星期,我完全無法容納這些操練,而禁食不吃飯的飢餓感讓我更緊繃。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聆聽有聲聖經的操練。我做晚飯時聽,洗碗時聽。漸漸地,我心中的聲音改變了。我經歷到生命的寧靜與和平,而不是混亂與噪音。
「減少消費、接收的來源(娛樂選項)」——只接收「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內容——長期下來累積的效果,是一種被解放的感覺。在搭乘地鐵或晚上在家的時光中,我不再向腦海擠進更多內容,而是有片刻的時間靜下來與我的思緒共處,並在突然有感時禱告,而如果我在玩手機或看Netflix,我可能會錯過這個「突然有感」的時刻。
但真正讓這種操練與之前不一樣的,是我的屬靈群體。在群體聚會的日子裡,當我們沉浸在彼此分享的故事裡時,時間完全失去了它的結構。我們彼此同理將這些操練付諸實踐的困難處,並相互鼓勵、並肩努力以新的方式駐足於時間之中。
與其他人分享我們的經驗——自在地掉淚、歡笑和分享智慧的言語——創造了Root所說的「共鳴」的時刻,正是能解決我們對時間的飢荒感的方法。根據Root的說法,共鳴是種時間的「集結」,充滿意義和目的。為了創造共鳴,我們必須跳脫自我,放下手機。在與上帝或與他人相遇的時刻,在這種延伸的時刻裡,我們讓自己處於敞開的狀態、脆弱地接受上帝所命定的恩典時刻。共鳴能將時間沙漏填滿,補足我們的靈魂,而不是耗盡我們。
當我與其中一位共同帶領靈命小組的牧師談話時,他說這個小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的簡單性——回歸到基督教信仰最基礎的事物。脫離及依附的節奏,在這個我們被告知要「善用時間」的時代,感覺特別地突兀——因為這種節奏著重於委身而非結果。禁食和禱告並非我們可以立即看到「生產力」的操練。
但事實上,一起聚會、讀經、靜坐這些基督教歷史悠久的簡單操練,在每個時代都感覺如此新鮮。在被評為美國最孤獨城市的華盛頓特區,我的牧師說,我們也應該視我們的群體/共同體(community)為一種靈修。我們無法以獨居個體的方式來重拾神聖的時間,尤其在科技如此強大且讓人上癮的情況下,單獨完成這項任務實在太困難了。
這個逆著文化而行的靈修小組改變了我與時間的關係:時間成為豐富的,而不是稀少的;時間成為ㄧ種機會,而不是負擔;時間是與他人共處的,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正如詩篇90篇提醒我們的,我們必須學習數算自己的日子,並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花費時間,因為「一千年在(上帝)眼中看來,如同一日」(詩篇90:4)。
在靈修小組結束後的幾個月裡,我沒有獨自努力逆著我們的文化而行,而是和別人一起主持週末的靜默退修會,並參與每週的聚餐。我委身於每天早晨的禱告和讀經,但這次是和朋友一起。在讚美和禱告中一起度過的時間似乎倍增了,也似乎慢了下來。時間變得好多、好充裕,但沒有多到壓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並且我的時間與他人的時間共鳴。燃燒的荊棘閃爍著,我的主在說話。
一個以能將人們帶入超然、神聖的時間而聞名的教會,是貪得無厭的消費文化和加速文化真正的喘息之處,是個能吸引人駐足的地方——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Aryana Petrosky是愛丁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研究生,研究大公修道、靈修和公共場合中的信仰。她協助創辦The After Party:Toward Better Christian Politics(邁向更好的基督教政治),並曾在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Initiative on Faith & Public Life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