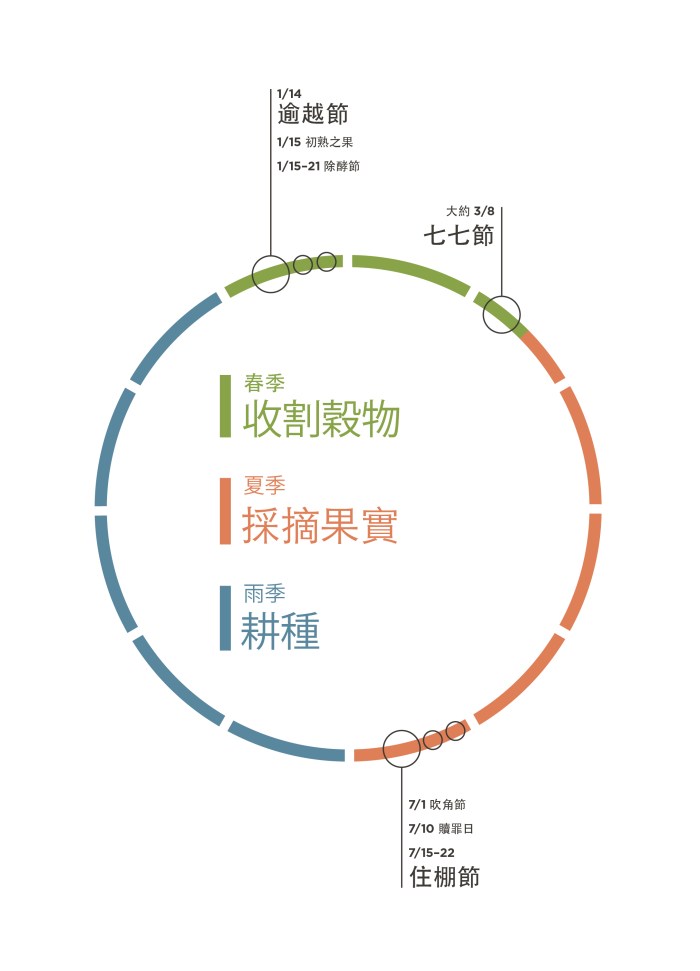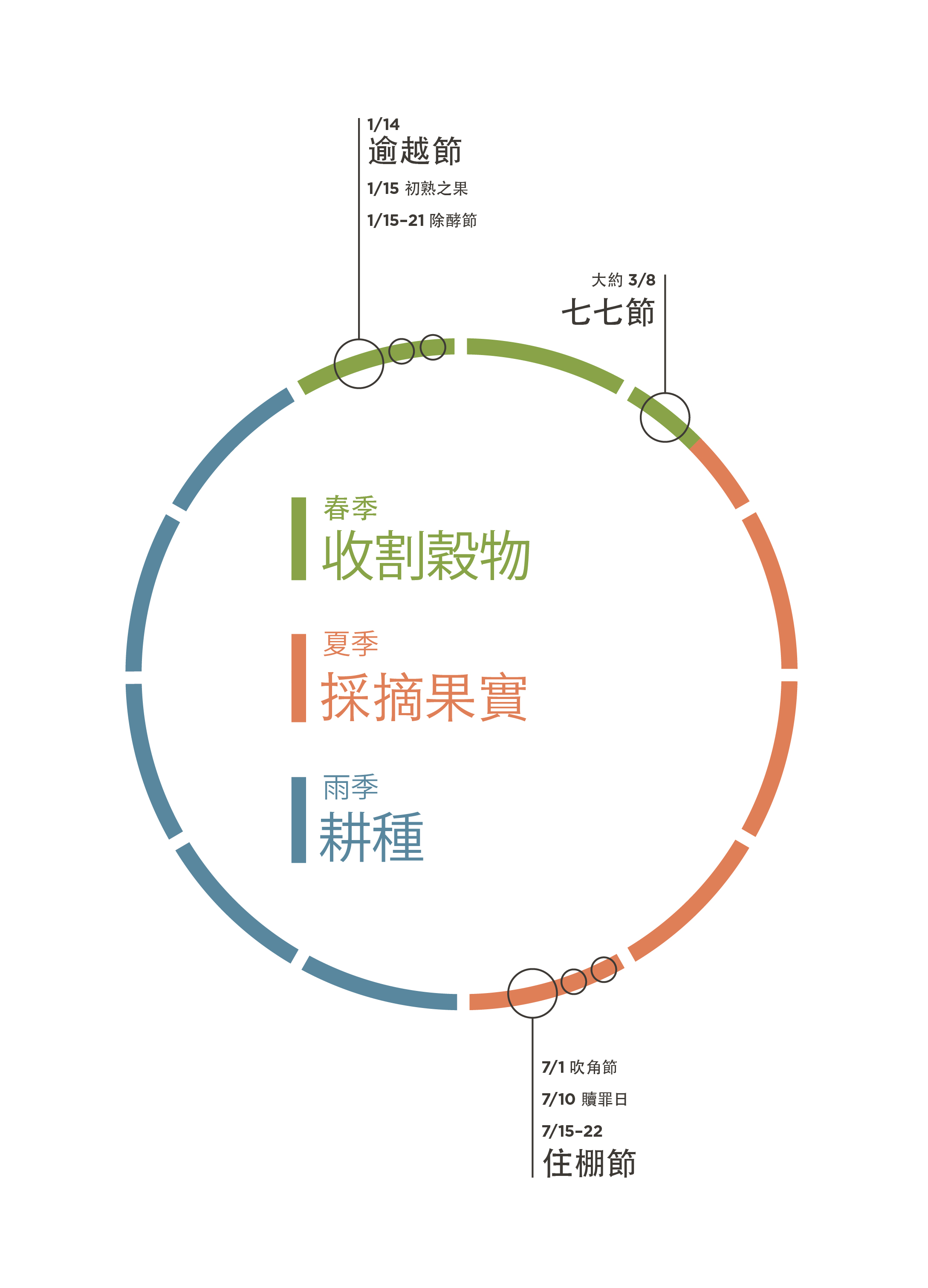1991年我在鮑伊州立大學(Bowie State University)上大學時,我和80年代和90年代的許多非裔美國人一樣,踏入了一個新的身份意識形態的溫床。 此時,許多進入大學的黑人(特別是傳統黑人大學)都會佩戴某種類型的文化飾品,指出他們與非洲的淵源,這包含用來自非洲的皮革製成的徽章到使用某種非洲藝術圖案描繪非洲大陸的短袖圓領運動衫。
對於黑人來說,那是一個與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掙扎摸索的重要時期。 你會看到黑人兄弟們在學生會里出售書籍和諸如藍尼羅河、檀香、乳香和沒藥等精華油。 這些攤位上擺滿了資源,承諾給我們真理以填補我們黑人思想的空白,這些真理原是白人不讓我們知道,以防止我們認識自己是誰。
作為一個黑人基督徒,我有時會覺得自己好像在追隨壓迫者的宗教。 這就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意識到你原本所有認為是正確的事物其實都是錯誤的。 在美國,同時身為黑人以及基督徒兩種身份有一種固有且持續的張力,這種緊張感深深刻在許多非裔美國人的心理中。
請看下面這些通常被稱為“黑人覺醒”群體支持者的引言。 “伊斯蘭教民族”(Nation of Islam)的長期領導人以利亞·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說:“所謂的黑人必須在時機已經太晚之前覺醒。 他們以為,無論發生什麼事,白人的基督教都會拯救他們,但他們犯了嚴重的錯誤。 他們必須知道,白人的宗教不是來自上帝,也不是來自耶穌或任何其他的先知。 它是由白人這個種族鎖控制的,而不是由全能的真主(上帝)控制的。”
或者以賈巴里·奧薩澤(Jabari Osaze)為例,他是歷史學家,自稱是古基米提斯(Kemetic,即埃及)王國的祭司。 正如他在《七個白色小謊言:摧毀黑人自我形象的陰謀》這本書所說:
“我記得教會主日學時,老師會從箱子里拿出摩西和諾亞的紙板剪影……他們都是穿著長袍的白人老人。 他們看起來就像我隔壁的鄰居,但是穿著長袍。 想像一下,作為一個孩子,我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基督教的所有英雄都是白人。 我確實認為那是一種錯誤。”
像這樣的評論給黑人造成了一種難以克服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作為基督教護教家,我們不應該回避這種挑戰。 這只是意味著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為什麼今天需要一種我稱之為 城市護教學(Urban Apologetics) 的眾多原因之一。
誠然,西方的、白人歐洲基督教經常努力破壞黑人身份。 然而,這些“黑人覺醒”(Black conscious)的群體卻拋棄了整個基督教信仰,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扔了出去(不分良莠,好壞一起丟——譯註)。 他們沒有做足夠的功課來仔細研究真相。 城市護教學破解了這些團體宣傳的虛假起源故事。
黑人基督徒總是被黑人覺醒團體的代言人審問。 我們總是因為接受了基督教而被他們批評,因為過去自稱為基督徒的白人在綁架和奴役黑人方面是主謀。 許多黑人被教導,非洲人與基督教的第一次接觸是通過奴隸貿易。 許多人認為基督教在奴隸制度中的歷史作用是摧毀黑人思想的一個關鍵因素。 他們認為基督教是歐洲人創造的,被白人壓迫者用來持續奴役黑人的工具。
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 在西方有奴隸制度的時代,有一種錯誤的基督教形式,為綁架人類來辯護。 這種形式的基督教的支持者是否創造了一本被稱為“奴隸的聖經”(the slave’s Bible)的刪節版《聖經》,以防止奴隸對福音有一個清晰和全面的瞭解? 是的。 某些所謂的基督徒是否把黑人說成是不如人的,從而玷污了每個人內心深處 神的形象(imago Dei)? 是的。
在過去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黑人群體一直在努力為我們的群體面臨的挑戰提供強有力的神學答案。 直到最近,我們才看到有人協同努力,解決黑人覺醒運動支持者提出的反對意見和問題。 而在目前的互聯網時代,遊戲規則已經改變。 反對意見傳播得更快。 關於基督教的謬論有更長的壽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迫切需要一套獨特的城市護教學,以解決黑人覺醒運動和其他黑人對基督教的反對意見。
回應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敘事
什麼是城市護教學? 城市(urban) 是當今的一個流行詞,在過去的四十五年裡,它的使用一直在穩步增長。 它指向的是城市。 在它成為一個俚語之前,城市 有又深又複雜的含義——由密集的人口、建築和交通所定義的景觀,以及文化、商業、政治和精神的多元化融合。
然而,在某個時候,“城市”成為黑人、棕色人種和窮人的代號。 這就是今天許多企業界使用“城市”這個字的方式。 公司的城市部門致力於向黑人和棕色人種推銷其產品。 當然,如今,城市文化不再局限於城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像嘻哈(hip-hop)這樣的藝術形式的急劇流行。 它是一種會移動的文化(mobile culture),我們在鄉村和郊區也會遇到的。
護教學 是一個依據彼得前書3:15創造出來的術語:“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give a defense to anyone,CSB)。” 這裡英文翻譯為“辯護”(defense,和合本譯為“回答”——譯註)的詞來自希臘語 apologia。 按上下文,護教學通過向他人展示基督的轉化工作,與人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互動。 它基於人在耶穌里所擁有的關於末世和迫切的盼望,是對福音的合理辯護。
就解釋護教學的《聖經》根據而言,猶大書第3節是另一個關鍵文本。“親愛的弟兄啊,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 爭辯(contend)這個詞翻譯自一個希臘詞(epago¯nizomai),指的是體育比賽,比如摔跤比賽。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9:25中暗示了這種關聯性:“凡較力爭勝(competes)的,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護教學有很多種類。 古典護教學(Classical Apologetics)強調對上帝存在的論證。 證據護教學(Evidential Apologetics)強調需要證據來支持基督教關於真理的論述,無論是理性的、歷史的、考古學的,甚至是經驗的證據。 歷史護教學(Historical Apologetics)強調支持基督教真理主張的歷史證據。 經驗護教學(Experiential Apologetics)訴諸一般的宗教經驗或特殊的宗教經驗,如明顯的超自然現象,作為相信基督的理由。 前設派護教學(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通常以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為前設,然後以多種方式說明為什麼只有基督教才合理。
當我談到 城市 護教學時,我特別指的是針對黑人的反對意見為基督信仰辯護,並論證基督教如何滿足黑人的獨特需求。 城市護教學以和諧的方式使用上述的幾種護教方式。 當我們與黑人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交談時,我們採用古典護教法,他們中許多人重視科學解釋,而不是基於信仰的論述。 在面對“向我證明耶穌的確存在”或是“《聖經》人物的墳墓都在哪裡”或是“基督教是在歐洲創立的”這樣的挑戰時,證據護教法特別有幫助。
在城市護教學中我們遇到的大多數陳述或問題,其根本原因是各種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敘事。 這些敘述吸引並肯定了許多黑人在種族主義和社會不公義方面的經驗。 為了駁斥它們,我們可以借鑒歷史和經驗式護教學的要素。 我們在城市護教學中的任務是以謙卑和謹慎的態度,存著禱告的心參與這些議題。
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裡講出真理
城市護教學所做的福音工作是根據少數族群在知識、情感和種族認同關切的問題,向黑人社群為基督教辯護。 儘管文化、歷史、靈性和神學上都存在黑人對基督教信仰的障礙,城市護教學為黑人提供了福音盼望的理由。 城市護教學的核心是恢復“上帝的形象”(imago Dei)。 因為種族不公和不平等的存在,我們需要既肯定人性,同時也挑戰人類罪惡的傲慢。 《聖經》要求我們把所有人當作上帝形象的承載者(創1:26-27;雅3:9)。
城市護教學還致力追尋在一個以謊言為特徵的世界中講述真理。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黑人宗教身份邪教(Black Religious Identity Cults,BRICs)宣傳假貨版真理的世界。 由於許多人還沒有學會區分真理與錯誤、真實與虛假,他們相信謊言。 大多數吸引黑人的意識形態或邪教也是基於猶太教——基督教世界觀。 他們根據基督教的故事來建構他們所謂的真理、拒絕基督教。 城市護教學致力語闡述只有基督教被證明是合理和真實的世界觀。
城市護教學還消除了黑人社群中存在的大量城市傳說、歷史神話、神學謬誤、科學誤區以及對基督教的簡化論(reductionist)觀點。 我們在城市護教學中對抗的大部分內容是在前幾代人中流行的論點,現在它們正帶著民族色彩重新出現。 例如,我們看到一種稱基督教不過是古埃及基米提斯教(Kemeticism)的複製品的理論重新出現,而這個理論早在幾十年前就被證偽了。
由於黑人群體對白人和歐洲思想極不信任,許多黑人往往很容易受到任何關於白人腐敗的說法的影響,而基督教就是一個很容易的目標。 當 BRICs 提出基督教是歐洲白人所建立的白人宗教時,許多黑人相信了他們。 然而實際上,基督教是從耶路撒冷傳播到非洲,然後再傳播到歐洲。 早在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在羅馬成型之前,基督教的核心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
人們願意相信歐洲人將基督教傳播到非洲,這突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正如神學家托馬斯·C·奧登(Thomas C. Oden)在其2010年出版的《非洲是如何塑造基督教思想的》中解釋的那樣,
現代思想史學家已經太習慣於這樣一個簡單的前設:無論非洲學到了什麼,它都是從歐洲學到的。 然而,就具有開創性的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而言,其從非洲到歐洲的軌跡(從南到北的運動)在文本上是清楚的。 但為什麼人們這麼容易忘記或否定這一軌跡呢?
關於非洲的基督教如何開始的錯誤信念,可以追溯到我們在世俗和基督教學術研究中看到的種族主義暗流。 在我自己對古實(緊鄰埃及南部的沿尼羅河的黑非洲王國)以及古實人在聖經時代所扮演角色的歷史研究中,我遭遇了仍然由白人學者主導的學術界中揮之不去的種族偏見。
我所說的種族偏見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不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在歷史和宗教學術中相對普遍的公然種族偏見。 相反,我們今天遇到的是潛意識或微妙的種族偏見——他們通常是無意的,卻仍然是真實的。 這種種族偏見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基督教歷史學界,它給非裔美國人向其他黑人分享福音的努力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下意識和同謀(complicit)的種族主義已經破壞了黑人社群的莊稼收成。
如今,我們在世界和教會中與種族主義對抗,與否認種族主義的存在、為白人身份優越性張目的黑人抗爭,並抵制正在摧毀我們社群的神秘主義邪教和黑人意識形態。 就在我們面前有艱辛的工作要做!
爭奪靈魂
當談到關於真理與謬誤的問題時,膚色重要嗎? 不是特別重要。 然而,白人在整個歷史中努力用白人的、歐洲的畫筆描繪基督教歷史,這使得膚色成為一個問題。 西方基督教學術界沒有帶頭對抗種族主義,而是跟隨了世俗修正主義者的腳步。 這種對歷史的粉飾是神所厭惡的。 用自己喜歡的人種膚色來描繪歷史,而不是研究《聖經》中提到的人和教會歷史上重要人物的真實民族身份,這是會造成分裂的。 這是對福音本身的侮辱,因為它暗示上帝只是通過歐洲白人拯救和做工。
我不能責怪我的黑人兄弟們對基督教不斷的懷疑。 護教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罪,而城市護教學則探討了這種罪如何影響少數民族。 可悲的是,正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罪惡的種族主義和不公正,這是必要的,。 你能想像人們拒絕福音,是因為他們相信福音只適用於白人嗎? 願它永遠不會發生!
我們的任務是給出答案,回應黑人所經歷的心理創傷,因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經與歷史上的(非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融合在一起。 自初代教會時期以來,基督教一直得處理一群人想要排擠另一群人的問題。 基督教是否只預備給某個特定民族的問題並不新鮮——這問題可以一直追溯到彼得關於列國得救的異象(徒10)和耶路撒冷會議(使15)。 加拉太書第二章更進一步表明,基於民族差異排斥人是福音的核心問題。
最後,我們蒙召向所有人傳福音,無論他們的種族或背景如何,而我們這樣做都是靠著神所賜的大能。 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2:1-4中所說: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保羅在這裡訴諸哥林多信徒自己信主的經歷。 拯救他們的是十字架軟弱但大有能力的道,而不是人類有力的修辭(1:18)。
護教學不是為了贏得辯論;它是關於爭取聽眾的靈魂。 不要搞錯了:雖然我們要克服民族身份、種族主義和不公義所立起的障礙,但最終我們試圖幫助人們認識到自己的罪(約16:8)。 我們的盼望是聖靈會照亮他們對福音的需要。
我們不想只談論他人對黑人犯下的暴行。 我們不會忽視這些暴行,但我們絕不能讓它們阻止我們強調 每個 人在我們生命中對耶穌基督福音救贖大能的需要。
本文摘自《城市護教學:用福音恢復黑人的尊嚴》(Urban Apologetics: Restore Black Dignity with the Gospel),由埃里克·梅森(Eric Mason)編輯。 版權所有 © 2021 Zondervan。 使用需經 Zondervan 許可。 www.zondervan.com。
翻譯:Addison Lin
責任編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