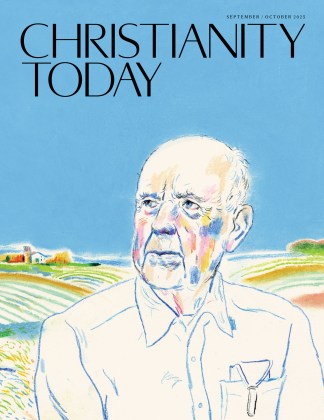年齡在18至28歲之間的教會會友,比起他們的哥哥姐姐、父母或祖父母,更常出席教會。一項由巴拿研究機構 (Barna Group) 與Gloo公司推動的「教會現況」(State of the Church) 研究計畫發現,疫情後,已滿18歲的Z世代教會會友的出席率正迅速成長。
如今,根據巴拿的調查,1997至2007年間出生的人,平均ㄧ年52個主日中,會出席約23次主日聚會。相比之下,X世代 (1965-1980年代出生) 的基督徒一年大約出席19次,而嬰兒潮世代 (1946-1964出生) 與更年長的一代 (1928-19-45出生) 則平均一年不到17次。
千禧世代 (1981至1996年出生) 的會友,一年參加聚會的次數為22次,較2012年最高紀錄的19次有所上升。巴納在新出爐的研究報告中稱此現象為「歷史性的世代逆轉」。
巴納副總裁柯普蘭 (Daniel Copeland) 在聲明中說:「年輕人比過去更常出現在教會裡,並不是個典型的趨勢。這些數據對教會領袖而言是好消息,也為教會補上這樣的畫面:靈命復興正在塑造今日的Z世代與千禧世代。」
不過,巴納這份研究 (基於1-7月之間進行的5580份線上調查) 並未關注美國整體教會出席人數下降的現象。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不到30歲的成年人之中,只有45%會參與宗教聚會——這個比例似乎在十年間下降了將近20個百分點,雖然不同研究的數據難以精確互作對比。
Z世代的教會出席率在過去五年內上升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那些委身程度較低、不太固定去教會的人,如今乾脆完全停止出席;而那些仍會去教會的人,反而更可能更頻繁地出席。
與此同時,巴納的數據也顯示,即使較年長的世代仍會去教會,他們出席的頻率也在下降。
「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好像人們每週都會去教會——主日去兩次,再加上主日學和週間的聚會。但數據顯示,這種模式已經改變了,」巴拿執行長金納曼 (David Kinnaman) 告訴本刊。「數據幫助我們看清那頭房間裡的大象:如今人們去教會的頻率,大概是每五個週末之中的兩個。」
巴拿的研究發現,1946年以前出生的教會會友,2025年的平均出席次數比2000年時少了11次;1946至1964年間出生的會友,每年則比過去少了7次主日出席。換句話說,他們一年有1.5個月及3個月的時間在教會缺席。
並且,有大量年長者乾脆完全停止去教會。雖然皮尤研究中心表示,因調查方式從電話訪問轉為網路問卷,要做直接比較有一定困難,但2007年的調查顯示,約有22%的65歲以上人士很少——或未曾去過教會。而在最近的調查中,這個比例已上升到40%。
若數據正確,就代表在過去20年間,每100位長者中,就有18位不再參與宗教聚會。
「我們在宗教社會研究中看到的一個較大趨勢,就是原本有兩種基督徒:『實踐信仰的』與『不實踐信仰的』基督徒。而就像在篩選麥子與糠秕那樣,後者正逐漸轉向自我認定為『無特定宗教者(nones)』,」金納曼說。「這也是為什麼聽到年輕世代說:『我覺得我們沒有真的給宗教群體足夠的機會證明自己』會讓人如此驚訝。」
新冠疫情的限制解除後,許多會友似乎重新評估了自己想如何度過週日早晨。
巴納發現,X世代的出席率已經回到疫情前的水準——甚至比2000初稍微增加。如今,X世代會友平均每月參加1.6次主日聚會。
而根據巴納的數據,千禧世代的出席率同樣在上升。今天,29至44歲的會友平均每個月會參加1.6次主日聚會,比2000年時一年多出約6至7個主日。
巴拿的研究人員認為,這些數據印證了許多牧師對教會人口結構變化的直覺感受:年輕人出席更頻繁,而且整體平均出席率 (也就是人們實際到教會的頻率) 正在變化。研究指出,許多牧師因為會友出席不穩定而感到挫折,覺得因此難以在會眾中建立持續、積極的動力。
與此同時,教會科技公司Gloo則希望基督徒領袖能看見新的可能性。
「這些教會出席率的變化為領袖們開啟了創新的大門,」Gloo總裁希爾 (Brad Hill) 說。「那些優先經營人際連結和數位互動的教會——例如透過教會電子報、社群媒體和其他線上工具——能更好地在年輕世代所在之處與他們互動。」
巴拿執行長金納曼盼望這些數據能幫助教會領袖「更積極主動」,並鼓勵他們專注於如何有效地回應人們的屬靈需求。
金納曼說:「教會生活的結構正在改變。我們真的需要認真思考年輕世代的學習需求,和信仰相關內容上的需求,以及當人們平均每五個主日只會出現兩次時,我們該如何規劃門徒訓練、信仰課程,以及建造教會群體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