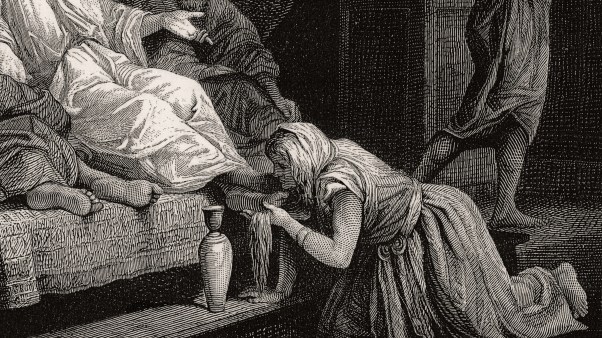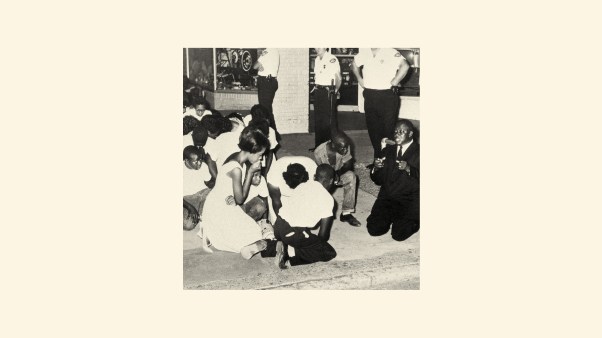幾年前,我開始越來越常聽到有人說:「推特上發生的事,正在成為這世界的真貌。」
他們的意思是,這個社交媒體app上的有毒爭論,正在定義整個時代——影響並塑造人們彼此溝通的方式,從學校董事會會議,到總統玫瑰園的記者會,再到教會的事工會議,無一倖免。
然而,如果「推特時代正在結束,我們文化的下個時代將由抖音 (或任何短影音平台) 來定義」呢?這會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這個問題在我心中盤旋了好幾週,起因是我意外聽到有人對美國民主的未來提出一個相對樂觀的看法。但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個看法的基礎竟然是:抖音/短影音。
在《以斯拉·克萊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 的一集中,《紐約時報》記者克萊因和電視評論員海斯 (Chris Hayes) 討論今年夏天早些時候,社會主義者曼達尼 (Zohran Mamdani) 在紐約市長民主黨初選中擊敗前州長古莫 (Andrew Cuomo) 的事。這段對話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當兩人開始取笑古莫嘗試抖音技巧的場面。
事實上,他們的話題很快就跳脫古莫本人,轉而談論許多民選官員與候選人在抖音上尷尬跳舞所造成的「社死」感,官員每一次的嘗試都證明他們與這種 (和選民的) 溝通方式格格不入。
克萊因與海斯推測,如果要從社會學角度觀察曼達尼的勝利,最重要的或許並不是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也不是他的「反以色列」外交立場,而是他「達到勝選的方式」:曼達尼似乎是美國大型選舉上,第一位能自然地用抖音和Instagram短影片來溝通的候選人。
「我實在不想過度引用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的理論,說什麼媒介就是訊息、人人都被自己所使用的媒介塑造⋯⋯因為很明顯地,在抖音或短影片平台上,很多人並不像曼達尼那樣深暗操作法則,或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說的這個理論是什麼意思,」克萊因說。
儘管如此,克萊因指出,我們仍應關注社交媒體平台的演變,是如何加快美國政治生活中所謂『氛圍轉變』(vibe shift) 的速度。為了說明他的觀點,克萊因舉例,歐巴馬其實就很不擅長使用推特。這並不是說歐巴馬在數位溝通上很笨拙——事實上,歐巴馬可能是第一位真正有效運用這些媒介來動員並維持支持群體的政治人物。但歐巴馬並不是推特的「原生物種」,克萊因說:
隨著民粹右派的興起,以及程度稍輕的民粹左派政治在全球各地同時冒出來——這個集中爆發的時期始於2000年代末或2010年代初,我認為導致這種現象其中最強大的驅動力,不僅僅與移民問題有關,也不是經濟因素導致的 (從數據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一點)。我認為,關鍵力量是「核心政治溝通平台」的興起,而這些平台的特徵是以高衝突、高互動,以及精簡的文字為主要表達方式。
「這些平台,在意的是『群體』,」克萊因表示。「平台關注的是一個群體內部,以及此群體和其他群體的互動;平台在意的是以極其精細地方式劃分群體間的分界線;平台的本質使其孕育出更民粹化的政治形式,或至少會創造一種政治溝通的結構,使外來的民粹派政治人物更容易茁壯成長。」
你不需要完全認同克萊因的論點,也能看出他所描述的輪廓——甚至在教會中亦是如此。
但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講道者,或一名成功的佈道家,所需的能力與在推特 (現為X) 上吸引追隨者來獲得「影響力」的能力完全不同。推特 (或Threads等短文字平台) 無法承載深思熟慮或深度的論述、交流方式,只能依靠「釣魚」式的衝擊戰術——挖掘越來越極端的立場,並以激起憤怒或恐懼的方式大量傳播。在這種情況下,「敵人」與「朋友」一樣,都是能放大影響力的有用工具。
然而克萊因認為,像這樣的科技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就像2000年代中期興起的臉書時代,那種「希望及改變將使我們團結」的氛圍,最終消散了——短影音平台上的暴戾氛圍也會如此。
「接下來的時代——你看看抖音、再看看Instagram短影片——我並不是說高衝突的政治內容會消失,而是其中的內容已開始更多是關於日常生活事物,」他說,「而且是非常高度視覺化的。」
克萊因在一些新一代的年輕政治領袖身上觀察到,他們使用的「語言」不再是推特的語言,而是抖音的語言。海斯承認:「對,就是那種有趣、帶點搞笑耍蠢的溝通方式。」
讓我們先暫時不定論這個現象是真還是假、好還是壞。先問問:這些政治人物「試圖呈現」的是什麼?——走上街頭,與人交談並聆聽他們的聲音。
如果這種現象開始成為美國政治的主導風格,會不會塑造一種新文化?也許會。這會不會與在推特/社交媒體上策劃激起人們憤怒情緒的文化不同?也有可能。但文化生態中衝突的減少、視覺表演的增加,是否就必然對民主有益?答案是否定的。
哲學家巴爾巴-凱 (Antón Barba-Kay) 在《刺蝟評論》(Hedgehog Review) 中指出與克萊因相似的論點——有種轉變正在發生,他稱這種新的政治環境為「抖音治國」(TikTokracy)。在這樣的文化中,民主不再根植於公民教育或理性辯論,而是取決於誰能在演算法的注意力爭奪戰中勝出——但這仍是推特文化的一種延伸,而不是逆轉。
對巴爾巴-凱而言,這不只是政治問題。失去「閱讀及理解」較長篇的論述,並以此來說服他人的能力,動搖了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更別說,我們甚至還沒討論另一個大問題:究竟是哪一小群科技創業家、國際大勢力、企業或政府在控制這些攫取我們注意力的演算法?
幫助人們重新學會「專注」的第一步,就是視他們為「有能力專注的人」。政客或許需要學會如何「佔領」短影音的領域,但那是因為政客僅僅是在回應又一次的文化變遷、迎合被這一波文化塑造出來的人。
然而,教會有責任塑造門徒——為他們的未來,以及他們所能影響的人的未來作準備。
在這個意義上,教會的呼召並不是要設法掌握所謂「抖音的語言」,或掌握下一個取而代之的平台的語法;而是要真正意識到,我們身處的文化語言正在塑造我們、形塑我們、「門訓」我們,甚至影響我們所提出的問題。
我們不僅僅需要為有疑問的慕道者提供答案 (即使這依然很重要)——我們更需要的是,建立一種帶領、以身作榜樣,及內在文化的方式,作為「逆著演算法而行」的力量。我們需要聽到聖經不斷大聲說出的那句:「耶和華如此說」,也需要耶穌教導我們的:「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路加福音8:18) 。
耶穌對我們說過的許多話都是逆著文化而行的。面對未來的年代,祂所說的最難做到的教導之ㄧ,可能正是我們許多人忽略的提醒:留心你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何處上。
羅素·摩爾 (Russell Moore) 是本刊總編輯,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