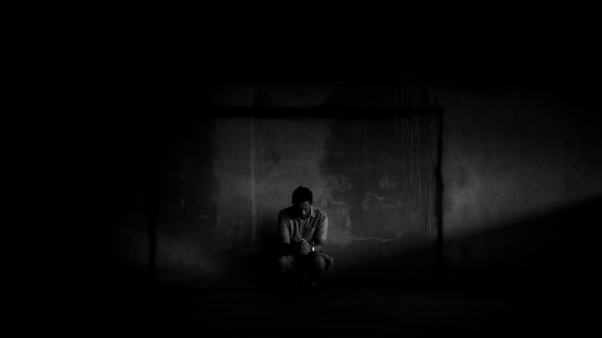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史蒂夫牧師有空嗎?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問他!」
她沒有說出她的名字,但我認得電話另一端的聲音。事實上,我的腦中浮現她習慣的座位——那個她每週都會慢慢走向的座位,儘管禮拜已開始十分鐘,我們甚至已進入認罪禱告的環節了,她仍毫不在意地姍姍來遲。(我竟然會記得這種細節,求主饒恕我愛審判人的心。)
「不,女士,」我說。「他現在不在。有什麼需要我轉達的嗎?」
我通常不會接教會的電話,畢竟我的職務是傳訊總監。然而,那天我正好在前台代班,沒想到,不只是我們的接待員和主任牧師外出辦事,這位來電者想找的大多數人都剛好不在辦公室。
「那麼,瓦爾特牧師呢?他在嗎?或是夏洛特牧師呢?」她的聲音開始有點急切,讓我不禁擔心是否出了什麼事。
「很抱歉,他們兩位剛出去吃午餐,應該一小時內會回來。在他們回來前,有什麼是我可以幫忙的嗎?」
「嗯⋯⋯我不確定,」她嘆了口氣,接著說,「也許可以⋯⋯」
在沒有其他更——更接近牧師的人選後,她直接拋出那個讓她急切不安的問題。
「『抹大拉的馬利亞』該怎麼拼寫?」
我加入這間教會的同工團隊已快十年了。我的辦公室靠近大門接待處,所以即使我不接電話,也能聽見這座繁忙的市中心教會每日人來人往的聲音。
當然,並非所有來電都像這通「聖經單字拼音」查詢那麼有趣。有些人從醫院的停車場打來,耳邊仍迴盪著剛剛得知的沉痛診斷;有些人則打來報告奇蹟似的痊癒消息。有自豪的祖父母特地來分享他們新生孫兒的照片,也有心碎的父母前來請求為叛逆的孩子禱告。我們接到過求助教會幫忙付電費帳單的電話,也接過那些只是想親耳聽到活生生的人親口說出:「是的,我們真心相信上帝存在」的來電。
多數人想到教會時,腦中浮現的畫面是主日早晨——擠滿人的長椅、優美的詩歌、衣著整齊的家庭。但這些年來,我越來越喜歡我的教會在週日之外的樣貌。
我喜歡週一早晨的教會,街友們會進來喝杯咖啡,借用乾淨的廁所。我也喜歡週二早上,看著一群背著比自己還大的背包的幼兒園小朋友,蹦蹦跳跳地在人行道上,搶著按下那顆能讓厚重玻璃門如魔法般打開的無障礙按鈕。
我喜歡午後時光,當「裁縫小組」的成員們陸續抵達,圍坐成圈,一邊聊天,一邊編織要掛在教會長椅上的禱告披肩 (prayer shawls)。我喜歡看年長的女士們來到教會,檢查祈禱室裡是否有新的代禱卡片;也喜歡觀察送貨司機在繼續行程前,進來教會拿瓶汽水的模樣;還有帕特 ,他幾乎每天都會來教會讀早報。我喜歡看對街公立高中數百名學生每週四中午過來吃教會提供的披薩,或是每個週三晚上,教會家庭聚集在教會一同享用晚餐的溫馨時刻。
我可以這樣一直講下去。因為我的教會很少有安靜的時刻。教會同工不停地佈置教會,然後再拆下來,總是在為下一批來訪者做準備。不同的詩班在走廊裡練習,音樂充盈著空間,而我們的風琴師一遍又一遍地彈奏同一段旋律,直到她覺得完美為止。在這歡樂的喧囂背後,鐘樓上的鐘聲日日敲響,標記著時光的流轉。
1991年,社會學家雷·奧登堡 (Ray Oldenburg)提出「第三空間 (third places)」的需求性,他認為,非正式的公共聚會場所對社群的健康發展和民主至關重要。教會建築物當然首先是個敬拜的場所,但當它在週日以外的時間向會眾及更廣泛的社區開放時,它仍能在這個數位化、碎片化的世界裡,扮演著重要的社區角色。教會確實是「第三空間」,是庇護所,是安息之地——是一座真正的聖殿。
早在三十年前,奧登堡就擔心第三空間的式微將帶來長遠的負面影響。當街區的小餐館、商店、劇院、圖書館和公共廣場逐漸消失時,我們便失去了像電視影集《歡樂酒吧》那樣夢幻的地方——在那個每人彼此熟識的地方,人們可以坐在一起,透過一杯咖啡或一品脫啤酒,共同面對、甚至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即使無法解決,也至少能與他人分享)。我們也失去了與他人交流的機會,少了接觸到那位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令人惱火的政治言論、但一但我們的車拋錨,卻會毫不猶豫地幫我們接電發動車子的鄰居。
雖然星巴克四處林立,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節奏快速的社會中,星巴克很難成為那種熟客相識、彼此關懷的地方。而且,作為商業機構,它們並非對所有人開放——你得消費,甚至得有能力消費,才能坐在那裡。
但教會不一樣。教會重視的是人,不是消費者。教會應該是人人都能找到歸屬的地方,不需要任何交易或交換。
在《大西洋月刊》近期一篇封面文章中,德里克·湯普森 (Derek Thompson) 提出,我們正活在一個「反社交」的時代 (antisocial century)。我們彼此間及與周遭世界互動的方式正發生極大且快速的變化,這並非僅是一時的熱潮——我們的思維方式已被重新塑造。
正如湯普森觀察到的,這個景象隨處可見:孩子們寧願在網路上和朋友玩電動遊戲,也不願和他們在商場見面。餐廳的外送取餐處經常堆滿餐袋,比店內座位還要擠。你可以不出門就與私人教練、心理諮商師甚至醫生見面。個人的方便和舒適是優先考量,但當我們把家打造成城堡時,是否也無意間讓它變成了「獨處牢房」?
當然,舒適的感覺很好。但正如湯普森所說,人類並不總是善於分辨自己需要和想要的東西: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期待能讓我們心安的物質——更大的房子、豪華的汽車、一份薪水翻倍但閒暇時間減半的工作——結果往往只是更多的焦慮。而在這堆我們誤以為是自己「想要」的東西之中,第一名便是「獨處」。
我們想要的,不一定總是對我們有益,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彼此。
湯普森雖是位不可知論者,但他的觀點彷彿是教會講台講出的。身為基督徒,在這個反社交的世代中,我們擁有一個獨特的資源:一個要求我們有意識地經常彼此同在的傳統。
這正是教會最早期的功課之一。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五旬節過後不久,初代教會人數迅速增長,基督徒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2:42 )。成長過程中,每次讀到這段經文,我總會想像成主日禮拜後的教會聚餐/愛宴。然而,這裡所說的「交接」的希臘文是koinonia,它的含義遠不僅僅是聚在一起、分享食物。我們通常將koinonia翻譯為「團契/聖餐 (communion)」。
koinonia意味著「共同參與」:一種既付出又領受的團契關係,其中帶著某種程度的義務與責任。亞里斯多德在討論 koinonia politike——英文通常翻譯為「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時,用的便是koinonia,更明顯地表達了這個字的含義。
我 104 歲的曾姑姑去世前,送了我一張手縫的「拼接被 (make do)」被子套,那是她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曾祖母,在美國德州大草原拓荒時,與一群婦女圍坐在縫紉圈裡一針一線縫製而成的。它色彩斑斕,布料的質地與圖案各異,交織成一幅絢麗的萬花筒。每當我細細端詳那縝密的針腳,腦中便浮現當年的畫面:婦女們坐在一起,分享手邊僅有的布料碎片,用僅有的資源彼此扶持、分擔重擔;在荒涼、狂風呼嘯的草原上,為自己與家人打造新生活。
當男人們架設圍欄、翻耕土地時,女人們縫製被子。這些被子就像豐收的糧食一樣,是這些家庭的生存必需品,因為當冬季的寒冷從泥屋的縫隙中滲透進來時,溫度成了生命的保障。然而,在這些縫紉的群體裡,人們不僅用針線縫合布料,更在聊天、團契及彼此關心之中,一針一線地編織出一個新的社會。
一百年後,公民社會的拼布依然覆蓋著我們所倚賴的每一個制度及社會契約。然而,這塊拼布已經開始破損,我們卻沒有及時修補。隨著這張網絡越來越薄弱,我們的社會信任也隨之崩解,逐漸失去正常運作的能力。在一個自由且平等的社群中,公民之間的合作能夠防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或極權統治,但這樣的合作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它必須由人 刻意地培養及建立。Koinonia——所謂的「聖餐/團契」,這種主動給予及領受的關係——是我們的責任。作為天國與這個世界的雙重公民,我們的神聖使命就是有意識地操練「出席/同在」這個屬靈操練 (the spiritual discipline of showing up)。
對越來越習慣過獨居、獨處生活的人來說,這項責任一開始可能會顯得沉重。但只要我們忠心堅持,最終它會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它將使我們從這個反社交時代中孤立的個體,轉變為 koinonia 的實踐者,而這不僅會改變我們個人的生命,更將為我們的群體帶來豐碩的果實。
《希伯來書》第 10 章為像我們這樣充滿爭論和複雜的時代,提供寶貴的指引:「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 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24-25)
在公司裡,接待員的主要職責是將來訪者引導至該去的地方。但在教會裡,這只是接待員工作的一部分。我們教會的接待員名叫凱西,她真正的事工並不是接聽電話,而是我們稱之為「臨在的事工 (ministry of presence)」。
她在教會的接待櫃檯實踐聖經所說的「款待之道 (羅馬書12:13)」,用溫暖、關心及基督的愛來迎接學齡前兒童、會友,以及路過的人。有時候,當凱西聆聽完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後,我會聽見她從座位上站起來,問道:「我可以過來給你一個擁抱,為你禱告嗎?」
雖然,來到教會的人的現實困難仍然存在,教會或許能夠、也或許無法滿足他們的物質需求。但在那一刻,他們被凱西「看見了」,被她「認識了」。她以行動讓他們想起,他們也被上帝看見、被上帝認識。她所付出的關心或許微小而平凡,但這種愛的表達卻與當今的文化「逆道而行」,就像寡婦的兩個小錢一樣,雖然微小,卻已足夠 (可 12:41-44)。
「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魯翰 (Marshall McLuhan) 在談到科技時,曾說:『每一次的增強,同時也是一次截肢,』」湯普森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寫道。「我們選擇了數位科技增強的世界,卻沒意識到自己正在失去什麼。」
或許我們當下沒有意識到,但作為基督的跟隨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一直都知道。我們的信仰警告我們,與葡萄樹——那永活生命的主——隔絕,是何等的危險 (約翰福音 15章)。
我們必須在基督裡,生命才能興盛成長。而既然上帝是我們整個生命的主,這份「連結」當然不僅限於靈性上的滋養。我們需要在這個孤立的世界裡,與上帝、與他人保持連結,不只是主日早晨,更是在每一個尋常的星期二午後。透過這樣的堅持,我們將讓世人看見,當我們失去koinonia (團契)時,失去的究竟是什麼?而每一次意料之外的關係建立,都是對破碎社會的一次修補。每一次愛的縫合,都是在將孤獨、受傷與被遺忘的人重新編織進群體之中。
這是教會,這是教會的尖塔~,我想起自己童年時在教會長椅上,默唱著這首歌,ㄧ邊配上歌曲的動作,等著講道結束。打開門,看看所有的人~。
Carrie McKean 是一位來自德州西部的作家,作品曾刊登於《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和《德州月刊》雜誌。可在carriemckean.com看到有關她更多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