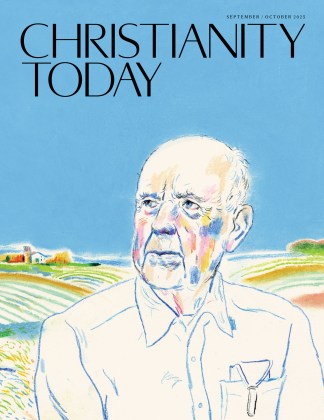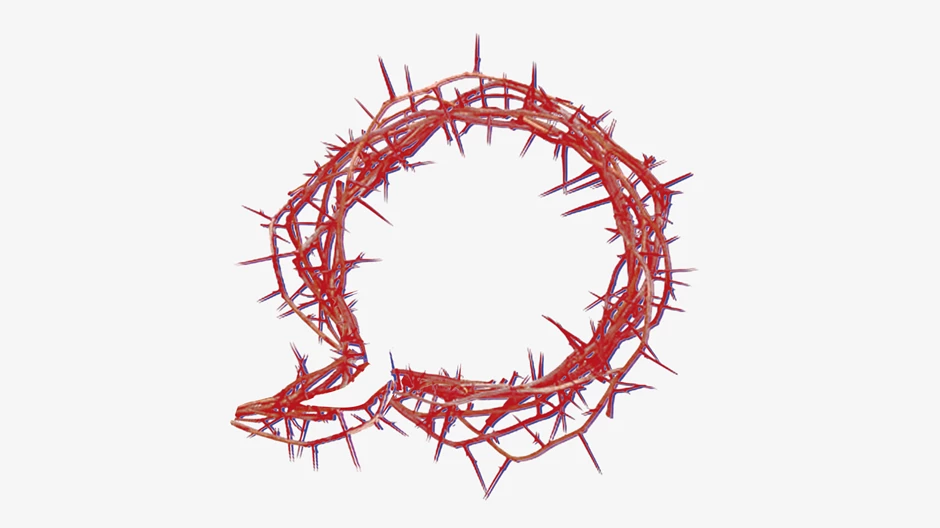幾年前,改革宗哲學家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為「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下了一個實用的定義。他指出,在學術環境中,原教旨主義者基本上是個污辱人的詞,有點類似⋯⋯(普蘭丁格用了一個我不能寫在這裡的詞)我舉個例子吧,類似「蠢蛋」。
當然,除了羞辱人的意思外,普蘭丁格認為,「原教旨主義者」的意思是,「從神學角度來說,我和我的開明朋友們相當偏右」。因此,學者、記者和許多基督徒開始用這個詞來形容所有「神學觀點跟自己相較之下,相當偏右的蠢蛋」。但由於總是有人比自己更靠右邊,所以「蠢蛋、原教旨主義者」這個詞的定義基本上是相對的:沒有固定的參考物,但反正說的絕對不是我自己。
如今,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評價「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這個詞已經失去了實質內容,變成相對性的詞。幾乎在所有談話中,這個詞跟「原教旨主義者」一樣,除了指那些「政見與我大相徑庭的蠢蛋」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意思了。「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標籤幾乎可以貼在任何事上:也許它指控的人是個名副其實的納粹。也許它指的是ㄧ個非常關心墮胎及稅收議題、終身支持共和黨的人。
最近,一些有想法、有善意的人努力以一種有用的方式來定義「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彙。但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淘汰它,再也不提到它。雖然它曾經對特定群體和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現在已經不再適用了;這個詞彙剩下的只有面紅耳赤的爭論,沒有光。甚至多數時候,這個詞彙都是被用於誹謗他人,而幾乎在所有情況下,人們使用這個詞來與人劃清界限。
確實,有時我們需要的正是界線。我不會給優生論者或否認猶太大屠殺真實存在的人一個公平的聽證會。但這些都是邊緣極端的情況,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中,公共討論的本質是粗暴的、多元的,偶爾會令人不舒服。我們需要傾聽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尤其當我們不同的程度很深的時候。如果我們是致力於熱情待人和愛敵人的基督徒,我們傾聽的意願應該要更強烈。
此外,所有有責任感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反對者」——那些沒有魯莽地把這標籤貼在所有比自己右邊一點的蠢蛋身上的人——對這個詞彙都有合理的擔憂。我認為有至少五點擔憂。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義往往帶有一個修飾詞:白人。
這一點的確值得我們抨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如此。但請注意它令人擔憂的原因:不是因為它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因為它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種族主義。任何透過社會地位提升或透過政治特權使一個種族凌駕於其他種族之上來作為其定義的政治運動,都值得我們譴責,無可辯駁。
其次,反對者對基督教民族主義不受法律約束的行徑感到擔心是有道理的,2021 年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騷亂就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典型例子。
有時,不受法律約束意味著不願意遵守規則。有時,不受法律約束意味著拒絕接受政治上的失敗。有時,它意味著訴諸暴力。除了基督徒出於公義的理由而參與的無暴力的公民不服從外,基督教民族主義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展現形式應被所有基督徒譴責(羅馬書第12-13章皆與此有關)。在美國首都發動宗教政變的想法應在萌生之際就被基督徒斬斷。
第三,批評者通常擔心的不是民族主義本身,而是陰謀論和煽動恐懼。
小說家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認為,恐懼「不是基督徒的思考習慣」。她說得沒錯。基督徒可以合理地辯論這個世界和我們國家的現狀,但我們無法合理地辯論基督在這個國家的主權或再臨的盼望(提多書2:11-15)。即使我們最恐懼的事情成真了——我們被某個禁止我們敬拜上帝的政權征服,和教會歷史上以及今日許多基督徒的處境一樣——我們的呼召也是一樣的:數算代價,背負十字架,跟隨基督至髑髏地。
第四,ㄧ些倡導要「把美國基督教化」的人似乎為非基督徒預設了一種次等公民的地位。
此時,那些恐懼被穆斯林或世俗世界「奴役」的基督徒試圖扭轉局勢,反身讓基督徒身份成為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有時,他們會把聖經包裝成一種管理文件,與憲法同等地位,或甚至取代憲法。我承認,我懷疑是否真有大量的美國人真心希望這種事成真,就像我尚未遇到一個真的支持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人一樣。如果反對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學者將他們的抨擊範圍局限在這類支持神權統治的人身上,他們的目標便是正確的——只是我懷疑這樣的目標會小很多。
第五,也是最後一點,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批評者非常正確地反對將上述幾點——種族主義、不守法規、製造恐懼、不公義的行為——披上基督教信仰的語言和符號的外衣(宣稱這是「聖經的教導,是基督教教義」)。
這種將基督降低至自己在世俗生活得到益處的手段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時代(腓1:15-18)。這種做法是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基督的名;這種做法宣稱基督是所有人必須服從的主,同時卻把祂的生命樣式和教導放在一邊。它將聖靈所結的果子視為軟弱無能,卻將肉體的作為——敵意、紛爭、忿怒、不和、放蕩和黨派紛爭——視為策略資產(加5:19-23)。
如果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內容僅僅包含以上這五個問題——成為「對福音的罪惡扭曲」這種行為的代名詞,我可能不會建議我們取消這個詞。但還有一些與上述無關、不應該被歸類在基督教民族主義之下的正當政治參與。
以下是應該與「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標籤脫鉤的六種信仰實踐。
1. 將上帝帶入政治之中。這一點我們能容易做到。在美國,我們歡迎所有信仰或無信仰的人將他們最深刻的信念帶入公共領域。沒有人需要假裝。無論是基督徒、猶太人或穆斯林,將信仰帶入民主辯論及對話的舞台上,在道德上、神學上或憲法上都沒有錯。
2. 將政治帶入教會裡。這一點比較棘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福音所公開宣稱的內容與聖所圍牆外的世界有關。這些主張涉及基督對萬國的主權統治,以及祂對窮人、邊緣人和弱勢群體的愛及關懷(路加福音6:20-26;馬太福音25:31-46)。對這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的敬拜永遠不可能真正與政治脫離——即使是艾美許派的分離主義和其他和平派教會的行為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行動。
3. 支持基督徒候選人競選公職。從人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比渴望在民主集會中擁有代表權更自然的事了。基督徒並不是唯一希望投票給與我們信仰相同的人的人,這種傾向並不值得擔心。有些基督徒只投票給基督徒同胞,這可能是不明智的——若這已經變成不容商量的標準,我覺得很不明智——但這還不至於上升到政治病態的程度。
4. 相信上帝帶領著美國。從微觀的意義上講,所有基督徒都相信這一點(上帝的權柄超越世上所有君王),而當無特定宗教背景的媒體對「天意」等相關的詞彙反應過度時,單純只是他們反應過度。但確實有許多基督徒贊同一種更強烈的說法:他們說美國是世界之光,是那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在上帝對世界的計畫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但我希望基督徒同胞放棄這種信念。這個信念所宣稱的內容實在太多了,這種宣稱忽視了教會的存在、忘記了以色列的教訓(羅11:1-2, 28-29)、過度將目光聚集在一個國家身上,而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一樣,終有一天會消逝(賽40:15;馬太福音24:35)。然而,實在沒有什麼比美國例外論還更美國的想法了。從建國開始,這種信念就一直伴隨著我們,往往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在這個問題上與我意見相左的基督徒通常不是激進的右派分子,而是再普通不過的美國人(尤其以老一輩和移民的標準來看),即使我不同意他們的想法,他們也不應被以如此貶義的方式貼上標籤。
5. 相信美國「是」或「應該是」基督教國家。正如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所記錄的,與美國例外論一樣,不正式的形容「屬於基督教的美國」的概念也深深根植於美國的歷史、文化和法律之中。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最近在《第一新聞》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基督教文化一直是美國的共識基礎」,而這一基礎在今天既可以恢復,也應該恢復。
霍利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不對的。但他的論點並非在呼籲基督教神權統治,甚至不是呼籲建立像英國那樣的國家教會,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主張「屬於基督教的美國」是合理的公共討論範圍。它與主張「美國應是世俗的」的論點一樣,都是美國式的。這兩種公共討論的意見都值得一聽。兩者都不荒謬,也不應被輕視。
6. 懷疑自由主義、民主或美國秩序。好了,這一點是極大的癥結所在。也許特別有愛心的讀者可以接受前五點,認為這是美國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不極端的觀點。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公開表示不支持自由,對民主持懷疑態度,或對整個美國聯邦共和國的架構持不確定的態度。難道他們這種想法沒有太越界嗎?這種人不危險嗎?難道我們不應用特殊的詞彙來形容「這類人」,並且這個詞應該要能強烈地表達我們的不贊同嗎?
也許吧。但請聽我分享我的理由。
基督徒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往往是以一種近視的「歷史終結」的心態來進行的。它無視基督教大部分的歷史,並視自由民主為人類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最終形式」。在這種觀點看來,我們正處於漫長進步過程的最後階段。我們無處可去,無事可做,只能保持自己的卓越。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對的。教會能夠並且將會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存活,歷史的終結不是21世紀初的美國,而是基督的再來。政治更迭、政府興衰、地圖重繪,在耶穌再次顯現之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歷史已經終結。當然,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值得珍惜或保護的東西。但是,把現在的情況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或最好被凍結在琥珀中,這在神學上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我的結果是什麼?基督徒可以質疑任何事。我們可以自由地對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持懷疑態度。
有時,這種懷疑是沒有道理的。但通常情況下,對既定秩序持懷疑態度的基督徒會幫助我們看到我們可能錯過的東西。多蘿西·戴(Dorothy Day)、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和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都曾對一些現代思潮打上問號:自由主義、民主、人權、資本主義、工業主義、核心家庭、數位科技、美國帝國——無論哪一個,他們都曾將其置於被告席上,對其進行質疑。這可能會讓我們覺得這些人不再支持我們了。但有時,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此,「懷疑民主」也不應被詆毀為一種基督教民族主義。至於我在最前面所形容的五種病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我們有理由反對,也有理由為它們貼上其他貶義的標籤,但「基督教民族主義」並不是最好的標籤。
這並不是說「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過於強烈。而是它太軟弱了。使徒保羅有個更好的詞來形容「基督教民族主義」:「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而這個更改過的「假福音」在政治上的展現只是這種精神疾病的症狀。但這類福音確實以現在進行式出現在基督的身體裡,這意味著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過,在我們振奮對抗假福音的同時也應受到責備:因為除了聖靈的大能,沒有什麼足以醫治這樣的假福音。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他著有四本書,包括《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