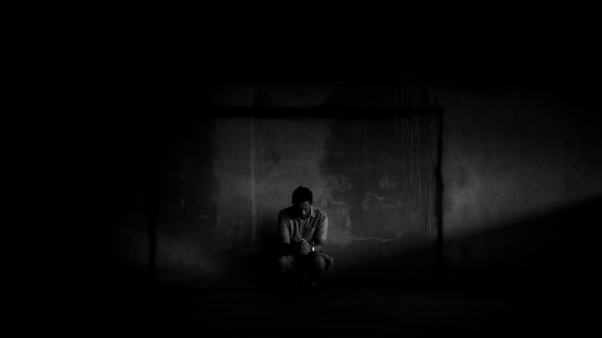2022年六月的最後一個主日,陽光明媚。芝加哥橋港(Bridgeport)新生命社區教會到附近的一個公園舉行戶外敬拜,也是這個教會英文堂和中文堂聯合聚會。當天兩個堂的兩位牧師用茶聊對談的方式講道,會眾則散坐在公園的草地上聽道、禱告。講道前帶領大家唱詩敬拜的人當中,吉他彈得相當有水平的弟兄是崔宇,主要領唱的姐妹是小旭。
崔宇和小旭是“荊棘火”樂隊——一個由一批年輕的基督徒中文聖詩創作者組成的團隊——的成員。這個團隊的屬靈帶領人是新生命社區教會中文堂的年輕牧師沙龍。
再早幾個月,陳明在佛羅里達奧蘭多的一個校園事工退修會中帶領敬拜。他是基督使者協會(AFC)校園事工的全職同工,同時也是另一個聖詩創作團隊的組織者。去年,在AFC的農莊退修中心舉辦的職青基督徒創意營會上,帶領詩歌敬拜的人當中有位吉他手叫欒欣,他同樣是既從事聖詩創作、又從事校園、職青事工的同工。
這幾位年輕的中文聖詩創作者目前在華人基督徒當中還不太有名,他們創作的詩歌還沒有像諸如“讚美之泉”、天韻合唱團和泥土音樂那樣的創作團隊的作品在華人教會中廣泛地被用在敬拜讚美中。但是他們的詩歌創作跟校園或職青事工關係更密切,而且他們更願意在新媒體上發布自己的作品——例如“荊棘火”會把一些他們新創作的一些作品錄製出來放在他們的YouTube頻道上。
華人教會愛唱的詩歌,一些是從優秀的英文詩歌翻譯而來,一些是像“讚美之泉”等比較知名的中文詩歌創作團隊的作品。我對這批年輕的來自中國的基督徒聖詩創作者充滿好奇:他們為什麼會認為需要創作新的中文聖詩?他們從事創作的動力跟他們委身的校園及職青事工有怎樣的關係?他們在詩歌創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他們如何看待別人創作的中文詩歌,以及對提高自己創作的水平有什麼想法?……
帶着這些問題,我採訪了沙龍、崔宇、小旭、陳明和欒欣等幾位詩歌創作者,請他們分享個人的創作動機和感想。
請問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創作中文詩歌?
沙龍:對我來說,想用中文創作新的詩歌詩歌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們就是中國人,中文就是我們的母語。而我是蒙了上帝的呼召要來事奉一個主要由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和職青構成的華人教會。我們當然也會使用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詩歌以及其他中文詩歌創作團隊寫的詩歌來敬拜,我們也為已有的中文詩歌感恩。但是我還是希望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自己創作新的詩歌。
用詩歌敬拜上帝本來就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就像我們常說禱告對基督徒來說就像呼吸一樣必須,唱詩敬拜對基督徒來說也像吃飯、喝茶一樣自然。我喜歡中國的美食和茶文化,也有一點做飯和泡茶的恩賜,所以很自然地,在我的服事中,我會自己動手為教會的年輕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做飯、泡茶。這是一種很接地氣、也能夠發揮自己恩賜的服事。創作詩歌也是如此。我信主以前就喜歡彈吉他、玩音樂,也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現在回頭看,感覺上帝都有預備。
陳明:老實說,我對自己創作中文詩歌沒有太多把握。但是我自己是學音樂出身,有過音樂的專業訓練;同時,我又受過基督教教育的裝備,在我的神學理解當中,詩歌創作是非常好的一種個人敬拜神和反思信仰的操練與體現。作為一名傳道人,我也認為這是我以創作為途徑,來鼓勵弟兄姐妹們、幫助大家反思和操練信仰的一個重要的服事。所以詩歌創作確實是我服事的一部分。
在你創作的過程中,你感覺最困難的難處是什麼?
崔宇:我覺得最大的困難,也許是尋找到介於服侍教會和自我表達之間的平衡吧。一個創作基督教音樂的人,自然希望用最好的詞句來表達他內心最真實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如果能找到知音,是很幸福的,但如果不能,他也不願意違背自己的初心,去表達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聲音,只為了迎合周圍的人的審美。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又的確不能放下服侍教會的心去做詩歌,因為這是神對我們的呼召。有的時候,我們的作品可能過於集中在自我表達,以致很難被會眾理解。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可以被人聽懂,可以帶給人見證,可以帶給人感動、鼓勵、啟發、安慰,最終可以幫助人們追隨他們的信仰,與神更加親近。如果我們寫的詩歌僅僅想要自我表達、自我感動,而失去了群體敬拜的功能,它們仍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
小旭:創作出和歌詞契合、並且好聽不落俗套的曲子,對我來說有很大的難度。因為我不是學音樂的,對樂理和樂器的掌握有限。
陳明:我以前曾經是一名流行歌曲的詞曲創作者,寫曲子對我來講並不是最難的,反而是作為詩歌信息主要載體——歌詞部分的創作,是我認為最困難的地方。我心目中那種具有層次與深度的詩歌歌詞,至今還未創作出來。
能否以你自己寫的詩歌為例,分享你在創作中感受最深的經歷?
小旭:我寫的第一首詩歌叫作《新生命》,沒有發表過。副歌是我在禱告時,連詞和着旋律唱出來的。那天我是經過特別深的一個掙扎、陷在對自己非常失望和厭惡的情緒里,但是禱告的時候神讓我看到我在祂眼裡的樣子,是一個已經被耶穌寶血更新了的人,是一個被聖靈主導的生命。
我就順着我的感動,一邊唱,一邊把歌詞在電腦上敲了下來。那首歌的創作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靈修和經歷神的過程,讓在禱告中我意識到神已經給了我新生命,所以我可以活出不再被罪拖累纏裹的生命來。縱然我還有軟弱,神看我在祂裡面仍然是“毫無瑕疵,全然美麗”,因為祂看到的不是我,是耶穌,而且祂是以發展、成長的眼光在看我。我真的感覺一下子就從試探和掙扎中被救拔出來了。
在團隊合作創作中,你們怎樣處理因為個人風格、偏好、意見等等的不同帶來的衝突?
陳明:通常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歌詞創作基本原則,譬如歌詞在神學上的嚴謹、傳遞的信息要明確、要有福音性,等等。如果在涉及這些原則的問題上爭論,以嚴肅、嚴謹的態度來把關,我認為是好的。但對這些原則之外的不同,我們需要保持忍耐和有彈性,最大限度地尊重個人風格與音樂曲風的偏好。
欒欣:按理說基督徒應該操練彼此順服,但做音樂這件事,很多時候是很難妥協的。比如在對編曲風格的意見差異太大的時候,是很難“彼此順服”的。所以我們的做法是反覆修改,盡量做到不同偏好的隊友都能滿意。曾經有一首歌我們寫過27個版本。
小旭:團隊合作也有它的好處。當我自己想不出好的旋律時,我會和我們團的成員一起jam(即興演奏和哼唱),尋找靈感,或者請團長崔宇幫忙操刀作曲。
常常有基督徒批評一些現代中文聖詩“聽起來像流行歌曲”,你們怎麼看? 你們如何看待詩歌創作中的傳統與創新?你們是如何改進自己的詩歌創作的?
崔宇:我其實鼓勵自己帶着開放和欣賞的心,去看待當今各種中文詩歌,即使它們很多聽起來和流行音樂很像。我不輕易否定它們。我覺得,這些聽起來像流行歌曲的詩歌,很可能是很多年輕及初信的基督徒在敬拜中成長的必要過程。這些流行歌曲可以用他們能夠最快接受的語言,來鼓勵他們的信仰。 。
曾經有屬靈長輩和我們分享說,跨代際服侍,本質上也是一種跨文化宣教。它要求你要用年輕一代熟悉的文化和語言,去服侍他們。如果你強行用你自己熟悉的文化和語言服侍他們,就會製造出“跨文化”的障礙。
當然,我們也不能單單停留在這種類型的中文詩歌中。敬拜音樂的內容和形式應當是豐富的,因為上帝的恩典和他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是豐富的。我們需要讓詩歌這種藝術形式儘可能地把這種豐富表達出來。音樂和詩歌是可以提供語言所不能提供的感染力的。我們既不能拋棄傳統,也需要創造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富有深刻內涵的中文詩歌。
陳明:我覺得需要把歌詞和曲調分開來看待。從歌詞來說,我個人認為目前在華人教會流行的一些中文詩歌歌詞確實比較單調重複、像是在套公式,而且神學用詞不夠嚴謹。
但從曲調上來看,歷史上的聖詩有不少是使用那個時代通俗歌曲的旋律,重新填詞成為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旋律,大都擁有好記、易學易唱的特點。個人認為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認為,歌詞在聖詩中的角色是主要的,歌詞的創作需要慎之又慎,甚至應當將歌詞創作看做預備一篇需要字字精雕細琢的講道。
欒欣:很多現代中文聖詩其實並不“像流行歌曲”。它們的問題是音樂風格單一乏味,曲調難聽,音樂水準比同時代的流行歌曲落後。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會哼兩句《奇異恩典》或是《普世歡騰》,那是因為當年的基督徒把詩歌做到了高水準,才能流行。所以我的盼望是:今天基督徒製作出的詩歌,音樂水準足以與同時代的流行音樂匹敵。
這需要既有創新,也有對傳統的繼承。我自己會嘗試不同的現代音樂的風格——可能第一首硬搖滾風格的中文詩歌和第一首金屬風格的中文詩歌都是我製作的。但我們寫的歌詞,跟以前的那些經典聖詩一樣,是在講述一個古舊的福音,這是繼承傳統。
沙龍:繼承傳統不等於就是照搬西方的基督教音樂。我們既然是用中文寫歌詞,也應該寫出中文獨有的美和韻味。我自己嘗試過採用一些類似唐詩宋詞的比較古雅的風格寫詞,我覺得現代的歌詞可以通俗易懂,也可以有一些陽春白雪,有一點文學上的美感的追求。
提高作曲的品質,需要加強專業性。我們做創作一段時間后,就能夠感受到我們在音樂方面的不足。我前段時間專門去認識了一些經驗豐富、專業從事音樂製作的高手,請教他們,也請他們幫忙為我們創作的歌曲配樂、潤色、錄製,做一些專業的處理,也給我們一些這方面的培訓。既然我們是有呼召來做,就要做得專業,盡量做出精品,不光是歌詞要好,音樂也要好,專業性也是呼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