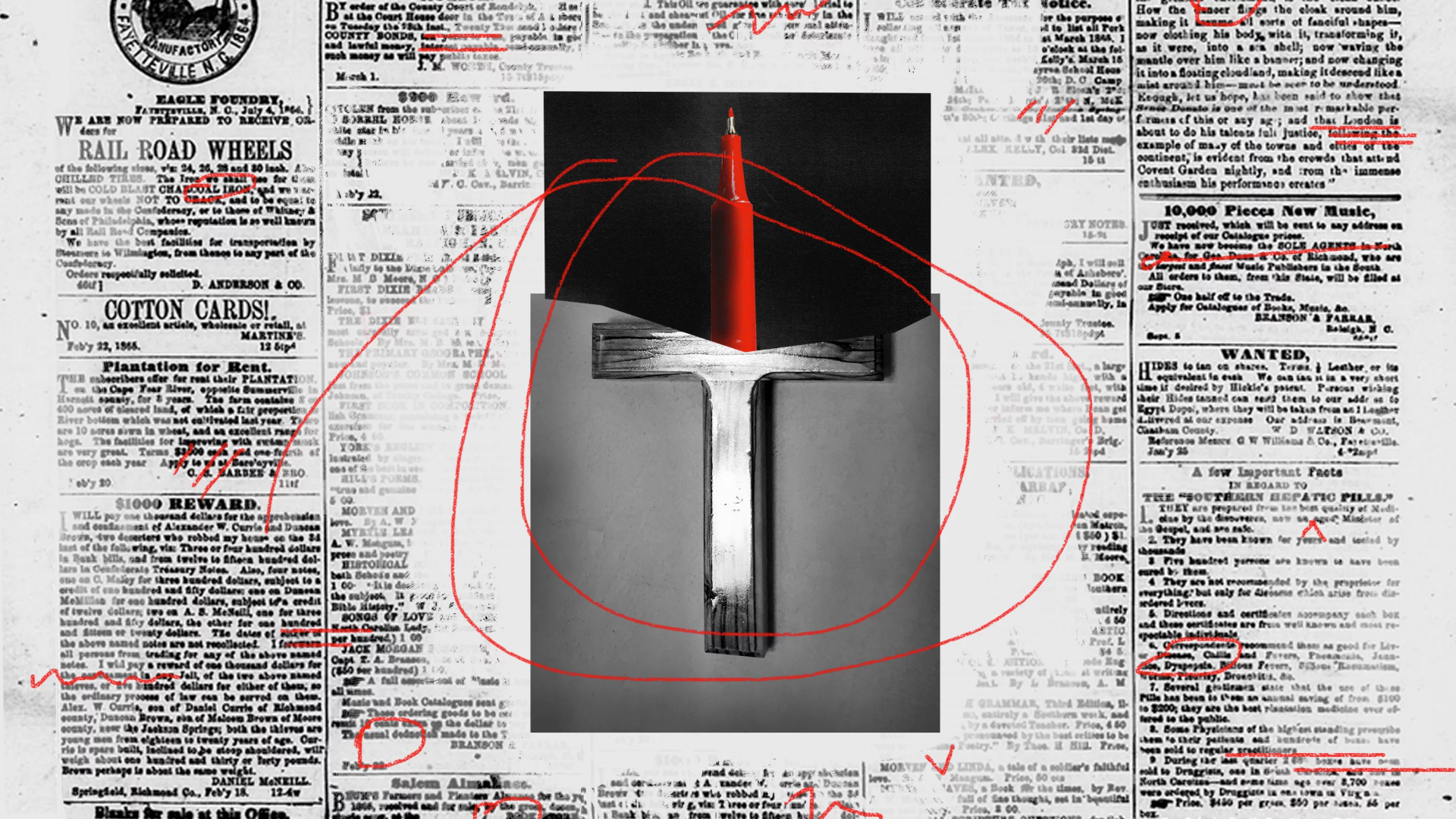在我居住的那條街的盡頭,就在我家外邊的幾碼處,飄來一縷催淚瓦斯。數以百計的示威者往相反方向逃去,極力尋找掩蔽——發生在街角的衝突,剛好在我的視線範圍以外。
眼前這一幕實在令人沮喪,但並不是催淚瓦斯令人感到意外。畢竟我所住的銅鑼灣區,已連續三個月發生多次警民衝突,眼中感到的刺灼亦早已習以為常。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眼前的一個人。
我立刻留意到他。他的衣著不像其他示威者,沒有戴著口罩,沒有拿著雨傘,也沒有任何裝備可以抵受化學物的衝擊。他一直站著,面向左閃右避的人群。大家正往另一邊逃跑,他卻站在原地。
最初我以為他正在堅定地參與非暴力抗爭行動;但我站著看他,留意到他口中唸諗有詞,他的頭也在左右轉動。他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憤怒;他是一臉關注,在向逃跑的示威者說話,但他不是在鼓勵他們堅守己見和反擊,而似乎是在關注這些人的身心狀況,想表達關心。他逆流而立,不計自己的安全,為要與人同在,令人安心。
他的姿態不見挑釁,只見同行。
我在旁觀看,聖靈在我心裏攪動。我在香港牧會已經20年,但這個人在這個時候所體現出的教會的力量,是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他就像迦勒和約書亞,雖然站在大多數持相反意見的探子面前,卻另有一個心志。我意識到──清楚意識到,原來我沒有這樣的心志。
香港教會正處於福音的拐點。除了全球的疫情之外,過去三年來,我在的這個城市見證了多次示威和政府恢復秩序的措施,這個城市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社會和政治動盪。很多人喜見街上回復平靜,卻也有很多人陷於傷痛和衝突之中。現在,教會必須決定怎樣回應。
未來數年,我們能否扎根福音的沃土,勇於釋出盼望、信心和基督徒的聲音?還是我們懦弱地退縮,隱藏在只顧自己、自我保護的陰影中?教會是否願意走進這個四分五裂的城巿,在最艱難的處境中牧養,與人同在?還是我們安於舒適的福音,只想教會大樓燈火通明,任由公共領域的先知之光晦暗熄滅?
香港本地教會社群那種不冷不熱的基督教信仰——只尋求上帝喜悅,但不願付上跟從耶穌的代價,已不再是個選項。或者這從來都不是選項。為了這個城市的教會的將來,必須放棄追求實用,轉而尋求嶄新的福音韌性,這份韌性是在社會劇變中熬煉出來的。我們需要牧者,像那位站在街角面對催淚瓦斯的人那樣,在令人困擾的政治環境中,帶來勇敢和與人同在的盼望。
陳韋安是願意順服這個呼召的牧者之一。他是八〇後,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德國研究巴特(Karl Barth),其後回港繼續牧養和教學的工作。他如今四十出頭,是個聰明、委身的人,能做深入的神學反思,又勇於將聖經與社會變化連繫起來,鼓勵人們處理他們的創傷經歷。他就如那位站在街角的人,在縷縷的催淚瓦斯中,帶來堅持同在的盼望。
“在我成長的時代,香港非常美好,”我和陳韋安喝著咖啡,他對我說。“那時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我們對未來充滿夢想,年輕人對這個城市有盼望、有期待。現在香港變了很多。”
他的牧養關懷集中在香港的初職信徒身上,這群職青還未踏進四十多歲名成利就的階段,卻又已脫離了二十歲以下相對青澀的狀態。“我這一代人,從小就比較專注賺錢,很多人都是政治中立的。如今的這一代,很多人都關心政治並會參與其中,這個轉變對教會而言是重要的,但也為教會帶來挑戰。”
這個轉變在2014年尤其明顯,當年發生的“佔領中環”,是首個政治性的學生抗議運動,其中的主要領袖也公開承認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身為學者的陳韋安,當時也留意到他的學生期望本地的基督教組織能給予指引。“我們的神學院要快速變陣,從教授政治神學,轉而教授政治倫理。突然之間,我們需要實踐多於理論。”
社會急速轉變,對於實踐的需要不單見於神學教育,也見於教會講壇。但從理論轉向實踐的改變卻來得很慢,許多牧者的裝備都不足以面對這個動盪的政治環境。陳韋安觀察到:“ 因為害怕被標籤為太政治化,只有很少牧者認為自己可以適切回應會眾所面對的重大議題。於是由那時開始,講壇漸漸與人失去連結。”
這種失聯的感覺,在2019年夏季再次變得明顯,大約就是催淚瓦斯飄過我的街角的時候。陳韋安說:“2019年的第二波學生運動出現,教會似乎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仍然重蹈覆轍。結果很多年輕人離開教會。他們不是離開耶穌,只是離開了教會。”
這批年輕人的離去,促使陳韋安建立了一間新教會──希望有足夠的彈性,容納新世代的基督徒,在追求耶穌的同時追求社會公義,並成為願意承擔的門徒,深化福音信仰。這間教會名為流堂(Flow Church),在幾年之間,人數已增長至超過4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職青信徒。
“流堂的出現,是因為香港基督徒面對獨特的挑戰,這個挑戰與西方教會的不同。”他說。“我們面對的不是政教關係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權力不對等和失衡的社會中生活。”
失衡的問題,不只是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陳韋安表示:“我們的處境獨特,正因為我們與祖國相連。”部分人對將來失去希望,也有愈來愈多人選擇移民離開。但對陳韋安而言,這句經文成為他更新牧養事工的根基:“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應許,耶穌來到,會使我們得著豐盛的生命。這個應許並不限於某個時空或生命的某個場景,無論香港的前景看起來有多艱難,我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得著生命的豐盛和喜樂。”
這個豐盛生命的異象,推動陳韋安的牧養事工。他和他的教會將要往下扎根於這個城巿,渴望在急速改變的環境中,堅持與弟兄姊妹同在,給予牧養關懷。這樣的工作需要不少勇氣、犧牲和力量。
同為在香港牧養的牧者,陳韋安的勇氣深深激勵了我。我不想只是站在遠處,旁觀別人展現他們的屬靈勇氣。我希望像他一樣心裏堅定,無懼眼中的灼痛,勇敢走進受傷的人群當中。
這樣的“另一個心志”——在迦勒、約書亞和我的朋友陳韋安身上所見到的——意思就是對上帝全心全意。這個心志也喚醒了我,使我看見自己的心原來已被許多恐懼、自我保護和制度的考慮撕開,失去方向。迎向這個新呼召,我需要一顆新的心,又或是一個新的皮袋,看看主會否許可。這總是聖靈工作的一步。
正如一位朋友最近所言:“最困難的呼召就是我們起初領受的呼召:向自己死。”就如街上的那個人,走進催淚瓦斯中予人安慰,願我們也能學效基督捨身,好讓他人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