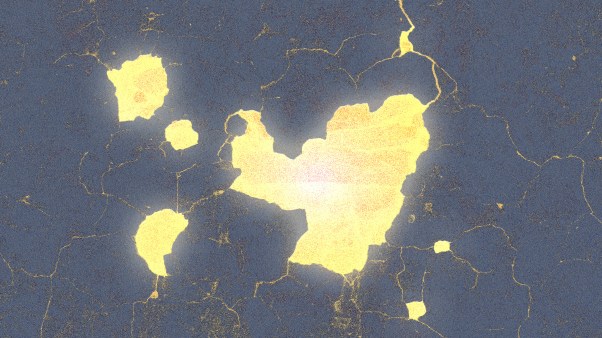一天清早,在我們全家的假期中,我的丈夫羅伯(Rob)離開了露營地,在瑞尼爾山國家公園(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人煙稀少處,展開長距離徒步旅行。當他和健行夥伴出發時,兩人對於前面的路程感到相當興奮,全身充滿著活力。他們都很喜歡徒步旅行,而且都是健行達人。
置身於戶外是羅伯重新得力、與上帝交通最喜歡的方式。但是,就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他的身體被一架直升機從曠野中運回登山口,冰冷、一點也沒有生命跡象。那一天,在家庭的日曆上,原本被標註爲全家旅行的大日子,如今成爲我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就在一瞬間,我的世界永遠改變了。死亡瞬間帶來的破壞力,仍然讓我驚慌失措,無力應變。羅伯的驟逝,讓我遭受失去親人的無情打擊,並陷入可怕的孤寂感。他悲劇式的突然離開,啃噬著我對未來的計劃,將我放在一條不想走的陌生道路上。
我的餘生勢必將與悲痛共存共生;我將沿着一條無人想走的小路走去。
在失去羅伯之前,我從不知深沈悲痛像什麼。我曾遭受其他的喪失,但沒有一次使我如此悲痛欲絕,也沒有一次會重新調整整個生命步調。我承認,從一開始,我就不願意走上這條陌生的傷心路。
丈夫留下四個孩子,由我獨自撫養,我沒有一刻不渴望回到以前的日子。羅伯與我一起度過 17 年不算完美但很美好的婚姻生活,我們一起過著非常滿意的生活,有著相同的熱愛和夢想。他全心愛著我,而我也愛慕他。
在這次悲傷之旅中,悲傷和痛苦召喚著我向前行,而我就像漢娜‧赫爾納德(Hannah Hurnard)經典著作《穩行高處》(Hinds’Feet on High Places)的主角 “驚恐小姐”(Much-Afraid)一樣,向著耶穌喊道:“我不能與悲傷和痛苦同行……我不能!我不能!哦,我的大牧者,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如何與它們一同旅行呢?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然而,我如今走到這裡了,我度過了自以為已死的那一刻。我已經可以擁抱憂患,把她當成我的夥伴一樣,雖然我每日都盼望她離我遠去。我活在羅伯已走的死蔭幽谷中,但我也決定將眼目跨過每天的黑暗,遠眺未來,朝向那應許著豐盛的地平線前進。我與自己立下誓願說:“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篇一一八 17)。
每當我思想並盤點羅伯死後所留下的東西,這清單就會拉得很長。他留下了朋友、同事,以及他努力奮鬥的工作;他留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一個非常愛他的大家庭;也留下我們的孩子和我自己,單獨在一條沒有他的道路上穩步踏行。
羅伯不幸死去,在壯年之際結束了生命,並在我們全家開花綻放的歲月中,帶來了死亡。我們的兒子們再也享受不到爸爸作他們教練的快樂了,再也不會在四健會(4-H)競賽或舞蹈演出會上,聽到他在觀眾席中爆出的熱烈歡呼聲。我們的退休和空巢築夢計畫,永遠不會實現了。
那年夏天,在他的追思禮拜結束後,我回到了家,心中滿是憂傷。我在淋浴間的架子上發現了一小塊愛爾蘭之春( Irish Spring) 香皂。這塊是我們度假打包上路時留在家中的香皂。它太小了,不值得帶去,如今,羅伯再也不會回來用它了。就連他留下的香皂都提醒我他不在了。
然而,這些損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爲羅伯也留下了文字遺產。羅伯是一位記者和作家,以寫作為生。他寫了關於商業和信仰、人道援助和財務的文章,還寫了有關死亡的文章,而這是他精緻細膩的意外的恩賜的證明。
在我們結婚初期,羅伯寫了一本書,書名為《死亡的藝術》(The Art of Dying)。他對新聞工作的好奇心及個人深厚的信仰,使他進入一家葬禮社工作。他加入了一個安寧醫護機構,並成爲一名志工,在週末探望疾病末期的病患。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羅伯發現,在過去 200 年中,死亡已不是公衆討論的議題。近年來,多數人在安養院或醫院內默默死去,而能夠給死者有很好照顧的家庭、社區和教會相當少。多數人都未準備好面對死亡,無論是面對自己的或所愛之人的死亡。
對多數人而言,在經歷到密友或家人死亡前,死亡只不過是電影和線上遊戲看到的螢幕上的死亡(圖像被分解成螢幕的像素,且在按下“關閉”按鈕就不見了),這些就是他們所知道的死亡。
當羅伯在葬儀社輪班工作時,他從諸多喪家中看到同樣狀況,他們全都沒有準備好面對死亡。因爲死亡被推到陰暗角落,被人遺忘,而憂傷也是如此。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很少有人會做點什麽。僱主要求失去親人的員工迅速返回工作崗位,社區和教會則繼續進行往常的計畫和事工。
羅伯發現,人們經常鼓勵悲痛者冷靜下來,繼續過以後的日子。他發現瀕臨死亡及憂傷之人,在一種根本不明白死亡的文化中掙扎著。
他有關死亡的文章深深地塑造了我們早期的婚姻。我編輯了《死亡的藝術》。在過去幾年裡,羅伯和我多次在夜間談論死亡。儘管我們當時仍年輕,但我們討論了生命結束時的選擇;我們大略列出所渴望的東西,並瞭解對方的願望。我們彙編了有關生命結束的文件,並買了人壽保險;我們努力成爲一對瞭解死亡的夫婦。
很多認識我們夫婦的人,都在問我,自己是否已準備好面對羅伯的死去。我總是這麼回答: “是的,但也不是”。儘管他的死亡來得如此突然,但我知道他想要什麼。因此,在他去世時,我只是盡我的能力實現他的願望。
是的,我已經準備好了。然而,你其實無法做任何事來預備好面對喪親之痛。
你可以閱讀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自傳,並聆聽他幾個小時的交響樂錄音,並通過類比方式來體會;您可以參加學術研討會,參與有關他的作品的討論;你可以知道有關他音樂的一切;但當你坐在鋼琴前,你的手指輕輕放在琴鍵上,你會發現自己竟不能演奏他的第 2 號鋼琴協奏曲,連一小節都不行。
即使用上你所有的知識,但你的大腦、心臟和每隻手指,都無法識譜。若要彈奏,您就得懂音符。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實際生活中操練。
我是這樣找到自己的悲傷之旅:在雜草堆中挑選;在森林中走出一條路;尋找引我朝正確方向前進的指標;並嘗試熟悉這陌生的憂患地形。憂傷一直都是一個痛苦難耐的教育,我必須在經歷的過程中學習,全程在摸索、顫慄中學習。
從我所見得知,我認爲一個人可以學得健康度過憂傷的技能。雖然每一次的失喪之痛都是獨特的,但我不認爲我們需要在悲傷的道路上,因盲目摸索而失足。悲傷帶來了深沉的黑暗,但我們可以學會前進的方式,使我們的痛苦更容易忍受。
作爲信徒的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面對死亡和悲傷。我們的生命是在我們的好牧者大能且溫柔的手中。雖然悲傷可能在我們一生中都與我們同行,但我們的救主也會陪伴我們同行。
嘉麗莎‧莫爾(Clarissa Moll)是一位獲獎作家、播客主持人,著有《衝破黑暗:給活在憂傷及走出喪親之痛者的溫柔指引》(Beyond the Darkness: A Gentle Guide for Living with Grief and Thriving after Loss)一書。
改編自嘉麗莎‧莫爾的著作《衝破黑暗》。版權 ©2022。經 Tyndale House Ministries 之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出版社同意刊登。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翻譯:榮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