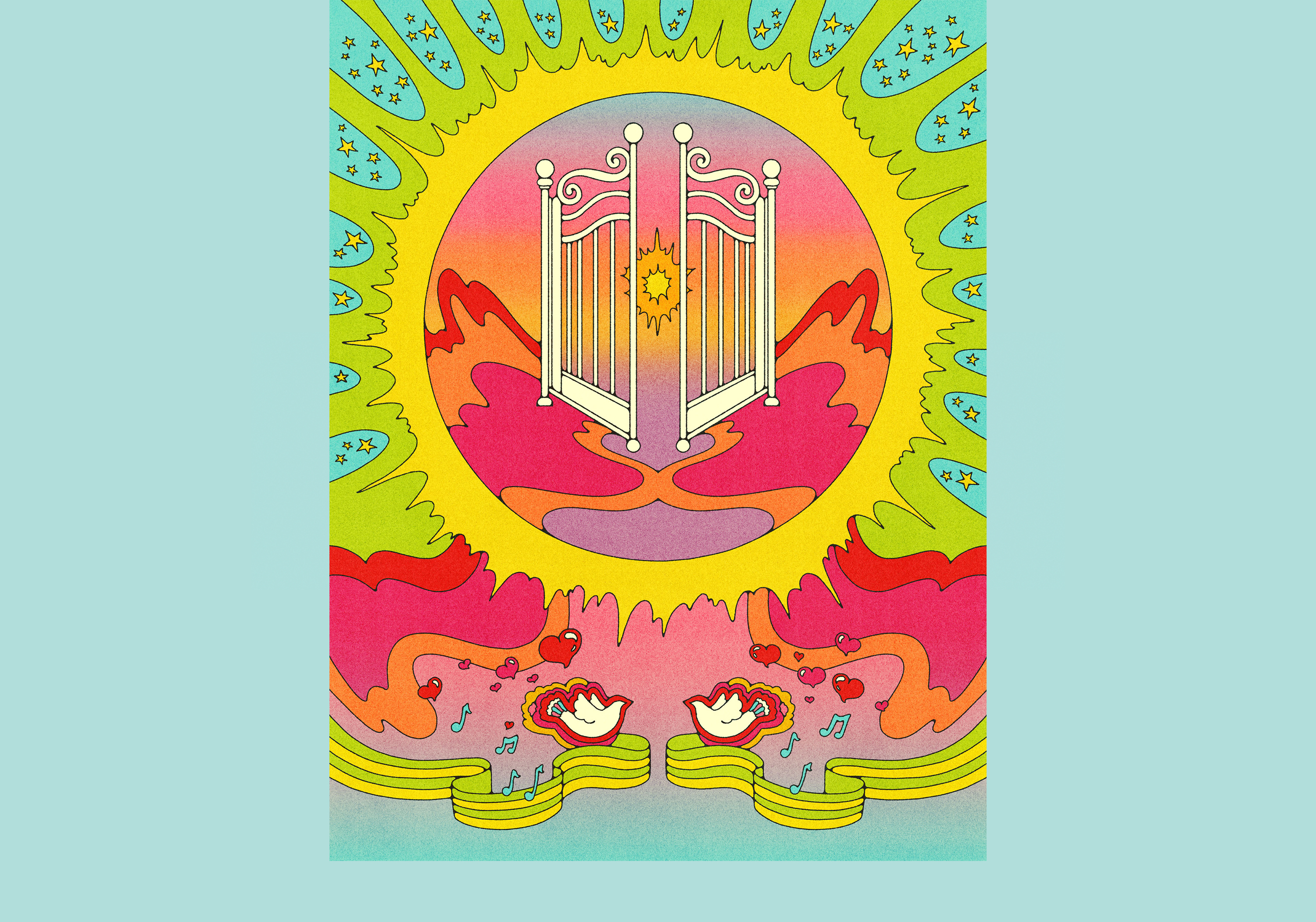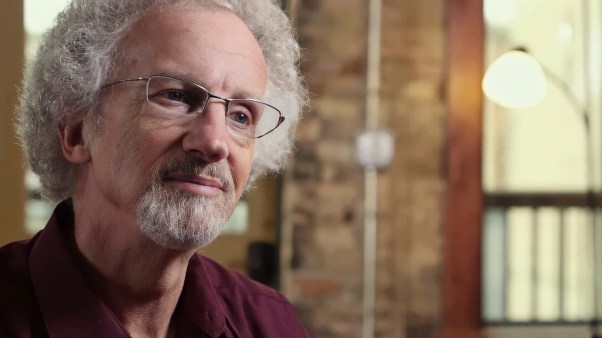當我還是個不可知論者時,我以自己擁有「開放的心態」為傲。
我傾聽各種靈性理論,涉獵了從佛教經典至加爾文主義宣言。我的研究真道之旅領我參與了俄羅斯正教的宴席,以及摩門教的歷史慶典。我在這些我不信其所指之神的諸般途徑中,都能找到值得欣賞之處。但有件事,當時的我卻如信奉教條般堅持:如果上帝存在,祂絕對不會認可當代基督教音樂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簡稱CCM)。
我其實說不清這種偏見從何而來。我平時對音樂並沒有強烈的意見。直到近期,我甚至也叫不出任何一首當代敬拜歌曲的歌名。原則上,我通常會為福音派辯護,反擊別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但身為一名歷史學家和記者,多年來,我聽過太多福音派基督徒自己對當代基督教音樂冷嘲熱諷,以至於對這類音樂的輕視,似乎成了一種人們可接受的偏見——甚至成了和「內行人」建立連結的方法。
2008年某個週末,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參加位於芝加哥西北方、以「慕道友友善」著稱的巨型教會——柳溪社區教會 (Willow Creek) 舉辦的研討會。早上,剛結束關於巨型教會門徒訓練未來方向的討論,燈光便暗了下來,舞台上方的螢幕開始閃現歌詞,貝斯手撥出第一段和弦。我記得自己坐在會堂後排,在震耳欲聾的黑暗中瞇著眼看筆記,心想:在教會裡辦搖滾音樂會,肯定是不對的。在我心靈深處的某個角落,我其實覺得旋律有點好聽,但這反而更加深了我的不以為然。
和多數不信主的人一樣,當時的我對「神聖」與「世俗」之間的界線,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想法。但我卻極其篤定:用好幾把吉他、電子琴和鼓組唱關於耶穌的歌,是十分褻瀆的事,更不用說會眾最後那粗俗的掌聲了。在我那時緩慢蹣跚的靈性探索旅程中,我從未讀過《詩篇》,因此完全不知道《詩篇》確實如此要求敬拜者:「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詩篇47:1)
然而,距離我在芝加哥郊區第一次聽見那「神聖的雜音」後約14年,上帝終於使我成爲一名基督徒。令我意外的是,祂選擇在一間巨型教會裡成就此事——而且並非「儘管」背景裡有著當代敬拜音樂,而是「正是」那些簡單的歌詞與洗腦的旋律,大大助攻了一把。我為自己過去的高傲態度悔改,並且如今能在更寬廣的視角下看待這些音樂和我自己的反應。
今日圍繞著當代敬拜音樂的爭論,其實是歷代以來屢見不鮮的辯論的最新一章:我們究竟如何在保持福音完整性的同時,觸及到所處的文化?我們又該如何設計一場既能牧養基督徒、又能吸引未信者的敬拜?我在摸索的過程中學到一件事:我們對某件事物的「本能排斥」,也許正是上帝要用來使我們謙卑的路徑。
但基督信仰所傳遞的信息,對這個世界而言本就是陌生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
基督的道德要求,在不同年代都以不同方式刺痛各種社會;但就本質而言,基督徒堅信: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恩典,並且永遠無法靠自己賺得恩典;這個信息對人類驕傲的心而言,永遠是極其冒犯的。更甚者,基督徒還宣稱:在這個充滿邪惡與苦難的世界裡,上帝的愛仍能合理地存在,並且兩千年前,這一切苦難在一位被釘在羅馬酷刑器具上的人的死亡裡,永遠地解決了。
保羅稱這一切信息為「絆腳石」。他花了整個宣教人生努力使這個信息更容易被人理解及接受。這意味著他得不斷進行「文化翻譯」的嘗試——他稱此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前提是不能因此粉飾基督信仰中最「怪異」的主張 (林前9:22)。廣義來說,今日的當代敬拜音樂,是兩千年來無數傳道人與藝術家努力效法保羅,以音樂吸引慕道者、門訓基督徒、和敬拜上帝的傳承。
美國第二次靈命大覺醒時期的聖詩作者曾借用小提琴舞曲、吉格舞曲、里爾舞曲,以及其他世俗領域的旋律。歷代以來,試圖把世俗音樂改編為教會使用的基督徒,並非每次都能成功,而且總是會惹惱、冒犯其他基督徒。五十年前,諾曼 (Larry Norman) 與其他耶穌子民運動 (Jesus People) 的人,將搖滾、福音、民謠與傳統聖詩混合,再配上涉及「情人節淋病」之類不太雅觀題材的歌詞。基督教書店店主對是否上架他的專輯猶疑不決,甚至把唱片藏在庫房或櫃檯底下,「怕有人走進來指責他們賣這種東西」。
雖然一些基督徒至今仍擔心搖滾樂被性與毒品玷污,但到了1990年代,最受歡迎的敬拜樂團與基督教流行歌手,已不再主要迎合叛逆青少年的口味,而是主攻那些想讓孩子遠離MTV的富裕郊區媽媽們。
也因此,今日的評論家們更常哀嘆敬拜音樂的「乏味」,而非「低俗」。在一則名為「為什麼現代主流基督教音樂這麼無聊?」的討論串中,一位留言者寫道:「所有歌聽起來都一樣,不斷重複一樣的和弦及聲線」。一位名叫約書亞 (Joshua Sharp) 的牧師則在Baptist Standard討論版上抱怨:「多數現代敬拜歌的歌詞,只是成功神學加上廉價的心靈雞湯。」
美國巨型教會敬拜事工的「四巨頭」:伯特利音樂、Elevation、Hillsong、以及Passion Music,以環境系流行搖滾的聲響,主導了整個當代敬拜音樂產業。我ㄧ位不可知論者朋友對這現象的總結是:「就只是對U2樂團的拙劣模仿。」與雷鬼或福音音樂不同,這類型的主流詩歌沒有任何鮮明的音樂特徵。西敏寺神學院教授兼牧師克拉克 ( R. Scott Clark) 甚至寫道,這類音樂「在美學上和真理教導上都很空洞⋯⋯多數當代敬拜音樂的主要功能,就是產生一種輕微的陶醉感。」
只不過,正是這「輕微的陶醉感」幫助了我歸信基督。
誠然,這些歌的歌詞很簡單。但除非你盯著投影幕上的字體時,從未認真思考那些文字所表達的思想,否則,說它們都很「空洞」並不公平。當然,如果深思過後,發現你教會敬拜時的歌詞確實很空洞且毫無實際的神學意義,請儘速逃往離你家最近的一場會合唱古典聖詩的禮拜堂。
真正定義當代敬拜音樂風格的,其實是一種「不協和感」:平滑的和聲、簡單的歌詞,以及當你稍作停頓去思考歌詞意義時,所感受到的衝擊反差。
想ㄧ想伯特利音樂2019年的熱門歌曲,〈神的良善榮美〉(Goodness of God) 開頭的幾句歌詞:
I love you, Lord (主,我深愛祢)
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祢的憐憫永不改變)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每一天,祢的恩手扶持我)
這19個字每一句都大膽到令人咋舌:一位全能的上帝認識並關心每一個人,知道我們生命中的每個細節;祂不只愛我們,甚至為渺小的人類開啟一條能夠回應祂的愛的道路。
的確,這是幼兒園程度的基督教神學;但耶穌告訴我們,要像小孩子一樣來到祂面前。如果我們緊抓著這個世界「成年人的」公平觀及權力觀,或以成年人的「常識」來定義上帝應該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樣的作為,我們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祂。
敬拜中那份「輕微的陶醉感」——社會學家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形容為「集體亢奮」(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的狀態——有時確實可能只是類似異教徒的搖滾演唱會快感。然而,對許多人而言,這種感官經驗與易唱旋律,就像父母的手輕輕按在幼兒背上,引導我們走向聖經所說的「敬畏耶和華」之心。這通常不是什麼神學上的突破,也不是神祕經驗,更像是羞怯而側面的瞥見救主榮面——瞥見那位面容「如同烈日放光」的救主 (啟1:16)。而對多數人來說,如此一瞥,已是我們所能承受的最大程度。
一段容易記住的旋律,加上一條在胸腔震動的低音頻,往往能瓦解我們的防備。它們能打開心靈的眼睛,使人看見基督教基本信條中那幅極度違反直覺的永恆圖景。這些音樂會卡在我們腦中,整天持續在我們裡面運作。最近剛在麥克萊恩聖經教會信主的布萊恩 (Bryan O’Keefe) 告訴我:「當我聆聽這些歌的時候,我開始把歌詞跟自己的人生經驗連在一起,然後它們開始讓我感覺自己被帶進一個更龐大的事物裡。」
敬拜音樂理當同時是「安慰的食物」,也是「苦澀的良藥」。至於什麼樣的內容才能安慰人心、或震撼人的味蕾,則取決於個人品味與文化處境。這或許正是為什麼上帝安排——或至少允許——現代教會呈現如此驚人的多樣性 (學者估計,全世界基督徒分屬近五萬個宗派、信仰傳統或教會聯會)。畢竟,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刺棒」來推動。
我認識一些在偏浸信會、無宗派背景教會長大的基督徒,後來走向聖公會、天主教或東正教傳統,因為古老禮儀的文字與節奏能將他們從21世紀的美國泡泡中抽離,幫助他們重新找回那能傳遍全球的福音的奧祕。然而,就我個人而言,我卻需要走在反方向的靈性之旅上。
是中世紀的合唱編曲與縈繞的香煙,引領我踏入最初的信仰探索。我長大的過程沒有任何宗教背景及經驗。大學期間,我因著對俄羅斯文化、語言及神祕主義的興趣而開始研究東正教。在研究所期間,教會歷史課又把我帶進學校附近的英國天主教教會。
我愛上了這些傳統——至今仍深愛它們——正因它們那種毫不掩飾的「奇異感」。我渴望一個與現代美國科技加持下的極致個人主義徹底不同、讓人感覺彷彿置身他鄉的空間。那些致力保存古老形式、對過去一世紀的流行歌渾然無感的東正教及英國天主教教會,正提供了像這樣的空間。
問題在於,對我這種不可知論者、熱愛教會史的書呆子而言,一個充滿雕刻物、苦像與彩繪玻璃,以及繁複禮儀的空間,給了我無限分心的契機,神遊四海地想著許多與耶穌無關的事。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向牧師讚嘆,去教會讓我感覺自己與西方文明連結更深了 (他人非常好地沒有責備我)。當然,我如今也並非想跟16世紀的「破像派人士」ㄧ樣抨擊這類教會禮儀傳統 (雖然我完全能理解慈運理的立場);我想指出的,只是我個人那點不甚高明的驕氣、個性,以及人類喜歡逃避艱難事物的傾向。
我曾連續聆聽俄羅斯修道院聖歌的CD好幾個小時,一心想著破解古教會斯拉夫語(我修過一學期),以至於我從未真正面對那些修士所讚美、所懇求憐憫的那位上帝。主日崇拜時,我坐在後排,心裡想著我有多喜歡在〈公禱書〉的悔罪文裡承認及哀嘆自己多重的罪與惡;甚至在成為有神論者之前,我就覺得「原罪」這個教義很有道理。然而,我的心思更常飄向的,是這些優美詞句的文學光彩,而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或明白是因著祂的受死,全然敗壞的人類得以有膽乞求赦免,甚至大膽地相信自己真能蒙赦免。
後來,我漸漸不再去那間英國天主教教會。對我而言,相信上帝仍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命題,更不用說理解何謂道成肉身了。我很感激那些沒有追問、也不強拉我去團契茶點時間的基督徒。但也許,是時候承認我是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形容自己時所說的,是個「在宗教上沒有音感的人」的人;韋伯一生研究各種世界宗教,卻從未宣稱相信任何一種。
博士畢業後,我又花了十多年讀書、查閱檔案、訪問基督徒、授課,做著所有讓我成為「美國基督教專家」的事情。我並不喜歡身為一名不可知論者,但我接受了自己的狀況,畢竟我已找遍所有「宗教醫生」——至少是那些有聲望的醫生——卻沒有一個能治好我。
我的故事雖然獨特,但我想說的道理卻非常普遍:人很容易欺騙自己,以為自己已經「弄懂」基督信仰,實際上卻只是把基督教的上帝改造成符合自己喜好的神明。
直到大約三年前,上帝伏擊了我。
當時我正在為一本雜誌撰寫一間位於羅利的美南浸信會巨型教會,頂峰教會 (The Summit Church) 的專題報導。他們的牧師葛瑞爾 (J. D. Greear) 把我們第一次的訪談變成了一場不斷延伸的對話。他逼著我意識到,我需要真正檢視基督教對人類歷史所提出的主張 (而且已有許多書籍精細地處理了這些問題)。我本該多年前就讀這些書,甚至需要讀它們的每一則註腳;若不是這些研究,我不可能走到這一步——承認新約文獻是可信的史料、並且「耶穌復活了」是對一連串令人費解的歷史現象的最可能的解釋。
然而,在我艱辛地啃著賴特 ( N. T. Wright) 的《神兒子的復活》等書時,我也持續參加頂峰教會的主日禮拜。每個週末,我坐在禮堂後方最上層、柔軟有靠墊的座位上,盯著巨型螢幕上的歌詞。我甚至會開口唱,因為周圍又黑又吵,沒人能看見或聽到我的歌聲。沒錯,那感覺就像在演唱會上——但對我而言,這個演唱會除掉了那些我曾在教會裡把它們變成偶像及藉口的東西。
漸漸地,我開始意識到,唱著「我們透過血、藉著父神得救贖」一點也不俗氣。而Charity Gayle的〈Thank You Jesus for the Blood〉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盤據著我的腦袋,也並不只是因為旋律好聽。
是的,人們對當代敬拜音樂的某些刻板印象,確實說中了要害。有不少歌曲把上帝的得勝與祂對子民的看顧當作主要主題,而較少著墨於罪與受苦。例如Tauren Wells在2020年的作品寫道:「在水中為我開路/帶領我穿越火焰/成就祢所聞名之事」;或如Passion Music這首歌的歌詞:「沒有任何事是我們的神不能做的/沒有祂不能挪開的高山。」
敬拜事工四巨頭裡,有三個偏向靈恩傳統,而雖然Passion City教會屬於較廣義的改革宗,但靈恩及改革宗傳統兩者皆強調基督復活所帶來的「那改變生命的大能」;當然,這確實也是新約的重要主題之ㄧ,尤其在保羅書信中。
如果公共敬拜的目的,是當日常生活把我們往反方向拉扯時,將我們重新牽引回敬拜造物主的姿態裡,那麼,唱ㄧ些能提醒我們基督在永恆裡勝利的詩歌——終有一天,祂將除去世上一切痛苦——就完全說得通,即便我們現在仍身處苦難之中。正如Vertical Worship的〈Yes I Will〉副歌所唱:「是的,我要在最低的山谷高舉祢。」
而有些當代敬拜音樂旨在培養「特定的屬靈經驗」:某種與上帝親密連結的感受——也就是批評者嘲笑為「耶穌是我男友」類型的歌。這類歌曲若沒有全面的聖經教導作爲基礎,的確可能助長一種膚淺的情緒狀態,比起順服基督,更像國中生的荷爾蒙波動。但即便在這種狀態中,同樣也可能有更深層的事正在發生。音樂人Melanie Penn曾告訴我,她認為自己像某種「心臟醫生」,打通人們頭腦與心之間的動脈。
例如Maverick City在〈Communion〉裡唱道:「祢比我的皮膚更貼近我/祢在我呼吸的空氣裡……這就是我應在之處 (就在這裡) /我在祢裡面,祢在我裡面」。歌詞裡的意象與聖經作者們相當一致:他們常用婚姻與愛情的比喻,幫助有限的人理解上帝盟約之愛的深度。在中世紀,《雅歌》甚至是修士們最喜歡書寫的經文之一,但不是因為他們是太過壓抑的獨身者,而是因為他們真正理解因基督的犧牲所成就的神聖親密感,是何等驚人。
說到底,沒有任何一種敬拜音樂應成為一個人靈命塑造的唯一來源 (無論是電子風還是葛利果聖歌) 。基督徒的神學飲食,應該像攝取熱量那樣,均衡、多元,並由懂得「屬靈營養」的專家把關。講道、禱告、查經與其他屬靈書籍的閱讀,應補足敬拜時較少觸及的主題。而我們這些普通會眾也應能信任牧者會仔細審視敬拜歌詞中的神學。
在網路上那些反對當代基督教音樂的圈子裡,批評者常抱怨流行敬拜歌曲背後的事工充滿爭議的神學及行為,例如伯特利教會激進的靈恩教導、Elevation教會帶有成功神學 (昌盛福音) 的味道、或Hillsong爆出的性醜聞與財務管理問題。
然而,這些團隊為大眾創作的歌曲,通常會避開神學上的差異之處,專注於「純粹的基督信仰」核心。而藝術家或牧者個人的失敗,也不會減損歌詞本身的神學正統性。憤世嫉俗的人會說,這些人之所以緊抓關於「白白得來的恩典」與「上帝主權」等基本教義,只是為了觸及並在全球最多類型的教會中賣出更多專輯。但我心中不那麼憤世嫉俗的部分,則感謝上帝讓我每週都能再次被提醒福音最基本卻最核心的真理;而歸信基督信仰本身,也要求我們脫離盛行於世俗文化的憤世忌俗姿態。文化與政治的潮流不斷將基督徒彼此拉遠,逼我們為次要議題吵架。當代敬拜歌曲能把我們帶回耶穌面前。
我如今在每個主日都滿懷感恩地唱著這些歌。我會在車上把音響聲開到最大,吵得全家受不了。而如果有一天,這些歌不再使我產生敬畏之心,我也會毫不猶豫地翻出我的俄羅斯東正教聖歌CD和《公禱書》。畢竟,要帶領及門訓像我這樣的罪人,需要整個教會的力量。
Molly Worthen是歷史學家、記者與教授。她最近的著作是《施咒:魅力如何從清教徒時代到川普時代形塑美國歷史》(Spellbound: How Charisma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Puritans to Donald 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