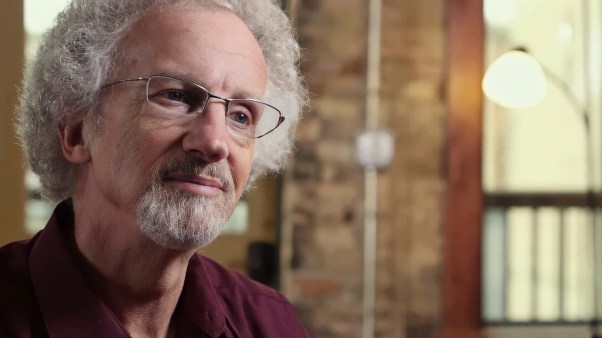幾週前,在某個如今已記不清原因的爭吵過後的早晨,我和大女兒坐在車子裡,緊繃的沉默仍盤旋在我們中間。「我昨晚的反應不是很恰當,對不起,」我說。「這是妳第一次當一個14歲的女孩,也是我第一次當一名14歲女孩的媽媽。我承認有些時候,我真的搞砸了。過去這麼多年,我已習慣幫妳安排好一切,如今我需要不斷提醒自己,是時候學習如何放手了。」
隨著我們之間的張力逐漸消散,我彷彿瞥見那個曾讓我頭痛、會把被捏爛的葡萄從兒童餐椅上往外丟的小女孩。那個小女孩消失得多快啊!一轉眼,在我面前的,是ㄧ位我既熟悉又難以完全理解的年輕女子。我心想,她不是我可以掌控的人——這是件好事。她被造的目的,本就遠遠超過我所能控制。
但像這樣乍現的領悟——這種安穩地信靠上帝對她和我預備的計畫及供應的心境——並不是我平常能長久停留的狀態,即便我多麼渴望自己總能如此。對我來說,組織一切、安排生活是我的天性。我總覺得可以再更努力點、準備得更周全一些、多擔心一點;我總感覺,這樣做能帶給我所渴望的踏實感和安全感。
當然,我也明白這種習慣背後隱含的罪性。我知道父母的焦慮、試圖控制那些無法控制的事,正是促成今日兒童焦慮症氾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已有各種研究佐證)。但每ㄧ天,我就像使徒保羅說的那樣,總做著我不想做的事 (羅 7:15)。我勤懇地管理、督促、建議、設計、解決——努力為那些我以為只有我能看見的「最佳結果」鋪路。
但上帝的視野比我們看得更遠、更廣。我偶爾會想起這個真理。
這正是牧師兼靈修導師卡拉 (Kara Root) 在她與丈夫路恩哲 (Andrew Root) 合著的新書《放手之聖旅:幫助父母與牧者擁抱關係中的不可受控》所傳遞的核心信息之一。
以下為本刊與夫妻倆的採訪,本訪談紀錄經編輯與刪減。
我很興奮能讀到你們的新書。因為我既在教會工作、同時也是幾個青少女的母親。我覺得這本書非常值得討論。書中不但深入探討聖卡斯伯特 (Saint Cuthbert) 的一生,也記錄了你們一家人橫跨蘇格蘭與英格蘭、旅行了63英里的朝聖之旅。但我最喜歡的部分,是你們對現代父母及牧者面臨的一大挑戰所做的診斷:我們的焦慮如何驅使我們更用力地抓緊對所愛之人的控制。
你指出了我們每個人都正在經歷的其中一種焦慮面向——但對你來說,你認為現代人為何特別容易把「控制」當作面對生命的「不可預測性」的解決方式?
要簡短回答這題真的很難,畢竟我在書裡花了一大篇幅來討論!但我想,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往往視「控制」為唯一的工具。在生活中許多地方,我們都被教導要靠自己「控制」局面來解決問題——尤其在社群媒體上。舉例來說,我們家養了一隻小狗,我只是查了一下某個與狗有關的小事,演算法便開始推播我一堆「如何訓練你的狗、如何安撫你的狗、如何控制牠的各種行為」等影片和貼文。只要稍微有點疑惑,我們就容易掉進無止境的兔子洞,試著修補我們認為有問題的一切。也許,若我們感覺自己「有能力掌控或修補好一切事」,便能對自己的存在感到安全。
而如今世界的一切運轉得越來越快——我們被驅使著要讓自己更大、更好、更強——身為父母的我們,內心也承受著這種壓力。我們不斷抓取各種資源,覺得自己只要有足夠的知識、足夠的能力、足夠的自信、或足夠的「某種東西」,我們就能掌控局面,避開那些讓我們害怕的東西:害怕自己是失敗的父母。但這世上並沒有一個提醒我們的號誌,讓我們停下來告訴自己:夠了,我已經做夠了。或,我現在已經算是一個好父母了。我們總是不斷回頭檢視自己哪裡做得不夠。
我就讀大三的兒子今年剛離家,去蘇格蘭交換留學。我明明知道他有能力做到這件事,然而,我人在另一個國家,卻還是為他列出注意清單,甚至半夜醒來傳訊息問他:「那邊一切還好嗎?行李收得怎樣?」我其實不需要這樣做——但焦慮就是推著我前進。從某個角度說,我們確實已經在放手了:我們讓他自己摸索交換留學的程序、自己上飛機、自己在國外生活。但在內心深處,我仍緊抓著控制權不放。這似乎是一場永無盡頭的掙扎。
就好像我以為,只要我能掌控一切,就能避免壞事發生,或確保未來一切美好。然而事實是,我們對任何事都沒有真正的掌控權——但我們確實被一位慈愛的上帝看顧,所以即使事情出了差錯,也不代表一切就此結束。
你認為基督徒在這方面 (渴望控制) 與我們的世俗鄰舍有什麼不同嗎?換句話說,當面對不可預測的情況時,一個普通美國基督徒的反應方式,會更像他不信神的世俗美國鄰居,還是更像非洲的基督徒弟兄姊妹?
容我過於大膽的這樣講:我認為美國基督徒的反應,會更像我們的世俗鄰居。因為我們所處的文化、我們所呼吸的空氣,都充滿了對大小事物的控制慾,以及對微小事情的焦慮。
我現在人在哥本哈根。我們下午四點開車進市區時,看到所有人都坐在河岸和公園裡——因為這是他們下班的時間。人們下班後會和鄰居、同事、朋友一起坐著閒聊、放鬆。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這雖然不是非洲的弟兄姊妹,而是丹麥的弟兄姊妹,但很有意思的是,他們在一個重視彼此連結、歸屬與共處的文化中長大,將一起欣賞日落當作一件重要的事。而對我們美國人而言,如果花時間做這些事,會感覺自己的人生好像落後了——我們會輸給大家。再者,當我們趕著送孩子去踢足球、拉小提琴、參加青少契聚會等一堆安排的時候,哪還有時間看日落?
我也同意你的觀察,但這也讓我想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文化對我們生命的塑造力,竟遠超過信仰與聖靈工作的力量?
我想,部分原因與我們的「美國例外論」有關——就是那種「有些事情不會、也不應該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想法。我們 (身處較豐足國家的人) 有更多資源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來讓自己感到安全。因此我們更容易活在對生命脆弱性的否認心態中。有趣的是,當我們的生活或社會開始崩塌的時候,我們反而會比別人感到更深層的存在焦慮。
我有一位朋友在教移民英文,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她說這些人雖然客觀上承受更高的風險,卻往往顯得不那麼的焦慮。有許多人經歷過極其艱難的事,但他們知道自己必須在困境中繼續生活下去,並且人生也不只有那些可怕的事,我們仍有我們所愛的人,仍有彼此共享的時刻。
但作為美國人,我認為我們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仰賴那些我們自己建立的、或被賦予的外在結構,而教會也常不自覺做著同樣的事。許多人想去一間「看起來成功」且「忙碌不已」的教會——甚至忙到連自己都做不完教會安排的所有活動。
同時,當我們沒做到我們認為自己應該做到的事時,內心也會浮現一種奇特的羞愧感:我應該多讀點書。我應該再學一門語言。我應該學習投資。總之,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
但這種荒謬的壓力其實是我們加在自己身上、再把它帶進教會的。最終,我們把信仰簡化成一種將人生「最佳化」的工具。我們盤算著:有上帝站在我們這邊,我們能把人生最佳化到什麼程度?或是,基督信仰能不能給我們更好的工具,去完成我們本來就想做的事?但事實上,基督信仰訴說的故事完全不是這回事。人生的重點與我們以為的不一樣——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麼,這對「信仰的塑造力」與「聖靈的工作」而言,又意味著什麼?我在教會服事,知道我們最真誠的心意是愛每一個人,帶領人們在基督的真道上更深地扎根。教會的各種事工也都以這個目標而努力。然而,我們似乎往往被帶往另一個方向。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想,部分的問題出在那種「我們能領人與耶穌建立更深的關係」的想法上。這種想法其實把責任與主動權放在自己身上,讓我們自以為能控制這些事。
我是個牧師,在我的教會裡,我們逐漸形成這樣一種核心信念及對上帝的信任:我們早已屬於上帝,也屬於彼此——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宇宙根本真理,但我們卻常常忽略它、抗拒它。
在耶穌基督裡,我們已經與上帝、與彼此和好。因此,這意味著與我們同行的人,是弟兄姊妹,而不是競爭對手。他們不是我們要去達成「轉化目標」的對象,而是與我們同行,「一起」活在上帝所愛的世界裡的人。
如果我們能真正把自己降伏在這個真理之下,真正按這個真理來生活——如果我們相信上帝「已經」在我們與他人的生命當中工作——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帶著這樣的期待而活,時常問自己:上帝今天要做些什麼?祂會在這裡成就些什麼? 我們的人生將會非常不一樣。
這種想法和原先把壓力全放在自己身上截然不同。難道讓人對基督的工作敞開,完全是我的責任嗎?難道確保孩童事工、講道或其他活動產生改變人心的果效,全是我的責任嗎?非也,那是聖靈的工作。這種認為自己或教會能掌控結果的想法,放在教會歷史長河中來看,其實非常荒謬好笑。
教會已經經歷過如此多風浪,在我們生命結束後,教會仍會繼續存在。我們只是在此刻暫時領受、觀看,並參與在上帝正在做的事之中。但若我們一味專注於「讓什麼事發生」,我們就可能錯過了上帝此時此地正在做的事。
回到更具體的教養議題上:不論是養育孩子,或在地方教會服事,其實多半是平凡而重複的工作,而非突發的、充滿靈性高光的時刻。我知道我們無法刻意製造那樣的瞬間,但你在書中提到,我們仍然可以「尋求」那種你們稱之為「共鳴時刻」的時刻:預備好桌子、培養一種敞開的姿態,讓自己有可能與超越我們自身的那位相遇。
我非常喜歡這個觀點,也確實經歷過那樣的時刻。然而,當生活枯燥、疲乏、毫無亮點時,要如何每天實際地活出這樣的生命姿態?那種能發揮「靈魂塑造力」的操練是否仍有其效力?
我覺得這類經驗往往發生在我們沒有特意尋求的時刻與地方。也許只是很平凡的一個星期四,當每分每秒都令人感到煎熬——也許孩子們正在後座,為著要放哪首歌而吵架的時刻。可是,養育孩子的時光轉瞬即逝。有時候,我在他們拌嘴的那一刻突然意識到:我竟然有幸能成為他們的母親。我們無法刻意製造屬靈高峰的時刻,但我們可以操練讓自己活在當下。我們可以在一天結束時,練習回顧這一整天:有哪些時刻我可能錯過了?明天我可以更敞開自己迎接什麼?
我記得女兒準備上幼稚園時,非常的興奮。她哥哥已經上學兩年了,她則早在七月就挑好開學要穿的衣服。但是,當她真正跨進教室的那一刻,她整個崩潰了。太多孩子、場面太混亂、太多壓力,讓她不知所措。我怎麼安撫都無法辦法讓她平靜下來。
我把她帶到走廊上,試著用各種方式「改變」她、控制她。但不管我做什麼都沒有效,我無法真正在那個時刻與她同在。最後,在完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並不是出於什麼偉大的信心——我半跪下來,看著她的小臉,說:「梅西,今天上帝為你預備了一個驚喜唷!」
她愣了一下,停止哭泣,眼睛睜得大大的,說:「真的嗎?」我告訴她是真的,並且說等我來接她時,我想聽她分享上帝給她的驚喜是什麼。
當我走出學校時心裡想著,好吧,上帝,祢最好親自出馬了。我剛剛才跟她說祢會在學校陪她。整整一天我都在禱告、緊張不已。但當我去接她時,她興奮地跑過來說:「媽媽,你說得沒錯。上帝真的給了我一個驚喜!」我已經不記得那個驚喜是什麼了,但這從此成了我們每天的小儀式:一起聊上帝今天給我們的驚喜。
而那些驚喜總是平凡的事。就是日常的生活。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明白,我們永遠可以在每個當下期待感受到基督的同在。上帝既然應許要餵養我,就真的會餵養我;但我們需要操練自己、也幫助彼此學會察覺這些恩典禮物。這關乎我們是否真的「屬於上帝、也屬於彼此」。上帝每天都想賜下禮物及照顧我們,而我們也彼此相屬。我常在與人彼此的關心中經歷到上帝的同在。
所以,當我們不再問:「我現在該怎麼做才能讓一切正常運作」時,也許我們就能注意到上帝在那一刻的同在。
是的。若我們相信上帝是真實存在的神,我們就能做到。但我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如此相信。我其實覺得這是今日教會最大的問題之一。我們口頭上相信上帝真實存在,也真心希望是這樣,並決心根據這個信念而活。但在實際生活裡,我們並沒有活得像上帝是真實存在的神——我們活得像一切都得靠自己。
若我們「真的」相信有一位真實活著的上帝——相信祂會親自動工,而且祂已經在動工了——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身為一名有兩位青少女的母親,我最近常覺得家庭衝突變得太過日常且頻繁,我很欣賞你在書中提出的「攻擊性觀點」(points of aggression) 的概念,讓我更理解人際關係底層正在發生的事:當我們把所有人、所有事都當作需要管理或最佳化的對象時,我們與孩子、與教會的關係就會被扭曲。
我在許多地方都看見這個現象,但我也想問,在實際層面上,我們確實需要「健康的權柄」,但不論在家庭或教會裡,「健康的權柄」究竟該怎麼做,才不會變成「攻擊性觀點」?這兩者有什麼具體的差異?
我們今天的焦慮,包括在教養孩子時,有一大部分源自於非常害怕讓別人失望。在這個時代,情緒被賦予了太多權力。但如果我們要學會說「可以」,就必須先學會說「不可以」——光是能劃清楚這個界線,就能給孩子帶來安全感與穩定感。這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有秩序、有可靠的架構的,他們不需要靠自己摸索一切。
現代教養的難題之一,是我們認為人必須靠自己「建構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整理好、展現給世界看。而我們把這個重擔從很小的年紀就放在孩子身上。雖然年輕世代的父母在這方面似乎開始改變,但很多 (西方) 父母仍會說:我們不會告訴你應該想什麼、相信什麼、做什麼,你要做你自己。可是有時候,孩子就是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我們家的孩子有時會不想去教會,這時我們會說: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家就是會上教會的家,這就是我們家的身份認同。
如果不設下這樣的界線,而是要求孩子自己去創造身份、定義一切,其實是在把超出孩子本分/當時能力的重擔放在他們身上。我認為,我們原本自以為的寬容、溫柔與恩典,最後反而會演變成帶有侵略性的彼此攻擊。這其實正是我們文化如今的寫照,我們活在一個缺乏寬恕、毫不留情的社會裡。
但基督信仰的敘事裡,擁有我們文化所沒有的——憐憫與饒恕。基督教敘事及教養之所以美好,不在於我們能夠避免教養時犯錯,而在於那些錯誤並不是最終的結局。上帝早已扶持著我們。我們能一次又ㄧ次回到祂面前,透過彼此的道歉與饒恕,以及透過重新扎根於彼此的愛,我們的關係反而能變得更強壯。
回顧你的家庭生活,你會發現,那些當下看似毀滅性災難的時刻,往往成為之後堅固彼此的契機。上帝從未停止在我們身上動工,這正是另一個美好的真理。祂會持續透過每一件事做成祂的工。問題是:我們願意參與其中嗎?還是我們會選擇抗拒、忽視祂的作為?
作為基督徒,我們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就是我們擁有「終末的盼望」。我們相信一位應許最終結局必然是「完全的愛」與「完全的連結」的上帝。所以,當我們身處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情境時,我們知道:這還不是一切的結局。任何一個糟糕的時刻,都不是那個決定性的時刻。因為我們把自己交託在一個更大的敘事中:我們有更遠、更寬廣的地平線。相較之下,我認為當今文化把每個決策、每個瞬間都變得極具高風險,好似一切都操之在我們手中、成敗取決於我們自己。但真相是:無論發生什麼事,哪怕不是我們原本希望的結果,我們仍然被上帝全然托住——這永遠不會是我們故事的終點。
的確,我在許多事上都深刻看見這一點:當一個人缺乏更長遠的視角時,每件事都變得更緊繃、更有風險。而這正是「靈命塑造」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也曾對我的孩子說:我們家就是會去教會、或做某些事——「因為我們家就是這樣做的」。我很常說像這樣的話,甚至有時我也會懷疑,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但當艱難的時刻來臨時,我也親眼見到這些日常習慣所帶來的影響,意識到這些操練如何獨特地塑造了我孩子的生命。
我們的信仰本質上是群體性的。我們一起讀聖經、一起實踐信仰、一起去教會——因為這個群體幫助我們成為教會。我們無法獨自成為教會。有些日子,你是那個感受到信仰力量的人;但其他時候你毫無感覺,而此時別人的信心會托住你。我們需要彼此,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也需要看見信仰群體一同生活的重要性。他們需要明白,自己屬於一個跟隨基督的愛的共同體,並且這個共同體正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