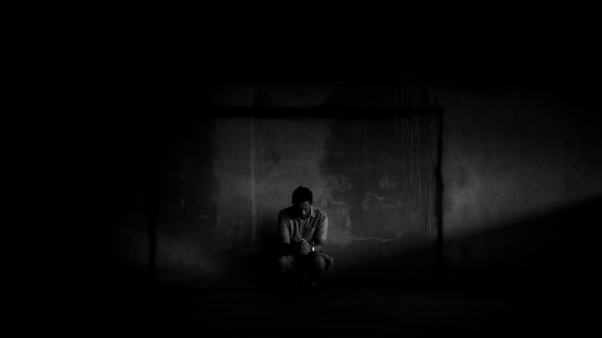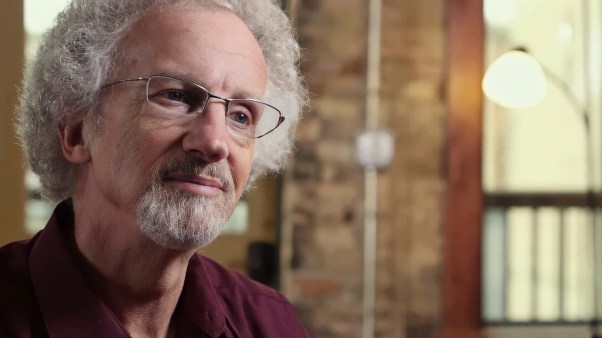有時候,一個很好的詞會嚴重失去它原本的意義,以至於最好暫時不再有人使用它。在1923年形容某人為「原教旨主義者/基要派」(Fundamentalist),與在2023年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1923年,這個詞指的是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存在)」的基督徒,如今指的卻是教派激進主義者 (sectarian militancy)。
幾年前開始,我意識到另一個很好的詞也已失去它原本的意義:「世界觀」(worldview)。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俗話是這樣說的。當然,這句話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對的。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框架看待現實,就塑造了我們的樣貌。但多年來,我已厭倦見到「世界觀」這個詞被放在教會與世俗世界打的文化戰爭的清單上,然後附上所謂「正確的基督教觀點」。
我也越來越相信,這些與「世界觀」有關的談話,預設了一些我認為不正確或「不符合聖經教導」的想法,也就是基督徒們會預設:一旦人們接受了某種真理後,就會將其應用在生活裡。 任何在真實世界與活人接觸過的人都應該知道,更常發生的,其實是與此完全相反的情況。我見過無數個有著「聖經/基督教世界觀」的人,一但陷入婚外情,就會瞬間改變自己的世界觀。
提摩太·凱勒牧師 (Tim Keller) 為巴文克 (J.H. Bavinck) 的《人格與世界觀》(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一書撰寫的前言裡,正好分析了我對這個詞被氾濫使用的方式的質疑。也許有些人ㄧ聽我提起這位過世很久的荷蘭改革宗神學家,就會想打哈欠,但這本書光是有凱勒寫的前言,以及其譯者兼編輯恩雅各 (James Eglinton) 所寫的序言,就已值得其定價且值得一讀了。他們兩人皆指出「看待世界的方式」(world-vision) 和「世界觀」(worldview)」之間關鍵的差異。
他們的論點之ㄧ是,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world-vision),但很少人真的擁有一套世界觀 (worldview)。
恩雅如此定義「看待世界的方式」(world-vision):個人的家庭和家庭環境、老師及受過的教育、所處的廣泛的文化在其身上形成的一套「關於世界的直覺思維」,然後再加上「個人氣質的特殊性」。這種獨特的組合使一個人擁有一個「可運作的思維框架」來過每一天的生活。
換句話說,我們不只是「因著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而依據一套我們認同/否定的真理主張 (propositions) 來看待這個世界——我們的個性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喜歡找到自己的九型人格 (enneagram) 或做MBTI測驗的原因之一 (或甚至是在網路上做「你是哪一種漫威人物?」) 心理測驗。
這類測驗,若沒有提供任何益處,至少還能為我們提供一種「能象徵我們」的東西,用以解釋為何我和妻子在聽到一個朋友在車禍中倖存的消息的反應會如此不同。如果像漫畫那樣能看到我妻子頭上的思考泡泡,你會看到她想著:「我們得把大家聚在一起,為他的家庭準備食物,幫忙接送他們的孩子去學校。」
而我的思考泡泡卻會是這樣:「生命真是短暫而脆弱的⋯⋯死亡會向著所有人走來⋯⋯」,然後再冒出《詩篇》104篇,或一些沃克·珀西 (Walker Percy) 的名言,以及吉米·巴菲特 (Jimmy Buffett)《他去了巴黎》的歌詞。
但如果我和妻子一起做一份解讀我們的原則或價值觀的「世界觀測驗」,我們的得分會幾乎一樣。畢竟我倆在離對方只有幾英里距離的海邊長大,我們成長的文化是如此相似。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我是九型人格的第四型,她是第二型」來總結我們對朋友的車禍為何會有不同的反應。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深不可測的,沒有任何人能完全被某種「世界觀」(worldview) 或「人格類型」(personality)「解釋」。
在巴文克的理論裡,雖然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看待世界的方式」(world-vision)——靠著這些基本的假設和框架來度過一生,但很少有人真的發展出自己所謂的「世界觀」(worldview),也就是對生命的意義有一個更加明確、有意識的認知。
許多人活了一輩子,從未真正質疑過他們人生的基本假設,或他們身處的文化裡的假設。然而,有些人 (通常是遇到危機時) 會問自己這樣的問題:「這(發生的ㄧ切)究竟意味著什麼?究竟有什麼意義?」
布希納 (Frederick Buechner) 曾說,當傳道人打開聖經並朗讀時,在任何教會禮拜上,都會有個靜止的時刻——會眾之中某些人,會希望聽到對某個問題的答案,並自問:「這 (聖經所說的) 是真的嗎?」
認為聖經給了我們好的原則來管理我們的生活、獲得靈性上的體驗、能用在關於「價值觀」的辯論裡;或認為聖經能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配偶、父母或公民,是一回事。但去問:「若一切事物,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是由祂的力量維繫在一起,對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和問「若世上真有一位上帝,我就在祂之中生活、行動和存在,這個真理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以及問「若『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這句話說的是真的,我的人生會有什麼改變?」——則是另外一回事。
與我們多數基督徒喜歡使用「世界觀」(worldview) 一詞的方式不同的是,「世界觀」其實並非一套確定的抽象概念;而一個人同意這些抽象的概念後,僅僅應用在一些與真理有關的問題上。世界觀 (worldview) 是關於「在所有事物/處境下,認識到『什麼樣的敘事』才是真實正確的,以及認識到『我自己正生活在什麼樣的敘事裡』」。而基督教敘事的時間線,暫時沒有完結點。
在耶穌從「餵飽眾人」到談論「吃祂的肉、喝祂的血」的沈重事實後,門徒在海邊對耶穌感到生氣時,手上尚未有初版的《使徒行傳》,更尚未經歷過關於基督在聖餐禮拜中的存在的各種神學辯論。彼得的腦子裡也沒有已經寫好的《彼得前/後書》的初稿。耶穌只是淡淡的對彼得說:「你們也要 (像那些人一樣) 離我而去嗎?」(約翰福音6:67)
彼得的回答,比起一百萬種將人類分門別類的「世界觀小手冊」更重要。他說:「主啊,祢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祢是神的聖者。」(約6:68-69)。
就許多方面而言,彼得看不到他將要走上的路,更不足以對他周圍的世界有個「全面性的理論」。彼得只知道眼前這個人就是道路;彼得知道,無論自己 (努力解釋腦袋中的理解) 會出多少錯誤,他都會跟隨這個聲音,進入祂呼召他去的任何不可預知的未來。無論這位耶穌去哪裡,都是他想去的地方。
彼得的人生是否與腦中這個信念維持著一致性和連貫性?福音書記載了太多彼得對耶穌所做的事的巨大誤解:彼得通常會說些蠢話,然後被耶穌糾正。並且,在耶穌被捕後的火爐邊,彼得的「世界觀」似乎是:我從不認識這個人。
但耶穌卻一直尋找彼得。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復活後,來到彼得與祂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在加利利捕魚的地方。而即使他們在情感上和解後,彼得又開始問些蠢問題,這次,耶穌拒絕回答。但耶穌對彼得說的最後一句話,與祂和他說的第一句話一樣:「跟從我」。
你的無神論鄰居的靈魂,遠遠深於他們的世界觀。無論你們在咖啡廳裡有過什麼樣的辯論,他都是個複雜的靈魂,而且經常以與他所持有的抽象概念 (價值觀/世界觀) 不一致的方式在生活——就像你一樣。也許他能告訴你15個為什麼「相信上帝跟相信飛天麵條怪獸存在一樣蠢」的理由。
即便如此,在這樣的「世界觀」的背後,可能是一個害怕、孤獨和充滿羞恥感的人。
也許他還會發現自己在那些他的世界觀似乎不「奏效」的時刻問自己:如果那 (聖經所說的) 是真的呢? 也許那會是他看著自己剛出生的寶寶、或他站在大峽谷前、或他聽到詩篇23的時刻;也許有時,即使在他所有的理性思維爭論下,他甚至會希望那 (聖經所說的) 是真的。
你也一樣,你遠比你的世界觀更深、更複雜。
當然,哲學性質的辯論在教會歷史和信仰的追求裡,佔有重要地位。但聖經呼召你「心意更新」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你學會辯論的方式,而是首先提醒你注意上帝的憐憫。透過心意更新,你將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羅馬書12:1)。這樣的努力涉及你的全人——你的情感、你的直覺反應,和你的渴望——而不僅僅是你的理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多數人在臨終前,不會轉向討論神學理論或各種爭議,而是吟唱我們學過的詩歌、我們知道的真實的信仰故事,以及那些親自在黑暗中以細小光芒見證這些事、讓道成了肉身的人——即使是以他們充滿缺陷的、零散的方式。
也許在那些時刻,我們甚至無法用我們的肉眼親自看到。但我們仍會知道我們想要走的路——祂所在的地方。這並不是一個可以一次性地解決所有問題,和贏得所有爭論的世界觀,但對一個在地球上的生命,以及在那之後的生命來說,已經足夠了。
羅素-摩爾是本刊主編,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