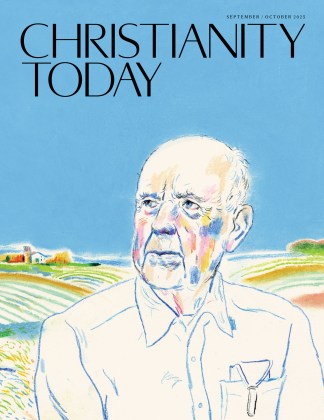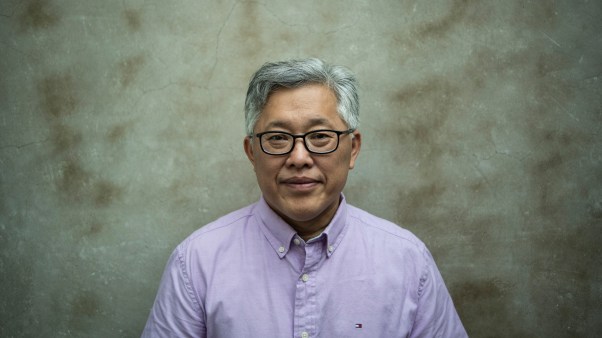也許你從沒遇過這樣的事,但它肯定曾發生在別人身上。
公司祕書交給你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急事,打電話回家。
你感到喉嚨乾澀,在辦公室按下電話按鍵。鈴聲才響一下,你的配偶馬上接起來,他的“喂”聽起來非常哀傷,似乎剛受到驚嚇並哭過。
兩分鐘後,你掛上電話,你的手發抖著,感覺喉嚨好像腫了起來。此時,你只能盯著牆壁看。你剛得知自己17歲的兒子在車禍中喪生了。
起初你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幾小時前我才見到他阿,他不可能死了!”
你告訴別人你必須馬上離開時,腦子ㄧ陣暈眩。你沒有多加解釋,別人疑惑地看你奪門而出。你衝進車內,啟動引擎,急速趕回家。
在震驚後的麻木狀態下,內疚和憤怒的情緒湧上心頭。我真不該允許他開車、他的朋友們不該叫他自己過去、他當時不該去的⋯⋯上帝不該讓這事種發生!
當你抵達醫院時,你的情緒從未經歷如此多變化,從內疚到無助,再到憤怒,最後轉至悲痛。還有那麻木的感覺,讓你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卻仍會感到疼痛。
在醫院的小禮拜堂裡,你問醫生和警察幾個問題:“是不是……車速太快了?到底怎麼發生的?”
你未曾想到的是,他們的回答會讓你陷入更深的黑暗中。警官低聲說,“你兒子把車子撞進水泥橋墩裡,他給朋友留下一張紙條,他是自殺的。”
你坐下來,這噩耗慢慢侵入你的思緒裡,你完全無法相信。你的兒子不只是死了,而且還是他自己決定要死的。自殺是拒絕一個人最終極的形式:出於某種原因,他覺得不繼續活下去,比和你一起生活更好。
眼淚終於止不住地流下來。你充滿內疚的哭著,雖然你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預防這場悲劇,但你還是讓兒子走上了不歸路。你甚至因他選擇自殺而替他感到內疚。
在那些你無法入眠的夜晚裡,你被拒絕的感覺逐漸轉為苦毒。孩子怎麼可以這樣對我?一想到要向親戚、朋友及教會解釋,你的哀傷轉為羞愧。當這羞愧緊緊抓住你時,你開始感到孤單,這種孤單的感覺是如此厚重,以致於你覺得沒有任何人能穿透它。
以上這個想像出來的場景只稍微揭示了自殺者的親人所經歷的情感漩渦的一小部分。因自殺而失去摯愛的人所感受到的悲痛,通常比我們多數人能想像的更可怕。
當自殺發生時,活著的親人往往會發現,有能力或願意幫助自己的朋友少之又少。通常會有牧師被叫去自殺現場、家裡或醫院安慰家屬。
我第一次面對自殺者親屬的傷痛時,是警局的駐點牧師。我被請去幫助一個家庭,他們的兒子用散彈槍朝自己的頭開槍。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或該說什麼,以及長期而言,什麼樣的做法對這家人而言才有幫助。
自那時起,我便有機會服事許多因自殺而陷入痛苦的家庭。根據這些經驗,以及一同服事於此事工的同事的見解,我能夠去裝備牧師、警官、警局牧師和諮商師。我發現,雖然他們身處於極大的震驚和悲痛之中,我們仍可對這些因自殺失去摯愛的人有著極有意義的服事。
誠實面對痛苦的事實
我所學到的第一個,也或許是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必須誠實以對。首先要向逝者的親人直白地說出“自殺”一詞,而不是委婉地說類似“不幸的事件”等詞彙。
這ㄧ點不容易做到。悲傷所帶來的侷促不安感會讓我們不想面對真相。那些因自殺而失去親人的人,都不想面對“摯愛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此痛苦的事實。但不去面對,只會讓人更難從悲傷中恢復。
克拉拉曾試圖隱藏真相。她的丈夫在她年輕時,死於一起悲慘的“意外事故”。在她所住的小鎮,每個人都知道她和吉姆的婚姻有些問題,而且吉姆一直深陷於憂鬱症。
當警方和她解釋意外現場時,克拉拉已懷疑吉姆是自殺的。她聽到有人根據驗屍官的調查結果在背後說著殘酷的謠言。她知道鎮上有許多人說吉姆是自殺的,只因驗屍官是他們的老友,為了減輕她的痛苦才判定為意外死亡。事實上,謠言是對的。
多年後,當她兒子到了會質問父親死因的年紀時,克拉拉被迫面對事實:吉姆是自殺的。這個事實帶來的震驚和羞愧遠遠超過她所能承受。承認多年來的自我欺騙及接受丈夫自殺的事實,幾乎使克拉拉情緒崩潰。當初幫她逃避事實的朋友實際上完全沒有幫到忙。
沒有人在面對自殺的事件時會感到自在的。但我發現,若不能誠實以對,哀痛就不會結束,醫治則不會發生。
當然,坦白的說出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粗暴或不敏感地處理他人的情感。我們可以溫柔、充滿愛的說出事實。我們不必假裝自己不害怕、不尷尬,或沒有同樣受傷。事實上,當我們流露出這些情感時,我們便是向喪親者表示,他們也能放心地去感受及表達這些情緒。
接受“毫無節制”的情緒
我們千萬別避開喪親者的情緒,無論有多令人不舒服。傾聽和接納他們的感受是這個事工裡很重要的一環。但要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可能跟我在馬克家的經驗一樣難。
馬克是開槍自殺的,他的家人因此對他感到極度的憤怒,其中有家人甚至希望他能再次活著,這樣他們就可以殺了他!
我第一個回應是試著讓他們冷靜下來。“你們不是真的想殺他吧!”,我這樣說。
馬克的妹妹冷漠且清晰地回答:“沒錯,我就是想殺了他。”當我看著這個痛苦的女人的眼睛時,我知道她是認真的。
但似乎在藉著言語發洩這些情緒後,她就得到釋放了。ㄧ陣子後,她得以放下恨意,好好的面對失去親人的感受。如果我當時地阻止她發洩任何想說的話,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我因此學到了寶貴的教訓:每個人都有權力,甚至有這樣的需求——去感受並表達這樣激烈的感受。馬克的妹妹無法阻止自己這樣發洩憤怒,就如同我無法阻止一朵雲飛過我的頭上。她需要面對這樣的憤怒,當她這樣做了,她最終會能夠控制她的情緒。
我們必須預備自己去傾聽多種不同種的情緒。有些喪親者感到強烈的憤怒和恨意,其他人則感到痛悔或內疚。還有一些人可能會感到釋放,甚至平靜及快樂。
問題不在於人是否應該有這些情緒,情緒已經在那裡了。問題在於:這些情緒裡究竟深藏著什麼樣的情感?最健康的表達方式是什麼?
當我覺得喪親者的情緒太極端或不夠深時,我會強迫自己去聽他們說話,豪不打斷。這能幫助他們釋放、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悲傷,並為其他家庭成員設下榜樣。這個榜樣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我願意聆聽你的任何感受,而你們也必須為彼此這樣做。」
只有上帝能審判
我記得約翰這個人,他似乎盡全力在妥善處理母親自殺的事。但是,他每天晚上都會醒來,因爲想著母親可能因自殺而下地獄而飽受折磨。
上帝是否已經因她自殺而定她的罪?長久以來,神學家一直都在辯論自殺者在永恆裡的去處,但是,根據我對聖經的理解,我不覺得約翰有任何需要恐懼的理由。我鼓勵他信靠神——那唯ㄧ有資格審判他母親的神。當約翰開始信靠上帝時,他的注意力就從他母親曾做過的事,轉到神已爲他們成就的事上。
對教會領袖來說,把審判的事交給神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常常被喪親者視爲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即使家屬很想知道神最後的裁決為何,但藉著拒絕對自殺者的去處下判決,我們能鼓勵他們去相信上帝的主權。
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提供虛假的盼望。有很多悲傷的親屬來找我,向我打聽某位親人“現在是否與神在一起?”
雖然很難,但我唯一能給的正確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即便我想赦免,而不是定罪,但審判的權柄終究不在我手上。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喪親者,神是唯一有資格的審判官,而祂審判的依據是我們與基督的關係。
以接納代替被拒絕的感覺
我們的生命裡可能充滿拒絕的不同種形式,如:無情的言詞、未獲得的傾聽時刻、說話被打斷。但沒有一種拒絕比因自殺而失去親人的人所感受到的拒絕還強烈。對他們而言,自殺的人向他們傳遞了“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生活”的訊息。
我有位警局牧師朋友曾會見一位年輕的妻子。她的丈夫在跟她吵架的當下自殺了。他在扣下手槍扳機前喊道:“我就做給妳看!”
這位年輕妻子受到極大的驚嚇。她的丈夫幾年前才宣誓要與她共度餘生。她覺得丈夫是為了擺脫這個承諾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她被丈夫以這種可怕又極端的方式拒絕,以至於她覺得自己是世上最沒有價值的人。
我的牧師朋友和她一起坐了好幾個小時。隔天也打電話陪她聊天。從那以後,他時不時就會去探望她。他透過自己的言語和行爲和她說:“神接納妳”。若不是他親自做了這些事,她可能會很難相信這句話。
要提供這種接納的感覺可能會花不少時間,而喪親者有時可能會太過依賴幫助者的陪伴。爲了避免這類問題,主要的幫助者可以在不中斷聯繫的前提下,介紹其他同樣關心他們的人。這能讓喪親者知道其他人也接納著他們。
不要忘了陪伴的力量
我們經常會以為在這種時刻必須對喪親者說正確的話。但僅僅陪在他們身旁也是極有價值的事。
在我早期接到的其中一次自殺案例裡,我被要求和家屬坐在他們家的飯廳,警察和驗屍官在屋子另一邊檢查現場及遷移屍體。這間房子很小,我們幾乎可以聽到每句話、每個聲音。
我問家屬是否願意暫時離開房子,讓驗屍官完成工作。他們拒絕了,默默地坐著。長達10分鐘之久,我試著向家屬們說些有意義話,卻想不出半句。所以我問他們,我是否可以只跟他們一起坐著,他們同意了。
我們就這樣默默坐了一個半小時以上。有時有人會移動身體的重心,我們的眼神會有所交會,好像在進行某種視訊會議那樣。我在那個飯廳裡有著前所未有的不舒服感,但我覺得這個家庭需要有人陪伴在那裡。
驗屍官和警方離開後,我又待了一個小時。在我離開前,我懷疑我們說到話的時間連15分鐘都沒有。
第二天,因爲這個家庭沒有所屬的教會,我被請去主持葬禮。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我和他們只有零星的接觸。那段時間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失敗。我覺得自己無法給他們需要的東西。我真希望當時還有別人能幫助他們。
自殺發生將近一年後,一位朋友提到,他曾見過這家庭的一位成員。他跟我說,“我不知道你當時做了什麼,但是他們肯定是非常感謝你。”
但我當時做的只有陪伴他們。如果我當天試圖與他們有些對話,也許結果就不會這麼正面。這些家庭成員需要一個外面的人與他們待在一起,和他們一起感受傷痛。現在每當我遇到這種情況,我會刻意允許一段沉默的時間。事件過後,喪親者們會和我提及那段時間的重要性。
當然,“在那陪伴”的時間要多長,端看幫助者的時間安排。我發現,在事情發生的當下,通常需要一到三個小時的陪伴,便足夠表達我對這個家庭的關心。在這段時間裡,除非家庭成員有所要求,否則我不會留下他們去獨自面對。我知道他們不會想要我一直留在那裡,但他們需要知道我不會離開他們。
引至饒恕的道路
當我和喪親者相處時,我發現他們也許需要兩種饒恕。第一種饒恕與喪親者有關:他們本身渴望得到饒恕。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上要為自殺事件負責任。有人會悲傷地說:“如果我更常關心他就好了”;“只要我更有愛一點,或讓她見她的男友,或…”。
有時,這些“只要”足以引起極大的痛苦。例如,珍妮特的家人知道她有自殺的想法。他們不停地注意著她,每十五分鐘就開車經過她家,查看她的狀況。有次經過她家時,他們看到她的車子在車道上,引擎正運轉著。他們觀察了一下,發現珍妮特坐在車裡,所有車窗都關著,但有一根吸塵器的管子接在汽車的排氣管,透過後車窗向車內灌入濃煙。
因為他們及早趕到,珍妮特還沒受傷。他們取下軟管,把她帶回她家,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他們應該打電話給警察,還是將珍妮特送到急診室?珍妮特向他們保證那天晚上她不會再自殺了,她只想睡一覺。最後,家人拿走她的車鑰匙和吸塵器軟管,就離開了。
但珍妮特還有一組備用鑰匙跟另一跟管子。次日早晨,鄰居發現她在車子裡,已沒了氣息。
珍妮特的家人知道自己作了錯誤的決定。當我見到他們時,他們不斷提起這件事。如果我否認這不是他們的錯,我也不夠誠實。但我可以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錯誤是可以被原諒的。
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可以原諒他們。他們需要從我的行動中看到,基督也願意饒恕他們。然後他們需要理解如何饒恕自己。在往後的幾個月裡,我不斷向他們保證他們可以得到饒恕,他們也慢慢的接受了饒恕。
對像珍妮特家屬這樣的人來說,神學性的對話並不能帶來醫治。但是,簡單地分享基督對我們的愛,以及祂願意赦免我們的罪,總是恰當的。我會試著解釋饒恕有其具體且實際的一面。我說:“我知道你們現在不覺得自己真的已被饒恕了,而且你們可能也沒有這樣的期待。但饒恕不僅僅是一種感覺,它更像是一種行動——決定不要求別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的行動。這是神在基督裡爲我們做的事:不讓我們為自己的罪付出代價。如果上帝饒恕你了,你也可以饒恕自己。”
如果一名喪親者感受不到饒恕,他會因自己沒有阻止自殺而感到憤怒。憤怒的根源在於受傷,只要他感受到這傷害,他就會對自己生氣。但他不需因生氣而拒絕接受饒恕。
我也許會說:“看看你對自己做的事”,“你沒必要一直懲罰自己、不斷提醒自己所做的事、拒絕別人給你的幫助。你有權決定,一步一步地接受上帝的饒恕,並原諒自己,從錯誤中學習,或許將來可以幫助別人。”一旦做到這點,喪親者就能在哀慟這條路上自由的走下去了。
第二種饒恕,是饒恕自殺的人。
傑克在13歲那年經歷到父親最終極的拒絕:父親自殺了。這男孩需要別人幫助他,饒恕拋下他的父親。
無論傑克聽到多少次關於父親精神病情的解釋,無論他聽到多少次關於父親所承受的壓力,全都無濟於事。傑克無法停止他的憤怒及怨恨。
幫助傑克的第一步,是讓他看到別人已原諒他的父親——不是一同責怪父親的決定,而是展現饒恕的意願。然後,幫助傑克看到,拒絕饒恕並不能傷害到他的父親,反而是傷害他自己。
傑克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接受他父親的不完美,但男孩最終能夠原諒,並在悲痛中繼續前行。
接到下一通電話時
在幫助自殺者家屬的事上,沒有任何方法能保證一定成功。有時我們會覺得這種事不是我們能處理的,因此需要轉介。即便如此,這並不妨礙我們去接聽下一通語無倫次的喪親者的電話。
陪伴經歷自殺事件的受難者,是一種特殊的服事機會。身為幫助者,我們對喪親者而言很特別。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代表著神,而他們通常會認真看待我們代表神的這個身分。我們雖然不必要求自己有完美的表現,但這確實給我們機會,以基督的方式向人樹立同理心及饒恕的榜樣。
版權所有 © 1989,本文作者或《今日基督教》/《Leadership期刊》,點選此處以取得《Leadership期刊》的相關資訊。
翻譯:榮懌真 / 校稿: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