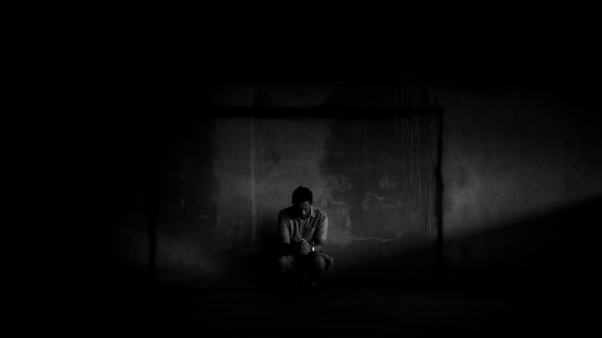在羅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最新著作《不靠謊言而活:基督徒持異見者手冊》(Live Not by Lies:A Manual 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中,有很多內容是真實的、有見地的,需要認真考慮的。
往好處說,這本書迫使一個日益破損、兩極分化的基督教會為其道德和政治冷漠做出回應。 然而,德雷赫的著作缺少了某些東西——一種自知、一種謹慎的清醒,並意識到,即使是那些站在正確一邊的人,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自己試圖摧毀的東西。
德雷赫是“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專欄作家,可以說是互聯網上閱讀量最大的保守派博主,他並不缺乏口才或智慧。 他在2017年出版的《本篤選項》(The Benedict Option)一書中展示了自己的洞察力。這是一本廣為傳閱的宣言,呼籲西方基督徒有意識地再投資,建設屬於自己的美德社區,而不是試圖通過政治贏得一場文化戰爭。 《本篤選擇》是一本撼動人心之作,它向處於十字路口的教會強力發聲,在那些渴望更健康地參與文化互動的基督徒中產生了共鳴。
不幸的是,前面那本著作所有的屬靈敏銳在《不靠謊言而活》中常常缺失。 事實上,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根本不是教導性的或與現實相關的,而是以基督教為主題的,就蘇聯極權主義進行的深入探討。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德雷赫與蘇聯壓迫倖存者及其後代的對話和相遇。 事實上,德雷赫將他寫作本書的願望,歸因於他接到的来自一個捷克家庭的電話。對方非常擔心,在美國發生的對宗教自由的攻擊,會類似於他們20世紀時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經歷。
兩本書合而為一
根據他的旅行和談話,德雷赫得出了一個可怕的診斷:美國已經心甘情願地接受與傳統宗教和保守思想為敵的人所施加的“軟性極權主義”。 德雷赫寫道:“一個進步主義的、堅決反基督教的好戰主義正在穩步地控制整個社會。教皇本篤十六世將其描述為一種‘貌似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全球專政’,將持不同政見者推向社會的邊緣。” 德雷赫接下去以一種雙重方式闡述了他的觀點:每一章都將共產主義倖存者的歷史見證與當代美國的情況進行比較,特別是在宗教自由、性和言論自由等文化戰爭問題上。
對這種總結感到反感的讀者應該知道,德雷赫並非完全沒有證據。 第三章題為“作為宗教的進步主義”,揭示出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普通大學校園的主導世界觀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 德雷赫對現代進步主義那種懲罰性的、因關聯獲罪(guilt-by-association)的絕對主義傾向的擔憂,絕不是右翼狂熱的夢想。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等非保守派人士(沙利文自認為保守派人士——譯註)也多次提出同樣的觀點(後者最近被迫辭去《紐約》雜誌的專欄作家職務)。 引用已故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對極權主義文化的觀察,德雷赫評論到:
思想罪(Thoughtcrime)… 就其本質而言,是把被控有罪和實際有罪混為一談 … 當代思想罪的範圍被不斷擴大——同性戀恐懼症、伊斯蘭恐懼症、跨性別恐懼症、雙性戀恐懼症、肥胖恐懼症、種族主義、能力主義(ableism)等等——讓人很難知道一個人何時踏上安全的土地,還是即將踩上地雷。
德雷赫的觀點似乎很難爭辯,因為在這個世界里,像J.K.羅琳(J. K. Rowling)這樣正宗的自由主義者,僅僅因為相信男人不可能是女人而面臨強烈反對;Mozilla高管布倫丹·艾希(Brendan Eich)可能會因為對同性婚姻的看法與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觀點相同而失去工作;或者,《紐約時報》意見專欄(op-ed section)的編輯,可以僅僅因為發表一篇讓某些《紐約時報》進步派工作人員感到反感的文章——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關於部署聯邦軍隊以平息今年(2020年——譯者註)夏天國內動蕩的 短文 ——而被迫放棄他的職位。 德雷赫有充分的理由懷疑,美國的進步主義已經在擁抱意識形態純潔性測試,其方式讓人想起了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濫權。對這一點還心存疑問的人,需要正視那些在典型保守陣營之外的人們所表達的日益增長的擔憂。
如果這是德雷赫的見解,那麼《不靠謊言而活》將是一本準確但不起眼的著作。 但這本書傳達的信息,不僅僅是進步主義者變得不寬容,而是這種不寬容——加上普遍的文化頹廢和監控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崛起——正在公開威脅傳統基督徒的生命和生計。 德雷赫將硅谷的“定位服務”創新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相提並論,並警告說,在正在形成的美國社會新形態中,殘暴政權的倖存者會認出敵人的面孔。
德雷赫寫到,“極權性共產主義政府為更容易地掌控被其奴役的人民而曾強加給他們的那種粉末化和極端孤獨感”,正在被技術資本主義(techno-capitalism)複製。 對於這一觀點,他主要以人們的故事來支持:基里爾·卡萊達(Kirill Kaleda)是一位俄羅斯牧師,其職業生涯和前途因他的反蘇信念而永遠被壓制;尤里·西普科(Yuri Sipko)則是一為俄羅斯浸信會信徒,他記得老師被迫在學校向他灌輸思想。
《不靠謊言而活》中真的包括了兩本書。 第一本書是就對抗蘇聯的非凡屬靈韌性的歷史記錄。 第二本書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懇求,要求當代美國基督徒在第一本書中看到自己,感受歷史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併為將遭受的壓力、迫害甚至其他做好準備。
德雷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在報導宗教自由鬥爭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鑒於此,就即將到來的覺醒(woke)極權主義危險,《不靠謊言而活》所提供的證據弱得令人驚訝。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給人一種印象派的感覺,從對蘇聯歷史的見證轉向當代文化分析,然後再回到蘇聯歷史,似乎這種做法本身就足以使論點不證自明。 德雷赫承認,19世紀後期歐洲的宗教、社會和政治狀況與現在的美國大不相同,但他認為這種差異基本無關緊要。 他對美國基督教的評價很低——“治療的風氣已經征服了教會。 … 相對而言,當代基督徒較少願意為信仰受苦”——但他幾乎沒有提到美國對宗教自由的強大(儘管不是不可滲透的)法律保護。 最終,他沒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路線圖表明,一個法律體系受到第一修正案深刻影響的國家,及其在歷史上篤信宗教的公民,如何能夠陷入覺醒主義的恐怖之中。
這樣的路線圖是否存在? 有可能。 但也有其他可能需要考慮,比如另一位基督教公共知識分子羅斯·杜塞特(Ross Douthat)提出的替代方案,他的著作《頹廢社會》(The Decadent Society)認為,美國社會更有可能徘徊在懶惰的政治停滯和不可動搖的亞文化飛地中,而不是屈服於任何真正的極權主義。 關鍵是,預言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擁有最深刻的宗教信念、社會信仰的人仍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所有不斷變化的情況。 德雷赫熱情地陳述出論點,並非沒有任何支持論據,但說到底並沒有說服力。
兩種謊言
現在我們要討論《本篤選擇》和《不靠謊言而活》之間的相異之處。在屬靈上,後者似乎遠不如前作那樣對準那些誘惑保守派基督徒的特定誘惑。 雖然《本篤選擇》描述了對權力的追求如何使信徒失敗,但《不靠謊言而活》給人的印象是,我們在不再追求權力之前應該先鞏固權力。 《本篤選擇》找到了教會內部最緊迫的絆腳石,而《不靠謊言而活》毫無疑問地在說,精英的覺醒主義左派應該為此負責。 《本篤選擇》挑戰我要站在正確的一邊。 《不靠謊言而活》則讓我讓我安心——我已經站對隊了。
這些都是來自一個與德雷赫的神學承諾有深刻共鳴的人的批評。 關於主流文化鄙視傳統基督徒,他是絕對正確的。 我們的公共空間(public square)長期以來正在慢慢挪向虛無的相對主義,現在很容易受到集體主義團結一致的誘惑,關於這一點,他無可爭辯地也是正確的,。 但是,將《不靠謊言而活》寫成反對覺醒進步主義者的聲討檄文,德雷赫錯過了向世俗革命者和右翼反動分子兩方宣講對真理的承諾的一個關鍵機會。 儘管有少數幾段關於“雙方”罪惡的段落,但德雷赫如此一心一意地專注於在共產主義霸主和自由派精英之間勾畫出相似之處,以至於他錯過了基督徒身份和信仰所具有的反文化、反部落主義特質。
那些完全讓自己對絕對真理的承諾和上帝對萬物的主權來塑造他們直覺的基督徒,不會輕易地被映射到美國的政治網格上。 同一本《聖經》,既為待出生嬰兒之將為人而欣喜,也譴責不善待移民和陌生人的行為。 同一本《聖經》,既命令人們要照顧窮人、面臨種族衝突時要求和解,也揭示了上帝創造“男性和女性”的設計。 關於真理客觀性的同一聖經原則,既打斷了交叉性理論敘事(intersectional narratives),也駁斥了“被偷去的選舉”這種陰謀論。 在文化戰爭中,福音對於各方的冒犯是機會均等的。
我們確實必須拒絕生活在謊言中:不論是我們所處的世俗時代告訴我們的謊言,還是我們告訴自己的謊言。 德雷赫對第一類所說的話是對人有幫助的, 我希望他就後一類有更多的話要說。
塞繆爾·詹姆士(Samuel D. James)擔任 Crossway Books 的徵稿副編輯,他的博客是 “文字與聖禮”(Letter and Liturgy)。
翻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