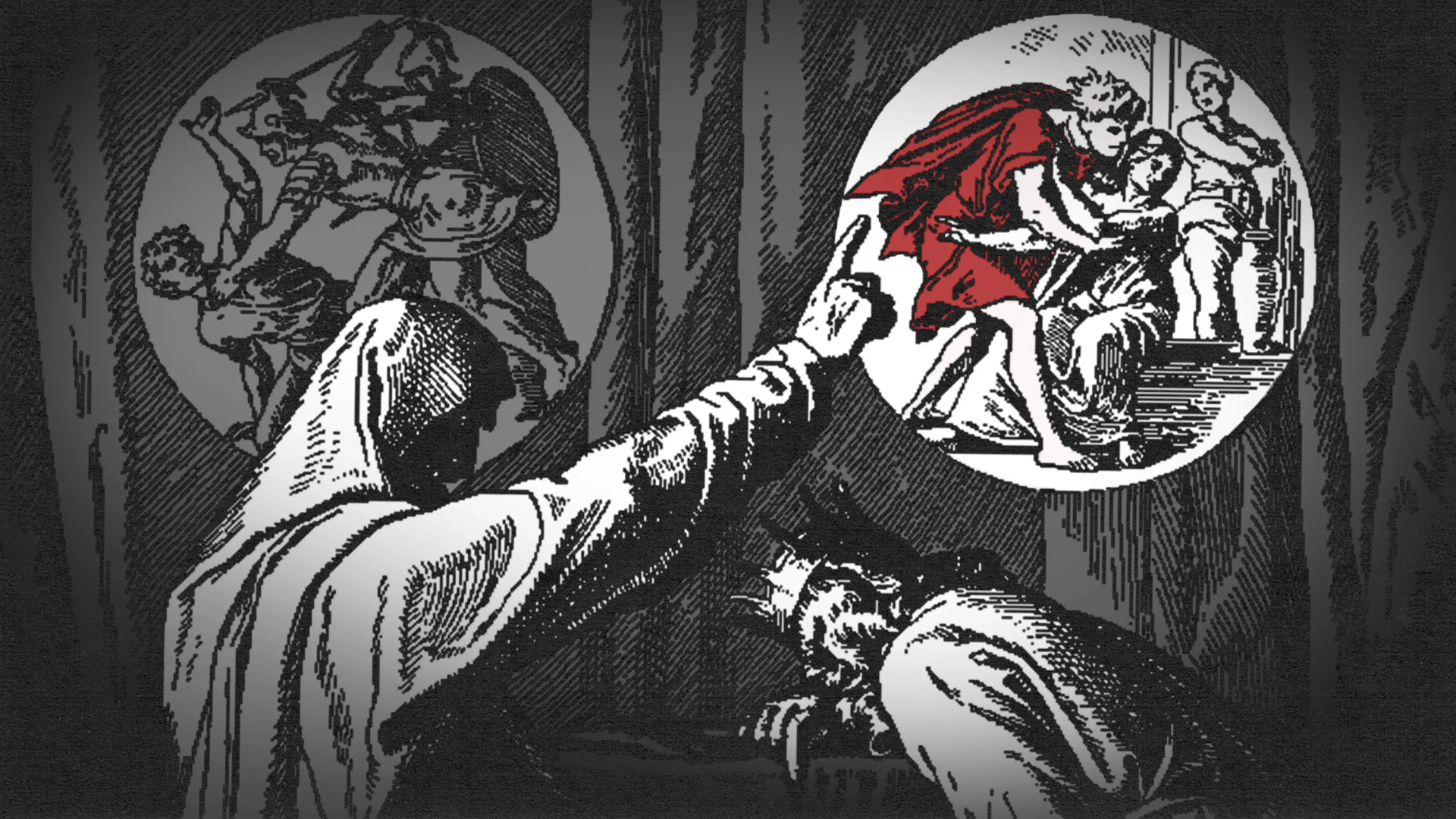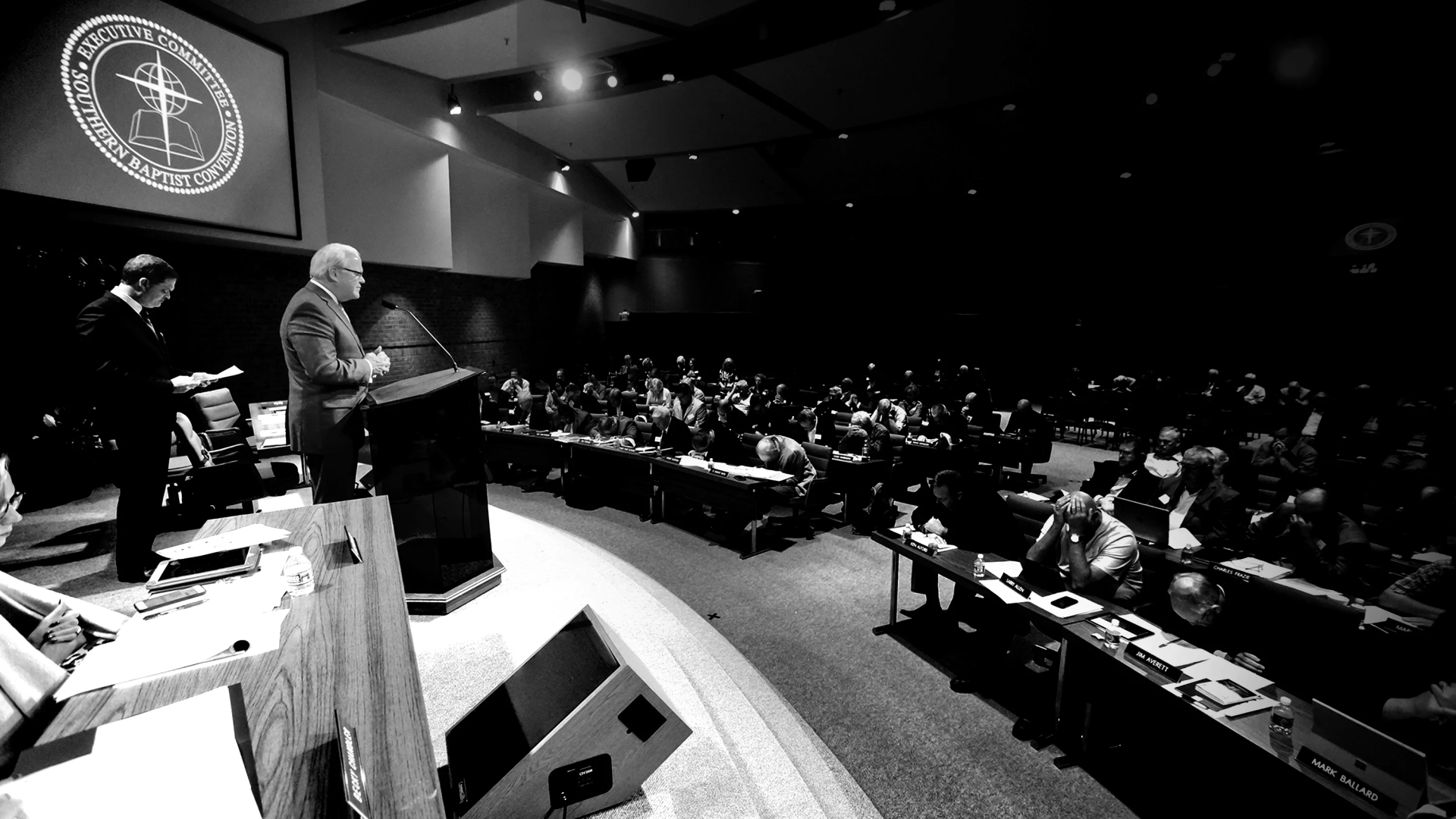當基督教新教在19世紀初來到中國時,中國人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已經相對固定了兩千多年。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儒家學說培養了對父權制的理解,在中國社會中婦女往往處於從屬地位。兩性也按照公認的社會角色進行劃分,男性關注公共事務,女性專註於管理家庭。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隨着女性識字率和經濟角色的積極變化,越來越多的有學識和有影響力的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最引人注目的變化要到20世紀20年代初的五四運動才發生。當時,改革者們團結起來反對纏足,主張婦女擁有選舉權、經濟獨立以及選擇結婚對象和離婚時間的自由。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新教的歷史包括一些支持男女平等的基督徒的故事,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走在了倡導婦女在教會和社會中平等的前列。到19世紀60年代,中國婦女通過基督教的事工獲得了離開家庭、從事教育、傳教和醫療服務的機會。到了世紀之交,中國的教會討論了女性基督徒領導和女性按立的問題。在整個20世紀,婦女在傳播福音和培養新信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近幾十年來,女性領袖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不承認建立中國教會的女性傳道人和牧師,就無法講述基督教在中國的故事。
聖經女教師(Bible Women)的崛起
1807年,英國蘇格蘭公理會的馬禮遜成為第一個踏足中國大陸的新教宣教士,他的事工以廣東(廣州)和澳門等沿海地區為基地。鴉片戰爭(1839-42年和1856-60年)后,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對中國徵收的“不平等條約”允許宣教士自由租用或購買財產,並在中國內陸建立自己的機構。雖然這些條約為宣教提供了新的機會,但新教宣教士很快意識到,儒家對禮節和社會秩序的理解限制了男性宣教士只能與中國男性一起工作。新教宣教士中的女性——宣教士的妻子,以及後來的單身女宣教士–專註於向中國婦女傳福音,但她們同樣面臨著文化和語言差異的挑戰。
19世紀60年代,女宣教士發現,傳播福音的一個更具戰略性的方法是招募當地的中國婦女作為“聖經女教師”,向她們的女同胞傳福音。最早的女宣教士往往是從宣教士家庭的僱員或中國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和母親中招募的。有些人受過教育,但許多人是文盲。由於新教對聖經的重視,女宣教士需要教她們閱讀中文——通常在自己能閱讀聖經,並傳達基督教基本教義之前,她們先學習羅馬字母化的中文。這些信念鼓勵女宣教士創建寄宿學校來教育中國女孩。由於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優先考慮男性的識字和教育,宣教士則希望每個人都有能力閱讀聖經,這一願望為這些中國婦女打開了機會。
最初,聖經女教師在外國女宣教士的監督下工作。她們的主要職責僅限於向婦女和兒童傳授聖經,通常是在農村。隨着她們的人數和技能的增加,這些職責開始包括探訪病人和提供各種形式的醫療服務。到19世紀80年代,一些宣教機構允許女宣教士公開向男女混合的群體傳福音和教授聖經。
最著名的女宣教士之一是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1873-1931)。余氏是中國長老會宣教士的女兒,在蘇州女子醫學院學習醫學。除了醫療工作外,她還擔任巡迴佈道員。1897年,她陪同美國人約瑟芬·坎貝爾(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韓國宣教,在韓國婦女中行醫和向她們傳講福音。六年後,當她回到中國時,她最終放棄了醫學,把注意力放在了復興佈道上。在一次復興聚會中,她帶領一位名叫林和平的婦女信主,在後來的聚會中,她又帶領林和平的兒子,年輕的“守望者”(倪柝聲)信主,這兩個人都成了傳道人。余在中國各地領導復興會議,並應邀在1927年的英國年度福音會議——凱瑟克(Keswick)大會上擔任主要發言人。
1896年,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從密歇根大學畢業,她是第一批從美國大學獲得醫學學位的中國女性之一。回到中國后,她看到了由當地華人發起和管理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她共同創立了中國宣教士協會,成為中國基督教婦女節制聯合會的第一任主席,並與美國傳教士詹妮·休斯(Jennie V. Hughes)在上海建立了伯特利(Bethel)宣教機構。石美玉和休斯的宣教機構在組織一些為傳播福音而成立的 “佈道團”方面發揮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931年由計志文(Andrew Gih)建立的伯特利全球佈道團,該團後來的成員包括著名佈道家宋尚傑(John Sung)。
婦女按立問題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在上海召開的會議幾乎聚集了所有在中國的新教宣教機構,討論全國的基督教工作。然而,女宣教士和女聖經工作者的聲音往往被擱置一旁,被歸入 “婦女工作”的單獨類別。當全國基督教會議在1922年舉行,並允許越來越多的中國基督徒發言時,這種情況開始改變。
燕京大學的誠冠怡(英文名Ruth Cheng)在一篇題為“婦女與教會”的論文中指出,五四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婦女權利的改善並沒有與中國教會中的婦女權利的改善相匹配。她解釋說:“我並不主張我們設立女牧師,但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我想問為什麼不承認婦女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和教會中的其他職務。”她進一步推斷,雖然早期教會和西方教會禁止設立女性領袖可能有其合理的歷史或背景原因,但這些原因對中國教會來說可能不再合理。婦女在教會中是擁有平等的權利,還是處於從屬地位?她總結說:“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目前的問題,而是這個權益的制定與否會對未來女性在教會運作中起到很大的影響。”
慢慢地,各教派開始正式接受正規的女性教會領袖。歷史學家達娜·羅伯(Dana L. Robert) 特指出,早在1871年,美國衛理公會的女宣教士就認為這些聖經女教師的出現意味着恢復了聖經中的女執事職權。然而,這些女宣教士的解釋在美國和中國等宣教區被爭論了幾十年。1924年,衛理公會大會在馬薩諸塞州舉行會議,談到 “在某些國家,特別是在國外,非常明顯地需要婦女有效地主持聖禮”。大會做出了一個不朽的決定,允許婦女通過按立成為當地的傳道人並享有有限的權利。這項決定將迅速影響到在中國的事工,在這個決定之後的幾年裡,有五名中國婦女被按立為福州和江西教會的地方傳道人。
另一個重要事例是中國的“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這是當時最大的教派。在1931年的總理事會會議上,華北教區詢問婦女是否可以被按立為牧者。經過一些討論,會議得出結論,教派憲章沒有禁止這一點。更令人驚訝的是,總理事會發現,它的許多成員教會已經按立了女長老。到20世紀40年代,其南福建教區也同樣報告說,它按立了更多的婦女為其教會服務。
在英國聖公會,羅納德·霍爾(Ronald O. Hall)主教於1944年在日本入侵時期,在澳門按立了李添嬡 (英文名Florence Li Tim-Oi, 1907-92) 為第一位女性聖職者,這引起了爭議。這在全球範圍內的英國聖公會中沒有先例。因此,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后,為了避免爭議,李氏辭去了她的聖職。1971年,當英國聖公會最終同意女性可以被按立為聖職時,黃嫻芸(音譯,英文名Jane Hwang Hsien-Yuin) 和喬伊斯·班尼特 (Joce M. Bennett) 是香港的最初兩位被按立者。
基督教的熱潮走向加爾文主義
在中國大陸,公共宗教活動在1960年代實際上已經停止。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年)結束和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的改革使得對競爭性思想的開放程度再次提高。到20世紀80年代,政府文件開始描述全國各地出現的“基督教熱潮”,即新教信徒的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既通過“家庭教會”運動,也通過在國家批准的“三自愛國運動”中註冊的地方聚會。從1980年代到今天,新教教會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女性。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婦女擔任領導職務的問題沒有再被爭論,女牧師和傳道人的大量出現成為常態。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是巡迴佈道者呂小敏。小敏生於1970年,出身於河南農村的回族,1989年加入了類似靈恩派的基督教教派,她以一種不太可能的形式的領導力而聞名:讚美詩。小敏的歌曲被統稱為“迦南讚美詩”,由於她沒有受過西方音樂記譜法的訓練,因此由其他人轉錄。小敏的1500首讚美詩在中國教會中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在註冊和未註冊的教會中都被廣泛傳唱。
但是在過去二十年裡,婦女在教會領導中的地位變得不那麼明確。雖然在政府批准的新教教會和神學院中仍然有強大的女性領袖,但在未登記的教會中,情況卻不同,這些教會越來越受到加爾文主義的影響。這些基督徒認為加爾文主義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神學體系,可以對抗越來越多的受基督教啟發的新宗教,政府將這些新宗教稱為“邪教”。許多對加爾文主義感興趣的人轉而閱讀派博(John Piper)、卡森(D. A. Carson)和凱勒(Tim Keller)的北美加爾文主義和新加爾文主義著作,以解決與培育基督徒家庭和在中國城市傳道有關的問題。其他人則從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荷蘭新加爾文主義教義中汲取資源,以參與中國的公民社會。
然而,這種在中國興起的對加爾文主義的興趣往往強調一種強烈的互補主義觀點,這與美國加爾文主義者寫的並被翻譯成中文的書有關。法爾曼(Fredrik Fällman)認為,互補主義的部分吸引力在於它與儒家父權制觀點的共鳴。這些變化對中國教會中女性領導力的發展軌跡產生了負面影響。
這些發展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中國基督徒對基督教性別理解的成見,比如認為男性有更多的理性恩賜(如加爾文主義所表現的),女性有更多的感性恩賜(如類似五旬節的基督教形式所表現的)。有些人擔心有魅力的婦女和錯誤的教義會把別人引入歧途,就如末日(異端)組織東方閃電是由一位婦女建立,她教導說基督已經回來了,但現在是以女性的形式。因此,加爾文主義和互補主義提供了保障,防止不可控制和極端形式的基督教對中國教會和社會造成問題。因此,這也促使婦女在教會中的從屬感增強。
我們不可能預測中國新教教會在未來會如何發展,特別是在女性領導方面。然而明確的是,19、20和21世紀的許多女傳道人和女牧師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新教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就像毛澤東著名的宣稱“婦女能頂半邊天”一樣,婦女也能頂起中國教會的半邊屋頂。
Alexander Chow博士是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神學和世界基督教講師。他寫了兩本關於中國基督教的書,最近的一本是《中國公共神學——中國基督教中的代際轉變和儒家想象》(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他在https://alexanderchow.wordpress.com上有一個學術博客,他的Twitter號是@caorongjin。
翻譯:平凡的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