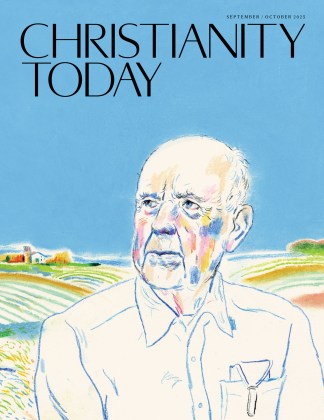當兩歲的蘿拉在高腳椅上扭來扭去時,我還是個青少年,正試圖逗她開心。我自認是個聰慧的保姆,於是我拿起她的塑膠餐墊,上面有米老鼠和米妮的圖案。
「這是唐老鴨和黛西鴨的照片嗎?」我問。
「不是,」她咯咯笑著。
「是高飛和布魯托嗎?」
「不是!」她大叫否認。
「好吧,他們是誰?」我問,並準備好獎勵她正確的答案。但她的回答讓我措手不及。
「他們是穿著戲服的陌生人!」
如今蘿拉已長大成人,但我一直在思考她在幼兒時期展現出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她對這個世界(迪士尼世界)一本正經的態度是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描述的「低符號藩籬」的完美範例。
我是在天主教作家羅海瑟(Ronald Rolheiser)的著作《四碎之燈》(The Shattered Lantern)中認識到這個概念。羅海瑟說,如果許多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感知到上帝的存在,那麼或許問題在於,我們的文化缺乏強而有力的符號。
使用符號的能力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想想看與「進食」有關的符號。所有動物都倚靠食物維持生計和愉悅身心。但人類可以使用燭光、瓷器、祝酒詞和祝福語來為一餐飯增添意義。透過符號,我們在進食的同時能體現浪漫、友情、榮譽或慶祝的情感。
我必須承認:我通常既沒有時間,也不願意為這些符號費心。例如,當我在路上吃東西時,我的符號藩籬就很低;食物只是身體的燃料,我的「那一天」只是個充滿需要我管理一堆事的「數個小時」。
但羅海瑟爾警告我們,低符號藩籬會耗盡我們人生經驗裡的意義。為了解釋這一點,他請我們想像一名被慢性背痛困擾的中年男子。
這種疼痛意味著什麼?它可能意味著他患有關節炎,這是個醫學符號;它也可能意味著男子正在經歷某種中年危機,這是個心理符號;它也可能意味著男子正經歷逾越節的奧秘,這是他的十字架,是個宗教符號。背痛也可能兼具以上三者。我們可以以低階的方式(關節炎之苦),也可以以高階的方式(成為逾越節奧秘的一部分)解釋自己經歷的符號。
上帝在我們日常經驗中的明顯缺席,與我們符號藩籬程度的降低密切相關。
我讀羅海瑟的書是因為有兩位朋友(一位是基督徒,一位是懷疑論者)承認他們渴望能更敏銳地意識到上帝的存在。無法「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這讓兩位女子很受傷。
《四碎之燈》提醒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不等於有信心。無論我們是否感受到祂,上帝都在我們身邊。耶穌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聖十架約翰(St. John of the Cross)在他知名的著作《心靈的黑夜》裡說,上帝有時會收回祂的同在。
然而,聖十架約翰指出,在其他情況下,我們的問題更多與我們自身的「盲目」有關。鑑於耶穌鼓勵我們尋找才能尋見(路加福音11:9),羅海瑟希望我們培養ㄧ種在冥想/沉思中「接收到祂」的能力——他相信在一般情況下,我們能感覺到上帝的存在。
在一個自戀、追求享樂和躁動的文化中,這樣的「接收能力」似乎徒勞無功。「低符號藩籬」既是我們問題的原因,也是我們問題的症狀。用詩人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話來說,我們身處的土地曾經「擠滿了穹蒼」,但現在往往更像蘿拉那張塑膠餐墊一樣扁平。當詩人看到「每個普通的灌木叢都燃燒著上帝的火焰」時,我們只看到矮矮的樹。
某種程度而言,我們低矮的符號藩籬是一種現代教義的副產品,即相信「大自然裡能見到的事物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但這也是我們宗教改革傳統的產物,因為我們對「迷信」心存戒備。畢竟,蘿拉是對的:米奇和米妮確實真的只是穿著戲服的陌生人,如果不這樣認為,就太愚蠢了。
但若有些情況真的就不只是表面上那麼簡單呢?當麵包和酒不僅僅是食物和飲料,而是破碎身體的符號?當洗禮之水確實能將我們帶入死亡及復活之中?
當古以色列人需要喚醒他們對上帝的意識時,同樣需要提高他們的符號藩籬。在撒母耳記上7章,他們倒出一桶桶的水來表達悔改,用石頭建造「以便以謝」來紀念上帝的供應和拯救。有時候,水不僅僅是水,石頭也不僅僅只是石頭。
許多人討論著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離開符號藩籬「低」的新教教會,轉而加入更注重禮儀的教會的現象。也許他們追尋的一部分正是更高的符號藩籬。如果我們在敬拜中用根基於聖經教導的符號包裹他們,事情是否會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必須對冒牌的「穿著戲服的陌生人」持警惕的態度,但我們也必須幫助自己記住,我們被邀請進入一部奧秘而奇妙的福音劇中——進入一個比虛構故事更奇怪(以好的方式)的真理敘事之中。
卡洛琳·阿倫茲(Carolyn Arends)是一名歌手、作曲家兼作家,她創作並發行了9張專輯,撰寫2本著作,包括《與天使摔跤》(Wrestling With Ang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