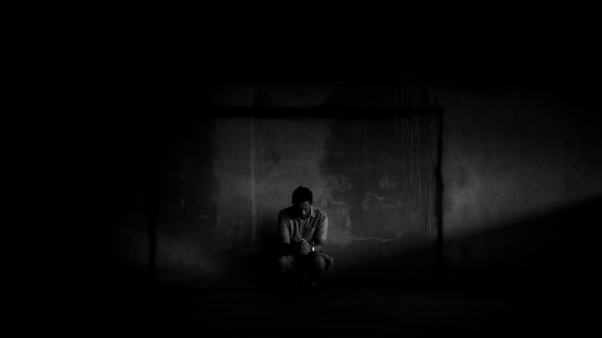如果你還沒有聽說,90年代又回來了。 頭髮亂蓬蓬的、超大的西裝外套、大地色系、還有厚底鞋 另外,當然還有對迪斯尼的抵制和關於自由派戀童癖的性崇拜的陰謀論。
我在90年代上初中和高中,當時既享受着我自己的那份對時尚的懵懂,也參與文化戰爭。 作為一個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成長起來的保守派,我記得那種為從不信神的左派手中拯救美國而鬥爭時,所面臨的不斷被圍困的感覺。
因此,當關於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覺醒主義”(wokism)和不斷變化的性風尚的辯論再次升溫時,我感受到時光的倒流。 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文化戰爭? 為什麼我們不能戒掉它們?”
公平地說,西方文化在90年代正經歷着一場徹底的轉變,就像今天一樣。 前蘇聯集團崩潰了,啟動了全球調整。 橢圓形辦公室的醜聞使“口交”成為一個常見的短語,甚至連我這個受庇護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在查了字典后)。
可以理解的是,那是一個政治兩極分化加劇的時代,特別是隨着保守派談話電台的興起。 像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這樣的人給這場鬥爭帶來了一種快樂的激情——一種自信和豪邁,不知何故感覺真實而自由。 他在銷售Snapple和Sleep Number的床時警告大家說要反對“女權納粹主義者”(feminazis)。 甚至當他嘲笑總統的女兒時雖然只是鑒於她父母明顯的腐敗,我們也覺得是合理的——而那是一個與我同齡的女孩。
因此,當美國共和黨在1994年奪回國會時,就像恢復了希望。 當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 Starr)領導的調查最終導致在1998年對克林頓的彈劾時,我感到了正義的快感。 沒有什麼文化戰爭可以像過去的老式文化戰爭那樣。
儘管有這樣的血統,我發現自己在看待當前的政治衝突時,仍然夾雜着疑惑、沮喪和深深的悲哀。 因為在21世紀的某個時期,在911之後和奧巴馬當選之前,我長大了。
我結了婚,組建了家庭,並進入了事奉的生活,包括基督教出版、《聖經》教學和農村社區的地方教會工作。 這些事務帶來了更多緊迫的問題,而政治則退到了後面。 我說服自己,這就像我的淺色水洗高腰牛仔褲一樣,某些東西已經在我身後了——已經過時了,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你看現在。 雖然目前的衝突表達方式略有不同,但我仍能識透它的基本輪廓。 當我聽到右翼和左翼的談話者複製我年輕時的那種篤定、自信和膽量時,我也會有一種間接的不適感。
多年來,我一直試圖理解為什麼文化戰爭會如此滿足人內心的需要,甚至是還在初中和高中的時候。 我是一個狂熱的基督徒,想討好上帝,並渴望得到肯定。 當我發表某些意見時,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
當我嘲笑自由主義者時,我周圍的成年人都笑了起來。 當我寫關於好萊塢和音樂產業墮落的論文時,我在基督教學校得到了高分。 而當我在大學里為保守派政治候選人競選時,我得到了額外的學分。
現在回想起來,我明白我的亞文化在鼓勵我走向戰鬥。 但就像我在那些年所犯的時尚錯誤——一英里高的劉海和裁剪的波波頭——還有更多我知道的錯誤。
當一個青少年嘗試時尚時,他們往往試圖找到自己,渴望適應,並處理從童年到成年的普遍焦慮。 所以我很同情年輕時的自己——既缺乏時尚感,又缺乏政治上的天真。 但我不想為我被吸引到文化戰爭中的事實找借口。
《雅各書》4章談到了我們對戰爭的熱愛,並指出了其根源。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着; 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1-2節)
這些告誡就像是對我所說的。 作為一個年輕的文化戰士,我有一種義的突然衝動。 我需要知道我是一個好人,而發動文化戰爭正是向自己和其他人證明這一點的一個好辦法。 我想,這也是我想讓上帝也認同這一點的一種方式。
但就像任何其他藥物一樣,自以為是這種葯需要一個源源不斷的供用渠道。 每一次受到打擊都需要彌補。 當你喜歡上這種衝動時,你很快就會上癮,直到你唯一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就是戰鬥。
對於想要公開作見證的基督徒來說,這就是事情變得棘手的地方。 我們應該是不情願的戰士,只有在正義的衝突召喚我們去保護他人時才拿起武器。 (社會正義就是一個例子。)在公共廣場上倡導和捍衛我們的原則是一回事;享受戰鬥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而我們中有太多人喜歡戰鬥。 我們樂於對我們的意識形態敵人進行掠奪和破壞。 我們喜歡戰爭,因為伴隨着正義感的涌動。
因此,我想知道打破這個循環的方法是否是重新評估我們的慾望和需求。 如果我們不需要在Twitter上的尖銳評論所帶來的優越感呢? 如果我們可以依靠我們自己的作為——不論是政治的或其他的——以外的東西來知道我們是安全的和被愛的呢?
當我回想起90年代的我,我看到一個渴望討好神的年輕女子。 但我也看到一個不成熟的年輕女子——她太忙於討好神,而不明白神在基督里已經悅納了她。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我所做的只是成長。 我已經清醒過來了。
在我20歲出頭到20歲中期的某個時候,我遇到了一種福音的表達方式,即把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公義置於我自己之上。 我一直知道我是個罪人,一直知道其他人也是。 但是我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處理罪,也沒有理解基督為我所做的工作。 因此,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通過更努力地工作,努力做正確的事情,並重塑自己來表明我對上帝的承諾。
如果我能夠重塑自己,足以克服我的罪,那麼其他人也應該能夠做到。 當他們做不到的時候,至少在當時的我看來,我完全有理由譴責他們,與他們交戰。 由於不了解神的恩典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作用,我無法看到它在別人的生活中起作用,甚至在我們的辯論中恩典向其他人 延伸。
我對特殊恩典視而不見,這意味着我對普通恩典也視而不見。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不知道我是否變得不那麼保守了。 我仍然持有讓我的進步主義朋友們感到不安的政策立場和觀點。 但有一件事對我來說已經改變了:我不再需要戰鬥了。 而且我不需要戰鬥,是因為我不需要證明什麼。 在上帝的仁慈和基督的公義中獲得安全感,我可以自由地在我周圍的世界中為他們的益處而工作。 我可以自由地愛人如己,為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因此,在新一輪的文化戰爭肆虐之際,請聽從一位老兵的建議:憑愛心講誠實話,但不要以為持有某種立場或以某種方式投票就能讓上帝更愛你或更少愛你。 不要以為祂愛你的鄰舍比祂愛你更多或更少。 不要以為你的公義來自於其他地方,除了祂。
嘗到了上帝的美意,經歷了祂無償的恩典,就到世界上與他人分享。
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和《謙卑的根:謙卑如何磨練和滋養你的靈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譯:平凡的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