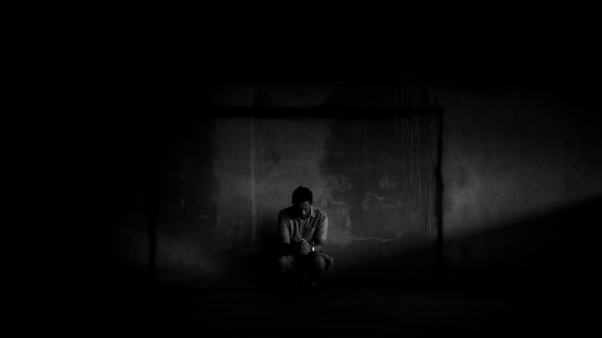1902年,在我家南邊只有幾小時車程的一個俄勒岡海濱小鎮庫斯灣(Coos Bay),一名叫做阿倫佐·塔克(Alonzo Tucker )的黑人被人處以私刑,吊死在一座橋上。 這是本州唯一有案可查的私刑案。 但是這僅有的一點細節,就已足夠讓我的喉嚨感到發緊了。 因為有人指控塔克襲擊一個白人女人,一群憤怒的暴徒糾集在一起,要把他當街處死。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保護他不被眾人傷害,他被關進了拘留所。 在被關進去後,他驚惶失定,居然想辦法逃了出去,在某個碼頭下面藏了一夜。
到了早上,一夥人發現了塔克。 當他試圖逃走時,開槍把他打中。 儘管沒人有把握,但塔克本來很可能死於槍傷。 為了保證他必死無疑,也為了讓此事昭示公眾,在這個俄勒岡煤礦小鎮的城中心,他們將塔克吊在四街橋上。
塔克的故事,是我在研究俄勒岡的種族不公曆史時偶然發現的,於是在心中就久久揮之不去了。 當我們全家要到海濱度假時,我告訴先生要繞道去庫斯灣一趟,拜訪一下塔克的罹難之地。 他開車去五金店買木材,做了個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帶著上路。
等到了地方,我卻無法找到四街橋了。 於是,先生在當地的歷史博物館把我放下,然後帶著孩子們去公園玩。 當我尷尬地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提起私刑的事時,他倒是恰好知道我要問什麼。 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了我,還從地方史誌中為我複印相關資料。 我問他博物館是否會考慮辦一個關於塔克的展覽,他傷心地搖頭。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信息,”他說,“阿倫佐甚至連張照片都不曾留下。”
原來,由於海岸地貌的變遷,塔克被吊死的那座橋早已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緊挨著高中的一條挺繁忙的街道,一邊是橄欖球場,另一邊是棒球場。
在公園裡,我和先生、孩子們會合。 我告訴他,也許我們不該去安放我們的紀念物,這個主意有點蠢。 但是就在此時,我在公園裡看到一個很大的雕塑,是一個下面帶著銘牌的十字架,用來紀念在越南戰爭中參戰、犧牲的本鎮居民。
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已的十字架愚蠢?為什麼我對自己紀念塔克、承認俄勒岡歷史上黑暗的一天的計劃會猶豫畏縮,而老兵紀念碑卻看起來這麼容易接受。 不管怎麼說,紀念物是美國景觀的一部分。 我意識到,不那麼顯而易見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中用以選擇紀念什麼人、什麼事情的那套標準。
從1877年直到1950年代早期民權運動興起,有4000名以上非裔美國人被處以私刑。 私刑是為了維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公開採取的一種粗暴手段,經常得到政府當局的默許。 儘管我所在的家庭學校社區非常強調美國歷史,儘管為引起世人對私刑氾濫的關注,十九世紀最著名的反私刑活動人士埃達·B·威爾斯(Ida B. Wells)等人進行了種種勇敢的努力,卻從未有人向我教授這一部分文化遺產。
我們決定按原計劃行動,把車開到了高中。 看著眼前不斷的車流,我想,這可不是我原來想像的情形。 現在是午餐時間,到處都是學生,真不是一個進行沉思靜默、致敬的地方。 我在膠合板做的白色大十字架上寫上“阿倫佐·塔克1902”,先生試著把它釘到鋼絲網眼柵欄旁的地裡。 我則呆在車裡,安全地躲開人們的注視。 他沒辦法把它插入堅硬的地裡,而我們也沒想到帶什麼東西來把它係到柵欄上。 他只好把它靠在鋼絲網上,拍了幾張照片。
 Courtesy Krispin Mayfield
Courtesy Krispin Mayfield一輛警車駛過,我感到一陣恐懼:我們會因此惹麻煩嗎?我告訴先生快點,他就跳上了車。 駛離那裡,我深感到缺少個儀式。 在開回海邊的路上,孩子們在後座上哭叫,我則緊緊把住方向盤,依然不停地往後看,觀察是否會被攔下。 對於自己是如此的緊張、所做是如此之少,我感到吃驚。 我的先生向我保證,即使不為別的,只為我們自己的緣故,今天所做也是值得的。
我們這時還只是剛剛開始了解,這些紀念標誌是被賦予了怎樣的神秘權威,來決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哪些故事會被流傳下去,哪些會被遺忘。 在五月(2017年——譯者註)的某個時刻,當時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邊,關於是否移除新奧爾良邦聯紀念碑的爭論正達高潮,我們開始意識到,紀念性標誌對於我們如何對待過去的罪,有著一種微妙的影響力。 這種力量可以把這些罪遮掩起來,也可以把它們暴露在日光之下。 我開始思考那些我們寧可忘記、無人提及的歷史。 在我們最想忽視的那些集體之罪中,令人悲痛的美國私刑史大概名列榜首。 但是這次旅行讓我感觸最深的卻是這個:人無法就被掩埋的罪悔改。
學習認識罪
為阿倫佐·塔克設立紀念標誌,不完全是我的主意。 幾個月前,我拜訪了布萊恩·斯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以及他創建的政策推動團體“平等司法倡議“(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的辦公室。 史蒂文森當了三十年的律師,為死刑犯爭取司法公正。 部分由於他的暢銷回憶錄《只是憐憫》,他在全國都有名氣,已是為爭取美國種族司法公正而發聲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斯蒂文森在非裔美國人循道宗-聖公會教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AME)長大,在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之前,指導東方大學的福音合唱團。 他在公共演講中穿插聖經經文,說信仰是他事業的支柱。 我想親眼見識他的工作。
在那裡,我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牆。 它幾乎完全被擺在木架子上的漂亮玻璃瓶子遮住。 瓶子裡裝滿了土,揉合著綠到棕、金黃到銹紅的不同色澤,一排又一排地層迭起來,從地板一直到高高的天花板。 乍看起來感覺很漂亮,但湊近細看就不然了:每個瓶子上都有一個名字和地點。 斯蒂文森告訴我們,每個瓶子裝著的土,都是從阿拉巴馬州內已被確認的某個私刑地點取來的。 這整面牆,包括所有這些瓶子、這些名字,只是一個州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對這段我並不完全了解的歷史的快照。
斯蒂文森是在黑人的課堂上開始受教育的,親眼目睹律師們為了消除當地學校系統中的種族隔離而進行的抗爭。 他非常清楚,美國人是各自按著差異顯著的歷史版本被培養長大的。 也是因為這個,在為司法體系中繫獄者的合理、公正待遇奔波了三十年後,他正在改變與種族偏見做鬥爭的策略。
“幾年前我開始意識到,執法者受到歷史敘事的影響。 對歷史的了解、他們的價值觀以及響應敏感度,都在影響著他們。” 斯蒂文森在一次訪談中說到,“就種族問題而言,我覺得美國在如何面對歷史上做的不怎麼樣。”
斯蒂文森開始著迷於開拓一些介紹真相的空間。 他說,“在這個國家裡,沒有幾個地方你可以誠實地體驗奴隸制的歷史,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誠實地體驗私刑和種族恐怖。” (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會有例外。 比如在明尼蘇達的杜勒斯,就為1920年一個巡迴馬戲團被處私刑的三名黑人成員,建立了一個紀念標誌。)
於是,斯蒂文森決定自己建一個。 明年(2018年——譯者註)夏天,EJI將為一個紀念碑揭幕。 來訪者將看到從一個方型結構上懸下的一個個有字的大方塊,從視覺上提醒人們曾發生私刑的八百多個郡。 數不清的標誌牌刻著數不盡的名字,這一景觀將把俯瞰阿拉巴馬州蒙哥瑪利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岳,變成一處哀悼、紀念之地,一處慟哭、甚至集體懺悔之地。
它的名字是“和平與公正紀念碑”,還包括了主建築旁延展開來的土地。 每片懸掛的方塊,都有相同的一片安放在那片地裡,帶出一種類似於墓碑的令人心悸的感覺。 這些標誌牌將由各郡的人來領取。 斯蒂文森夢想著,會有不同人群來到蒙哥瑪利,取走私刑史上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他們的鄉鎮、城市顯眼地展示出來。 如果某地的人不想認領他們的那一片,它就將突兀留在蒙哥瑪利的山頂上,成為無人承認之罪的紮眼標誌。
 Courtesy EJI
Courtesy EJI聖經與紀念
對於美國人來說,紀念碑、紀念物就是集體記憶中的一種建築砌塊。 就像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家柯克·薩維奇(Kirk Savage)所形容的,它們試圖“保存那些值得記住的,而丟棄其餘”。 對於基督徒,這也是聖經的關鍵功能。 聖經就是一系列神啟的回憶,通過傳統和社區而流傳下去。 這麼多的故事,尤其是舊約中的那些,並不是俗套的道德故事或者勵志型陳年舊事。 這些故事鉤勒出的,是一個為愛神和愛鄰里而掙扎的民族,裡面充滿了告誡的警句和對更忠誠、更正直的敦促。 記住與神的約,記住神的誡命。
不能遵守神的誡命,即使在個人層次,也可能招致深深的集體傷痛。 在《約書亞書》第七章中,亞幹從耶利哥城中盜竊被禁財物的決定,並不僅是一件他獨自承擔後果的個人之事— 亞幹的家族和其他三十六個人因此丟掉了性命。
作為對集體之罪的回應,先知們樹立了集體懺悔的樣板。 在《但以理書》第九章中,但以理為在別處、別的世代犯下的罪懺悔,他認為把自己包含在這些集體悔罪中是至關重要的。 他是這樣祈禱的:“主啊,我們的君王、首領、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 (但9:8)同樣地,時間和距離都意味著尼希米個人並未參與拜偶像、壓迫人這些他所懺悔的罪。 但他知道,為了他的人民,必須公開承認這些罪。
集體之罪超越時間和世代,這一概念並不限於舊約。 “使創世以來,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算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耶穌告訴法利賽人(路11:50-51),“是的,我告訴你們,這都要算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在聽彼得講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徒2)的眾人中,沒有幾個是當時在各各他現場的。 實際上,這裡的“你們”,包括了“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西亞省、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呂彼亞一帶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旅客,猶太人和進猶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亞拉伯人”。
利洛伊·巴博(Leroy Barber )陪我拜訪了EJI。 這位著名的黑人牧師兼作家,經常在教堂中談及種族問題。 對他來說,這個土樣蒐集項目和建議中的紀念物是對逝者表示尊敬,是療傷,而且非常個人化。 “我的母親就出生在蒙哥瑪利南邊一點,一個叫做門羅維爾的小地方,”巴博告訴我,“當我在那裡查看標有所有私刑地點的地圖時,我母親出生的這個小鎮就有七、八處,這真讓人感到難以置信。 我的家人要生活於這種現實中,實在是一種深深的悲哀。”
對於巴博等人來說,在蒙哥瑪利這種地方設立紀念物、紀念碑不只是關於集體懺悔、改過,儘管他也認為這些很重要。 關於正確敘述歷史的重要性,他在聖經中找到了強有力的先例。 “《申命記》中說,‘這些故事,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以免你的子孫忘記,要讓你的子孫知道他們從哪裡來。 這是基督徒的立場。” 他說道,“布萊恩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它讓很多黑人可以自由地講述他們的故事,為他們儿女、孫輩再現歷史敘事。”
巴博的話讓我想起,多年前參觀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紀念大屠殺博物館時,我被紀念廳中用大字展示的《申命記》4:9節經文:“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
我從未想過這些經句的重要性。 但對於神的子民保守信仰與傳統,它們確實是必不可缺的。 在聖經語境中,這一勸誡讓人們記住與神之約以及違約的嚴峻後果。 對於任何經歷過種族、民族暴力衝突的國家、社區,這已成為一條共同的脈絡。 牢記再牢記,以使你們不會忘記,不會重犯同樣的暴行。
正如斯蒂文森經常指出的,我們的國家“到處充斥著邦聯的標誌”。 這既是一種對歷史的偏頗複述,也擠掉了悔改的空間。 “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的罪懺悔,我們就不會被原諒,在這個國家我們就無法把這件事處理好。”
面對我們過去的罪
作為一項全國性的倡議,EJI已經獲得了相當的名流支持,包括與穀歌合作發表它的研究成果。 斯蒂文森也曾在紐約市的救贖者長老教會和柳溪協會的全球領導者峰會上發表演講。 但他還是非常渴望能把EJI介紹給更廣泛的基督徒聽眾。
說基督教在美國的種族不公問題上(包括奴隸制、私刑和反民權政治)有著一段複雜的歷史,還是有點輕描淡寫。 一方面,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頌揚像英國的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這樣的基督徒廢奴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蓄奴制不僅受到作為個體的基督徒奴隸主和莊園主的支持,也受到教會、各宗派和神學家們的支持。
在十九世紀美國的廢奴運動中,基督徒經常是活躍在最前列的。 但是基督徒中的大多數並不是這樣的。 南方教會積極地為施行奴隸制辯護。 例如,1864年南部邦聯的長老會代表大會宣稱,“我們的對手長久以來持續不斷的挑釁,使我們內心更加相信,家庭蓄奴是神的旨意… … 我們毫不猶豫地確認,保持奴隸制,並使它成為對主人、奴隸雙方的祝福,是南方教會的特殊使命。”
直到最近幾十年,各宗派才開始公開地面對自己充斥著種族主義的過去。 主要因為與北方浸信會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分歧而於1845年創立的美南浸信會聯會,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影響廣泛的宣言,為在體制性種族主義中的共謀行為道歉。 而美國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則在2002年為其先人在維護奴隸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懺悔。 2016年PCA通過了另一項提案,為民權運動時期教會內部的種族主義而悔改。
但是這些高層的懺悔姿態有多少會涓流觸及到各個教會、每個信徒,這就很難說了。 我們美國人,天生具備捧高成功的本事,但在選擇紀念哪個悲劇時,就矛盾的多了。 斯蒂文森喜歡提到,為“911”事件的受難者建立紀念碑只花了十年時間,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個關於奴隸制的國家級紀念碑。
宗教與暴力攪在一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許多有很高基督教人口的國家裡,你可以在種族衝突的雙方都找到堅信聖經的基督徒。 在訪談中斯蒂文森經常提及,在柏林,“你走不上一百呎,就會看到一座紀念碑,安置在被綁架的猶太人家庭住宅前”;或者,真正的人頭蓋骨就展示在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博物館裡。 但在美國,他指出,“我們不提私刑這件事。 更糟糕的是,我們還編造了一種反敘事,說我們沒有什麼可羞恥的,我們的過去是浪漫而榮耀的。”
 Courtesy EJI
Courtesy EJI經上告誡我們,悔改不是為了傷害,而是一種讓我們遠離罪、另選他路的工具。 在悔改中,我們認識到罪在我們的靈魂和社會所造成的裂隙,進而承諾去做修補的工作。 “我對用歷史來懲罰美國並不感興趣”,斯蒂文森告訴我,“我想使我們得解放,找到讓我們得救贖的道路。 但如果不願意讓我們過去的真實情況為人所知,我們就不能達到救贖。”
沒有幾個地方像蒙哥瑪利一樣,把這種不情願明顯地表露出來。 這裡有五十九個紀念、頌揚邦聯的標誌物,但直到2013年為止,還沒有一個紀念國內奴隸貿易的紀念標(EJI現在已經設立了三個這樣的標誌,註明蒙哥瑪利作為美國最繁忙的奴隸交易港之一的角色)。 “我覺的我們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真正尋求真相為和解”,斯蒂文森是這樣說的。 “只有真正尋求這些,我們才會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尋求交集
在斯蒂文森的私刑紀念碑行動中,可以聽到逝去的基督教改革的迴聲。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有大量著述,講述了相互競爭的基督教派系— 一派強調集體之罪,另一派注重個人之罪— 如何在十九世紀初走到一起,發動了戒酒和廢奴運動。 一方面,當時公認的主流正統基督教組織強調聖約化社會的概念。 他們認識到全國性之罪對於美國的威脅,呼籲加強教會的道德權威作為解決方案。 成對比的是,那一時期新興教會,例如循道宗、浸信會及其他較小的宗派,更傾向於把罪視為個人之事。
但是在1830年代,基督教的這兩個派系在某些社會關懷事業上找到了交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對酗酒和奴隸制。 而這兩者都被視男扭曲個人和集體道德的力量。 部分基於新的著重點,同時強調全民之罪和個人、公眾懺悔,這些基督徒發動了美國歷史上最早的社會運動之一。 特別地,中產階級基督徒婦女熱切地參與糾正社會弊病。 在她們的公開抗議下,許多教會公開地摒棄奴隸制。 至1838年,已有1348個專門的廢奴社團登記在案。 在其他社會組織還在保持沉默之時,這一情況表明了人們要解決時代的道德之罪的渴望。
“北方的白人廢奴主義者,隨著第二次大覺醒帶來的屬靈復甦而迅速擴展開來,將個人之罪和全民問題聯繫起來”,楊在訪談中說到,“內心情感的深度與社會運動的廣度相結合,是這次運動的動力。”
例如,1837年紐約州West Bloomfield 第一教會通過的反奴隸制決議在總結聲明中說:“作為個人,也作為教會,我們對此做出承諾。” 這種情緒在廢奴主義者中是很普遍的,迫使宗教組織與信徒個人將懺悔作為一種結束全民之罪、使自己靈魂免受刑罰的手段。
楊注意到,這就是舊時懺悔運動與斯蒂文森希企通過EJI、私刑紀念碑所要實現目標之間的關鍵相似之處:比許多現代抗議示威中表示出的憤慨要深刻的多的,一種個人轉變的要素。 “所謂‘懺悔抗議’的核心觀念在於它沒有那種自義的成份在內”,楊指出,“做見證的人差不多承認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悔改的另一面
 Steve Jurvetson / Flickr
Steve Jurvetson / Flickr肖恩·盧卡斯(Sean Lucas)對於公開懺悔是知道一些的。 為幫助整個PCA做到這點,他忙碌了好多年。
這位改革宗神學院教授參與起草了2015年長老會的一項決議案,就教會在民權運動時期所犯下的踐踏民權共謀之罪表示悔改。 這項議案在當年的代表大會上沒有通過,但是其修改版在2016年通過。
“特別是對於改革宗裡的人,這不應被視為奇怪或瘋狂的想法”,盧卡斯說。 長老會在聖約社區這個概念上有著深久淵源,甚至認為,在某個特定時刻,所有的基督徒與其他正在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是結合在一起的。
盧卡斯知道,像斯蒂文森所鼓吹的那樣,對以往的罪進行公開的紀念、懺悔,並不就意味著通向得救。 但是,“儘管這樣不一定就會得救,但是實際上得救的證據就在於對你自己罪的承認,以及認識到祖輩犯下的罪是怎樣對你和你的社區持續地發生影響。”
在斯蒂文森開始為死刑犯們服務後,他被悔改的威力打動了。 他還記得,作為一名年輕的律師,是怎樣將他的客戶、他所代理的人視為潛在的使徒的,就像使徒保羅一樣,其過去所為可以幾被饒恕,成為被救贖者的楷模。
“我們[基督徒]對於悔改的另一面、認錯的另一面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就是修復”,斯蒂文森說,“如果我們強調指出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鼓勵整個民族,就歷史上煩擾我們已久的偏執、歧視,更好地從中恢復、認知和做出響應。”
建立新的紀念物
紀念碑和紀念標誌在本質上是解釋性的。 它們幾乎總是在事後樹起,給出一種更深刻的敘事。 這敘事不僅僅是關於那些它們要紀念的歷史,更在於一個社會所希望保存的那些價值。 所以,因其在影響、拓寬我們對歷史、社會不公及其他問題的理解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當前對這些紀念物進行再評估的討論是有很意義的。
例如,當一些教會領袖努力保留住一間具有歷史意義的德國教堂中的一座反猶雕塑時,這正是他們的意圖所在。 他們不是把雕塑移走,而是加上一塊銘牌,喚起人們對大屠殺的恐怖暴行悔改,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在公共空間中,一類紀念碑充斥氾濫,而另一類卻明顯缺乏,於是我們許多人多多少少因此而形成了一套扭曲的歷史觀。 在這種前提下,當基督徒投入到相關的社會問題中,這意味著什麼呢?
對於我們某些人,這正好意味著需要去蒙哥瑪利朝聖,審視這段歷史負擔。 對於我,則意味著親自來到俄勒岡的庫斯灣,和我的先生和兩個孩子一起,舉起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向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的名字和記憶致敬。
我們臨時搭起的紀念物倒底有什麼長遠的意義?這個很難說。 會有學生走過塔克的十字架,然後去網上搜索他的名字嗎?會有老師利用這個機會來給學生上一堂歷史課嗎?它會招致投訴嗎?這就像附近越戰紀念碑上的十字架引起“免除宗教影響”團體的抗議一樣,提醒著我們,無論結果如何,塑造記憶的爭鬥本身又在被不斷變化的社會習俗所塑造。 或者,乾脆就是某個清潔工找到它,然後扔進垃圾箱,而沒有讓任何人感到自己對走過的這片土地的衝擊?
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我只知道,我和先生在本州內,到離我家不到一天車程的一個地方進行了一次參拜之旅,來向一位種族暴力受害者的名字表示敬意。 通過安放我們自己的紀念物,這樣一件細小而不起眼的行動,這次旅行使我們發生了改變。 我們所發現的,是不會被忘記的;我們也無法抹掉過去的恐怖。 我們試圖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來面對它。 認錯,和悔改、哀慟一起,是我們在成長中作為基督徒學到的基本功課。 為了盡力尊重我們的歷史,我們就必須完整地把它敘述出來,我們也要盡力把它們教給我們的孩子,以免我們都把歷史忘記。
作者梅菲爾德(D.L. Mayfield)為《今日基督教》的定期投稿作者,並著有《是融入,還是回歸故國》。 近作包括《今日基督教》的封面故事“為什麼我不再酗酒”(2014年六月號)。 她生活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 安迪·奧爾森( Andy Olsen)關於本文主題有另外報導。
翻譯:吳京寧